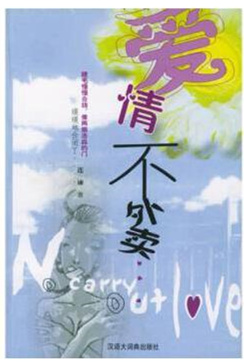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愛上你不是我故意
文:連諫
1,背後的班駁老牆
瀚遠坐在營業廳的沙發上,窗外不遠處是一堵老牆,爬滿薔薇,粉色花瓣之間瀉露著老牆的班駁和頹廢,他的手不時在茂密的頭發裏穿來穿去,很是煩躁的樣子,他的信用卡卡在取款機裏了。
我遞給他信用卡和身份證時,順便遞給他一杯水。
他握著水,看我,嘴唇抿得很緊,一仰頭,一次性杯子就空掉了,扔進垃圾箱,生動地笑了一下,走到門口,忽然回頭,指著我的胸牌說:王若夕,我叫伍瀚遠。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瀚遠,像姍姍來遲的翅膀,飛過我的生活。
我以為,隻是飛過而已,他那般倜儻的男子,我這樣平庸的到自卑女子,有些事注定是相互擦肩而過的翅膀而已,包括在想象裏。
隻是,我牢牢地記住了他的名字,伍瀚遠,1973年出生。
後來,瀚遠常來,與其他試圖接近女孩子總以存錢取錢等行為做為欲蓋彌彰的借口的男人不同,他從不掩飾目的,業務忙時,他雙手插在休閑褲後兜,依在窗邊,看我,或看窗外薔薇花下的班駁老牆,沒人辦業務時,他走到櫃台邊,表情嚴肅地說一些笑話,別人用聲音和表情笑,他的笑在目光裏,隱隱閃爍,像頑劣的孩子觀賞自己製作的惡作劇。
他在時,用來點鈔的濕海綿就沒了用武之地,我的手,從掌心到指尖,終日濕潤,鈔票卻數錯了N次。
瀚遠喜歡熙熙攘攘的街道,說每一張臉背後都隱藏著一種別人不知的生活,精彩迷人或者灰暗碎落,人生的意義就是承擔上帝安置給一份生活,掙紮越多傷害越深,在一起時,他愛說些奇怪的話,沒邊沒沿,像一潭水,我探不到底。
瀚遠第一次拉我的手,很小心,像膽怯的小小乞丐,擔心被貴婦拒絕,我捉住他的中指,再沒鬆開,瀚遠沿著路基飛快走,不說話,好象世間布滿了刺眼的光芒。
瀚遠愛給我買衣服,化妝品,各種各樣的,掛在他的家裏,到處都是我的痕跡,妖冶而嶄新,如同我做女主人已經很久。
他帶我回家見母親,一個時刻保持著警覺的老年女人,像是我懷疑和瀚遠的愛情有做戲的成分,總以路過為由,敲開瀚遠的門,默默地觀察我們,目光裏藏著哀傷,有時,我們進門,會看見床上換了新床單,多了一個柔軟而漂亮的情侶枕頭,客廳裏多了一雙女式拖鞋,甚至在茶幾上留下了一對戒指,她用這種方式暗示:我想你們結婚。
瀚遠從不表示什麼,我靠在他臂上,問:瀚遠,你愛我嗎?
瀚遠歪頭看著我,眼神空茫。
我不想讓他看見,此刻正有淚水在心間滴過:如果你不是愛我,請不要用你的好來誤導我。
我走到窗前,刷拉拉開窗簾,在記憶中,窗簾從沒拉開過,瀚遠擋了一下眼睛,明淨的陽光紛紛撲到他臉上,我撫摩他俊朗的臉,自卑讓我從未好好端詳過,我仰起頭,閉上眼睛:瀚遠,如果你愛,就請吻我。
相處半年,除了拉手,他的唇從未碰過我。
我環過他的腰,舌尖在他臉上爬行,觸到了一滴鹹鹹的液體,瀚遠流淚了,順著舌尖,一滴滴爬進唇齒。
這是我的初吻,和淚流滿麵的、一直睜著眼睛的瀚遠,然後,進臥室換上吊帶睡衣,鏡子裏的女子,滿麵紅暈,有優美而修長的脖子,裸露著美麗的蝴蝶骨,小巧而圓潤的胸匍匐在滑軟的睡衣下,遭遇了愛情的燃燒,再平常的女子都會放射出耀眼的美麗。
我走出來,望著他,輕輕抹下一根吊帶,他的眼睛跟著睡衣跳了一下。
我伸手抹向另一根時,他的眼睛露出了驚恐,睡衣軟而涼地滑到赤著的腳上,我裸露在繽紛的陽光裏,說:瀚遠……
瀚遠呆呆地看著我,我鑽進他懷裏,滾熱的麵頰抵在他胸前燃燒。
從那一天起,我住在瀚遠的房子裏,用他買給我的東西,幸福像夏天的雨,說來便來了,一度讓我不知所以。
有時,瀚遠的母親來,我會來不及換下睡衣,她眼中則裝滿如釋重負的笑容。
除了上班,瀚遠很少出門,像貪婪糖果的孩子一樣貪婪著我們的身體,邊撫摩著我纖細的腰身邊喃喃自語:多麼美好,為什麼我不曾在意呢?
夜裏,我會蔌地睜開眼睛,總感覺溫暖安寧的愛情之下,潛藏著一絲神秘,我不知道是什麼,這種預感一直追隨著我,不棄不離,從最初的開始………
2,宿命的幸福距離
瀚遠失蹤了,我找不到他,整整兩天兩夜,不曾回家,我給他母親電話:阿姨,瀚遠有沒有回家?
她回答沒有時我就哭了:瀚遠有沒有打電話跟你說他要去哪?
沒有,或許,幾天後他就回來了……
我們抱著電話絕望地哭,瀚遠從不這樣,哪怕下樓買煙都會告訴我,當失去最愛的人的消息,總會情不自禁想到最壞結局。
瀚遠就是這時回來的,我驚叫一聲,扔了電話撲過去,他垂著頭,胡子參差頭發淩亂,滿眼血絲。
你去了哪裏?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
那是第一次,瀚遠讓我看見他的無助,把腦袋埋進我的胸前,無聲地流淚,我的心很碎,不知該怎樣去疼這個大男人。
眼前落了一雙腳,門一直開著,一個修長蒼白的男子,直直地看我和埋在我懷裏的瀚遠:對不起,這兩天,瀚遠在安慰被愛情拋棄的我。
我認識了俊輝,瀚遠從小長到大的死黨,一個愛惹事卻不能擔當的懦弱男子,每次挨欺負都要瀚遠為他出氣。他用陰鬱的聲音講著自己和瀚遠的過去,講到好笑的地方,他大聲地笑,仿佛沉滯的空氣都在受驚奔跑。
慢慢的,瀚遠緊抿的嘴角開始鬆弛。
走的時候,俊輝拍拍瀚遠的手臂:你和若夕結婚,我要做伴郎的。
我爽快說好啊。瀚遠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沒說話。
夜裏,瀚遠在黑暗中說:我不在家時不要讓俊輝進來。
為什麼?
他是個不祥之人,他走近誰,誰就和幸福有了距離。
沒想到你還是個篤信宿命論的人呢。
3,你是自己的青衣
我沒法不讓俊輝進門,我喜歡聽他講和瀚遠的輝煌過去,愛上一個人就會愛上他的一切,他的曆史現在以及未來,而瀚遠從來不說。
俊輝瘦得讓人擔心,白皙修長的手,會調很多種酒,做色彩誘人的沙拉,幫我把幾件普通衣服搭配得搶眼,送給我蒸汽麵罩時說:相信我,天下男人都愛美女,而所有美女都嫌自己美得不夠,它會讓你的皮膚更白皙細膩。
他教我做這些時,瀚遠叼著煙,調侃旁觀的架勢,有時鬧瘋了,俊輝還會披上我的衣服,做個嫵媚的倩然回眸一笑:如果演京戲,我是最好的青衣。
每每這時,我會看呆,真的,俊輝的回眸間有著女子都不可或奪的嫵媚妖嬈。
瀚遠卻騰地起身,冷冷說:你們不覺得無聊嗎?
氣氛就冷了,淡了。
好在俊輝夠大度,從不計較,玩太晚了,他就睡在客廳沙發上,闖進我們二人世界的俊輝讓瀚遠很是不悅又說不口什麼,隻是悶悶地怒,我便替俊輝開脫:全當安慰一顆因失戀而傷感的心嘛。
因習慣性失眠的俊輝在客廳走來走去,搞得瀚遠亦翻來覆去睡不著,早晨,頂著兩眼血絲焦躁去上班。
有天晚上,我翻身時習慣地把胳膊搭過去,竟落空了,瀚遠不在床上,我聽見客廳裏有壓抑的哭泣,是俊輝,女子一樣哀婉纖細,在我按亮床頭燈時,嘎然而止。
我下床,忽然感覺有些頭暈,視線也模糊,揉了一下,依舊模糊,聽見動靜的瀚遠走進來:若夕,你怎麼了?
最近總是頭暈。
瀚遠扶我上床:好好休息,可能睡得太少了。
4,開始遁匿
我頻繁地頭暈,食欲不振,甚至瀚遠帶我回他母親家吃飯時,強烈的惡心挨不到跑進衛生間。瀚遠的母親幸福地看著我,以過來人的口吻悄悄問:若夕啊,你是不是……
我不能確定,但沒有否認,如果我懷孕能讓一位老人幸福,哪怕是暫時的,為什麼要去剝奪呢?
從母親家出來,瀚遠陪我去了醫院,檢查結果是我沒懷孕,醫生亦找不到病症,隻好心地安慰我們,可能是眼下流行的都市病——亞健康,注意勞逸結合和補些營養就可以了。
可是我在一天天憔悴下去,梳子上纏滿了脫發,甚至,輕輕一擼就能脫下一束,洗臉池裏漂著零散的眉毛,我不敢照鏡子,瀚遠瘋了一樣地帶我看遍本市的名醫,無濟於事。
我隻能休假,躲在家裏,看著頭發越來越稀、眉毛幾乎褪淨、傾聽死神慢慢逼來的腳步,除了手足無措就是絕望,原來,上帝給的幸福是有限度的,沒有人可以擁有全部。
俊輝常常來,在瀚遠的焦灼和我的絕望中擰著手指,用千篇一律一句話安慰我們:總會有辦法的。
一次,瀚遠瞪著牆角,一瞪就是半天,偶爾一聲暴響是他在焦躁中踢翻了東西,好象俊輝真的是不祥之人,我們正在遠離的幸福就是因為他的靠近。
俊輝默默地看著他,很受傷的樣子,悄無聲息地離開,像遁失在黑夜中的悲哀老貓,許多天後,他興衝衝拿來一些粉末說:這些天我尋了許多偏方,不妨試試。說完,迫不及待地讓瀚遠倒水,喂我吃。瀚遠將信將疑,還是照做了。
竟真的效果,吃了半個月後症狀漸漸減輕,瀚遠再看俊輝,眼裏就浮著一層溫和的感激。
不妙的是類似我的症狀,正在俊輝身上重演,而且發展迅速,他的頭發和眉毛大把大把地落下來,他不肯去看醫生,我吃的偏方,在他身上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和瀚遠傻了。
5,謝幕的絕唱
俊輝病倒後一直住在瀚遠家,或許是以恩報德,瀚遠請假在家照顧俊輝,男人之間可以如此親昵,是我從沒見過的,瀚遠總是握著他的手,一開口就別過頭,大顆的眼淚順著青蒼的臉頰滾下來。
俊輝最後的日子,總在不停地睡,醒著的時候,亦是精神恍惚,語言喃喃,誰都聽不清他說了些什麼,瘦得像一片落葉,在冬天的空氣中單薄而脆弱,步履蹣跚如初學走路的嬰兒,他沒有絲毫的恐慌,很安詳,陽光很好時,讓瀚遠背到陽台享受太陽。
當春天的陽光普照大地,俊輝的生命已走到了尾聲,在一個黃昏,他帶著微微有點不安說:若夕,幫我買套婚紗好麼?
我驚詫,想問為什麼,看著他眼裏充滿疲憊的哀求,不忍再問,便跑到街上。
拿婚紗回家,瀚遠正在給俊輝化妝,撲粉底,畫眉,擦口紅,我說:瀚遠……
回過頭來的瀚遠淚流滿麵,俊輝努力地追著他的目光看過來,帶著羞澀的笑說:真羨慕你們的幸福,我……
俊輝穿上婚紗,一臉心願滿足之後的安詳,睡在瀚遠懷裏,美好的晨曦再也不能喚醒他。
送他去火化場時,我拿出瀚遠母親送我們的那對戒指,把女款那枚套在他左手的無名指上。
瀚遠默默地看著我,眼淚大顆大顆地落下來,最後一刻,我懂了那麼多,瀚遠母親的種種眼神,她希望我用愛情救贖她的兒子;俊輝所謂的失戀不過是因為瀚遠愛上了我,而他,對瀚遠的愛,即將被棄。
俊輝是愛瀚遠的,我出現之前,他們在一起。
回來之後,瀚遠說:若夕,知道我追你的目的嗎?
我搖頭。
為了騙我母親或者說給她一個安慰,因為你不漂亮,隻想把你當作一個遮人耳目的幌子而根本不會愛上你,是我和俊輝商量好的,可是,你偏偏讓我碰了你的身體,我不是故意卻愛上了你,我要和你在一起,和俊輝提出了分手。
我周身綿軟無力: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都不是故意,卻導致了俊輝不再求生……
俊輝是自殺,慢性自殺,知道我愛上你之後,他曾想不知不覺殺死你,但是,他眼見我因你痛苦而痛苦,還有你天真淳樸,他不忍了,他選擇了殺死自己,他送你蒸汽麵罩,又在美容水裏放了鉈鹽,一種無色無味的化學毒藥,讓你慢慢中毒,如果不做專項鉈鹽化驗,任何高超的醫生都查不出病因,他把剩下鉈鹽一天一點自己吃了,他給你的偏方,其實是他加工過的硫代硫酸鈉和普魯士蘭,專用來解鉈鹽毒的……他臨終前告訴我的,讓我替他求得你的原諒。
我不恨俊輝,即使知道他和瀚遠的故事,亦不曾厭惡,隻是,心裏升起軟軟的疼,無邊無際,愛情有很多張臉,有些,不必等到謝幕就預知了絕望,比如瀚遠和俊輝,在鄙夷的冷眼旁觀裏,注定無從救贖。
瀚遠說:原諒我曾騙你,你可以鄙視也可以離開我……
我看著他,心如浮萍,飄蕩在海的中央,找不到要去的方向。
木耳要父親活著,因為他要去天堂尋找小櫻桃,那裏有藍天白雲,她可以在他的掌上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