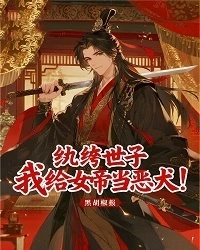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9章
福源貨棧外,已是一片人間煉獄。
火光衝天,將半個夜空映得猩紅。
灼熱的氣浪夾雜著木料燃燒的劈啪聲和房梁坍塌的轟鳴,如同一頭失控的巨獸,吞噬著周圍的一切。
濃煙滾滾,嗆得人睜不開眼,百姓的驚叫聲、衙役的嗬斥聲、水桶潑灑的嘶嘶聲混雜在一起,亂成了一鍋沸騰的粥。
左都禦史張承一張老臉在火光映照下,鐵青得如同鍋底。
他渾身都在發抖,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極致的憤怒。
他猛地轉身,一把揪住剛剛從馬車上下來的徐恪的衣領,唾沫星子幾乎噴到對方臉上。
“徐恪!這就是你說的證據?”他聲嘶力竭地咆哮道,“如今一把火燒得幹幹淨淨,死無對證!你擅動職權,引發如此大亂,本官必將據實彈劾!彈劾你!”
趙恪和陸時也麵露絕望之色。
千辛萬苦,步步為營,好不容易才鎖定的線索,竟在最後關頭,化作了眼前這片無法挽回的灰燼。
所有的努力,似乎都隨著這衝天的火光,付之一炬。
然而,就在這片混亂與指責的風暴中心,被張承揪著衣領的徐恪,卻異常的平靜。
他甚至沒有去看張承那張因憤怒而扭曲的臉,隻是抬起頭,靜靜地凝視著眼前那片滔天的火海。
那雙因病而略顯黯淡的眸子裏,沒有半分絕望,反而是一種冰冷到可怕的專注。
他那孱弱的身體在火光的映照下,非但沒有被吞噬,反而挺得筆直,一股掌控一切的無形氣場,竟從他身上油然而生。
“放手。”
徐恪的聲音很輕,卻像一盆冰水,澆在了張承的怒火上。
張承下意識地鬆開了手。
徐恪旁若無人地整理了一下被抓皺的衣領,隨即,一連串冷靜到可怕的命令,通過他身後那兩位已經徹底鎮住的下屬,如同一把把精準的手術刀,瞬間剖開了眼前這片混亂的局麵。
“陸時!”
“卑職在!”
“帶你的人,以貨棧為中心,五十步為界,立刻拉起警戒線!”徐恪的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壓過了所有的嘈雜,“許進不許出!所有參與救火的人員,無論官民,全部記錄在案!”
陸時那雙冰冷的眸子裏閃過一絲訝異,但他沒有半分猶豫,猛地一抱拳:“遵命!”隨即轉身,帶著鳳駕親軍,如一道黑色的鐵壁,瞬間將混亂的現場切割開來。
“趙恪!”
“屬下在!”趙恪像一頭找到了主心骨的猛虎,雙目赤紅。
“命令救火隊,放棄已經燒起來的外圍!集中所有水力,給我保住後院西側的賬房和東側的主庫房!”徐恪的指令匪夷所思,“其他地方,讓它燒!”
“什麼?”趙恪大驚失生,“大人,這......”
“執行命令!”徐恪的聲音陡然轉冷。
“是!”趙恪不再多問,轉身嘶吼著傳達命令去了。
張承和一眾言官看得目瞪口呆。
他們發現徐恪根本不是在救火,他是在進行某種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的儀式。
徐恪的命令還在繼續。
“所有從火場裏逃出來的夥計、管事,一個不留,全部給我控製起來!分開看管,不許交談!”
“是!”
最後,他將一名親信緹騎叫到身邊,用隻有兩人能聽見的聲音飛快地吩咐:“還記得我之前讓你們盯的那幾個點嗎?去查所有通往下水道的井口,還有南邊那條臭水溝。有任何動靜,立刻回報。”
這一係列操作行雲流水,不過短短幾十息,原本混亂不堪的火場,竟奇跡般地恢複了秩序。
所有人都像上了發條的零件,在他那無聲的指揮下,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
張承呆呆地看著眼前的一幕,看著那個裹著狐裘、在寒風中咳得仿佛隨時會倒下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產生了真正的恐懼。
這不是一個酷吏,這是一個怪物。
一個能將災難現場,都變成自己棋盤的怪物。
半個時辰後,火勢漸小,隻剩下殘垣斷壁在黑煙中苟延殘喘。
現場一片狼藉,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焦糊味。
徐恪緩緩走到臉色煞白如紙的張承麵前,平靜地開口:“張大人,您剛才說,死無對證?”
他隨手從地上撿起一塊被燒得焦黑、尚有餘溫的木炭,遞到張承眼前。
“您錯了。”
“這場火,就是最好的證據。”
張承的瞳孔猛地一縮。
徐恪的嘴角勾起一抹蒼白的弧度,那笑容裏帶著一絲智商碾壓的憐憫:“請教大人,我大周律例,‘縱火毀證’,該當何罪?”
不等張承回答,他便自問自答,聲音陡然拔高,字字誅心!
“若非心中有鬼,這福源貨棧為何要在官府上門之際,燃起這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大火?”
“他們想銷毀的,恰恰就是我們想尋找的!這場火燒掉的是有形的兵器,卻點燃了燕王謀逆這個無形的罪名!”
這番話,如同一柄無形的重錘,狠狠砸在張承的心坎上。
他張了張嘴,卻發現自己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因為徐恪說的,是法理,是邏輯,是他這個都察院禦史窮其一生都在維護的東西!
就在此時,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
陸時麵無表情地走了過來,身後押著一個渾身濕透、散發著惡臭、如同爛泥般的人影。
那人衣衫被汙水浸透,頭發上還掛著不知名的穢物,正是從秘道逃跑的貨棧管事。
“大人,人抓到了。”陸時的聲音平穩如常,仿佛隻是抓了隻耗子。
徐恪看了一眼那個已經徹底失去反抗意誌的階下囚,然後緩緩轉過頭,看向麵如死灰的張承,露出一絲和善的微笑。
“張大人,現在,我們人證物證俱在了。”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無比誠懇。
“這案子,您看,該如何向陛下彙報?”
張承看著眼前的一切,看著那個笑得人畜無害的病弱少年,知道自己已經徹底沒有了退路。
他被徐恪用一種他根本無法反抗的方式,牢牢地綁在了這艘即將撞向燕王的賊船上。
......
深夜,丞相府。
書房內,燈火通明。
王德庸正拿著一把小巧的銀剪,一絲不苟地修剪著一盆名貴的君子蘭。
一名心腹匆匆來報,將城南大火、懸鏡司封鎖現場、福源貨棧管事被擒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這位權傾朝野的老人。
王德庸聽著彙報,手中的動作沒有絲毫停頓,仿佛在聽一段與己無關的市井傳聞。
直到聽到最後,他手中的剪刀“哢嚓”一聲,竟失手剪斷了一支含苞待放的嬌嫩花蕾。
他沉默了片刻,緩緩放下剪刀,那雙渾濁的老眼中,閃過一絲與年齡不符的狠厲。
“這條瘋狗,不僅咬人,還會放火了......”
他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口浮沫,語氣平淡得像是在吩咐下人打掃庭院。
“去,告訴燕王府的人,就說火已經燒起來了,讓他們自己想好怎麼跟陛下解釋。”
“另外,”他頓了頓,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讓都察院的人準備好彈劾徐恪擾亂京城治安的奏章,天一亮,就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