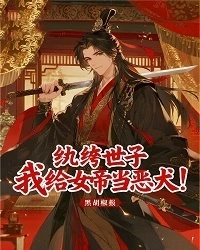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8章
審訊室外,空氣凝重得仿佛能用刀切開。
“錢先生”那句顫抖的招供,如同投入死水潭的巨石,激起的漣漪尚未平息,便被一道無形的牆壁死死擋住。
徐恪手持那份剛剛記錄下來的口供,聲音因虛弱而帶著一絲飄忽:“趙千戶,立刻點齊人馬,查抄福源貨棧!”
“我看誰敢!”
一聲厲喝,如平地驚雷。
左都禦史張承手持律法文書,一步跨出,身後十幾名言官如同聞到血腥味的鯊魚,瞬間將徐恪等人圍了起來。
張承的臉上沒有半分驚懼,反而是一種抓到把柄後的義正辭嚴:“徐指揮使!你瘋了嗎?此乃孤證!僅憑一個階下囚為求活命的片麵之詞,你就要帶人衝擊一處民間貨棧?萬一撲空,打草驚蛇,讓真正的逆黨有了防備,這個責任,你擔得起嗎?”
他將手中的《大周律疏》拍得啪啪作響,聲音擲地有聲:“在沒有其他佐證之前,你和懸鏡司,不得擅自行動!”
“你!”趙恪勃然大怒,繡春刀“嗆啷”一聲出鞘半寸,滔天的煞氣瞬間彌漫開來。
“怎麼?懸鏡司要公然抗法嗎?”張承不退反進,身後的一眾年輕禦史更是個個昂首挺胸,準備好了用唾沫星子淹死這群鷹犬。
陸時那隻沒有受傷的手也緩緩按在了刀柄上,眉頭緊鎖。
他知道張承說的是對的,按照律法,這的確是孤證。
可他也知道,敵人隨時可能轉移軍械,戰機稍縱即逝。
整個懸鏡司,被“程序”這兩個字,死死地困在了原地。
就在這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關頭,徐恪卻忽然低聲笑了起來。
他笑得太厲害,引發了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咳得整個人都蜷縮了起來,仿佛隨時會斷氣。
“大人!”趙恪焦急萬分。
徐恪好不容易緩過氣,擺了擺手,示意趙恪收刀。
他抬起那張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的臉,竟對著張承露出了一個無比讚同的微笑。
“張大人言之有理,是本官心急了。”
這出人意料的服軟,讓張承和所有人都愣住了。
徐恪裹緊了身上的狐裘,仿佛剛才那個殺伐果斷的指揮使隻是幻覺。他用一種商量的語氣,真誠地說道:“既然如此,案情陷入僵局,我等在此幹耗著也不是辦法。不如請張大人移步,我們去公房一邊喝茶,一邊梳理一下現有線索,看看能否找到新的突破口?您是前輩,還望不吝賜教。”
張承看著眼前這個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病秧子,心中警鈴大作。但他找不到任何拒絕的理由,隻能冷哼一聲,拂袖道:“哼,但願你不是在拖延時間。帶路!”
懸鏡司一間臨時征用的公房內,茶香嫋嫋。
徐恪與張承等人對坐,氣氛依舊冰冷。
表麵上,徐恪正拿著一份無關緊要的卷宗,與張承討論著昨夜“消防稽查”中某個更夫的口供細節,顯得胸無良策,一籌莫展。
張承嘴角噙著一絲冷笑,心中愈發篤定,這徐恪不過是黔驢技窮,想用這種方式消磨時間罷了。
然而,他沒有注意到,徐恪的另一隻手,在桌案下,正用一種極快且隱蔽的手勢,對著身旁的親信下達著指令。
“趙千戶,卷宗有些亂,你來整理一下。”徐恪頭也不抬地說道。
趙恪立刻會意,上前一步,裝模作樣地拿起一卷文書。徐恪的聲音壓得極低,快得像是在說夢話:“去,立刻查一下福源貨棧附近,最近三天,有沒有什麼地痞鬧事、商販爭鬥的記錄,無論多小,我都要。”
“是。”趙恪領命,轉身快步離去。
片刻後,徐恪又皺了皺眉,對一直如標槍般矗立在身後的陸時道:“陸都指揮使,我懷疑有同黨在監視我們,此地人手不足,勞煩你調派人手。”
陸時上前,徐恪用隻有兩人能聽見的聲音飛快地說:“派兩個最機靈的緹騎,換上便服,去城南最大的酒樓‘醉仙樓’,就說奉命尋找一個江洋大盜,把動靜鬧得越大越好,驚動的人越多越好。”
陸時那雙冰冷的眸子裏閃過一絲疑惑,但還是點了點頭,轉身離去。
緊接著,又一名親信被叫到身邊。
“去京兆府,就說懸鏡司懷疑有燕王逆黨餘孽混跡於南城市井,為防萬一,請他們立刻加派人手,對福源貨棧周邊三條街區,進行常規性的巡街盤查。”
一道道命令,瑣碎、零散,且毫無關聯。
張承等人聽得雲裏霧裏,隻覺得這徐恪是病急亂投醫,在做一些毫無意義的常規排查。
他們想阻止,卻找不到任何理由。
律法規定,懸鏡司本就有權在京城範圍內進行常規盤查。
他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在徐恪那看似漫不經心的指揮下,一張無形的、由無數細線編織而成的大網,正悄無聲息地朝著城南的福源貨棧,緩緩罩下。
公房內,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張承已經喝了三杯茶,心中的不耐煩幾乎要溢出來。
他正欲開口譏諷,公房的門卻被猛地撞開!
一名緹騎神色慌張地衝了進來,聲音不大不小,卻剛好讓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指揮使大人!不好了!京兆府的巡街衙役在福源貨畔外,與貨棧的夥計發生了激烈衝突!”
張承的眼皮猛地一跳。
那名緹騎喘著粗氣,繼續彙報道:“貨棧夥計不僅阻撓衙役的常規盤查,還出手打傷了兩名官差!現在雙方正持械對峙,場麵......場麵快要控製不住了!”
話音未落,徐恪“霍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他因動作過猛,引發了一陣劇烈的咳嗽,但那張蒼白的臉上,卻寫滿了“驚愕”與“凝重”。
他轉身對著張承,猛地一拱手,聲音裏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急切。
“張大人!您聽見了?”
“福源貨棧,竟敢公然抗拒官府盤查,甚至暴力抗法,其行徑何其囂張!此事,已非單純的懸案疑點,而是正在發生的、有損我大周朝廷威嚴的惡性事件!”
徐恪的目光灼灼地盯著張承,像一團燃燒的火焰。
“我等身為朝廷命官,食君之祿,豈能坐視這等狂徒在天子腳下撒野?本官懇請張大人與我一同前往現場,維持秩序,查明真相!”
他加重了語氣,每一個字都像一記重錘,狠狠砸在張承的心上。
“您是都察院禦史,代表的是朝廷法度,是天下清流!有您在場,方能彰顯此事的絕對公正!”
張承的臉色,在一瞬間變得煞白,毫無血色。
他瞬間明白了。
這是一個局!
一個為他量身定做的、讓他根本無從躲避的陽謀!
什麼衙役衝突,什麼暴力抗法,都是假的!
都是徐恪這個瘋子一手導演出來的戲!
可他能說這是假的嗎?
不能!
當著這麼多人的麵,一個“暴力抗法”的罪名,已經像一塊燒紅的烙鐵,死死地印在了福源貨棧的頭上。
他作為監察禦官,如果此刻拒絕前往,就是失職!
是瀆職!
是眼睜睜看著朝廷威嚴被踐踏而無動於衷!
這個罪名,他擔不起!
可如果他前往,就正中徐恪下懷!
他將從一個高高在上的“監視者”,徹底淪為徐恪此次行動的“同謀”和“擋箭牌”!
他被死死地釘在了職責和道義的十字架上,根本沒有第三個選擇。
他看著眼前這個病得仿佛下一秒就要咽氣的少年,後背卻竄起一股比三九寒冬還要刺骨的寒意。
在滿堂緹騎和自己下屬那灼熱目光的注視下,張承感覺自己的喉嚨幹得像要冒煙。
良久,他才從牙縫裏,擠出了兩個字。
“......同去!”
......
福源貨棧,後院。
一名管事模樣的中年男子,正聲嘶力竭地指揮著手下,將最後一批用油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連弩搬上馬車。
他剛剛收到了“錢先生”被捕的死信,心中焦急如焚。
“快!快!天黑之前必須出城!”
突然,貨棧外傳來一陣喧嘩聲和衙役的嗬斥聲。
“哪來的蒼蠅!”管事皺眉,以為隻是一般的市井麻煩,並未放在心上。
但當一名手下連滾帶爬地跑進來,報告說衙役被打傷,事情越鬧越大,甚至驚動了懸鏡司時,他心中警鈴大作。
太快了!
對方來得太快了!
這不是巧合!
他瞬間明白,自己已經落入了對方精心編織的羅網。
“不要管了!”他眼中閃過一絲瘋狂的決絕,對著身邊的死士厲聲下令,“放火!把所有東西連同這個貨棧,一起燒成灰!我們從秘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