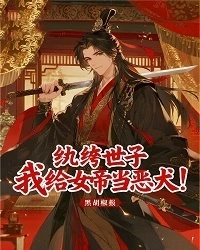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2章
徐恪的病房,如今已看不出半分療養之所的模樣,儼然成了一座高速運轉的臨時作戰室。
空氣中,濃重的藥味、陳年卷宗的黴味與新墨的清香混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令人神經緊繃的獨特氣息。
地麵上、桌案上、乃至窗台上,都堆滿了來自京城各大衙門的文書與戶籍冊,紙張多得連下腳的地方都快沒了。
“大人,全都在這兒了!”
北鎮撫司千戶趙恪頂著兩個碩大的黑眼圈,臉上卻帶著一種獵犬發現獵物蹤跡後的亢奮。
他指揮著幾名同樣一臉疲色的下屬,將最後一口沉重的木箱“哐當”一聲扔在地上,半人高的卷宗小山宣告建成。
“卑職動用了懸鏡司所有的人手,花了一天一夜,把京城裏有備案的兩百一十三家錢莊查了個底朝天!”趙恪抹了把臉上的汗,從那堆故紙山裏抽出三份整理得最整齊的卷宗,獻寶似的呈到徐恪麵前。
“我們排查出三家嫌疑最大的!‘恒通’錢莊,背後是安遠侯的影子,他家跟北疆常年有皮貨生意往來。‘裕豐’錢莊,掌櫃的是燕王妃的遠房表親。還有這家‘金源’,他們最大的幾筆放貸,都給了幾個與邊軍有聯係的糧商!”
趙恪的結論,是典型的懸鏡司辦案思維,直接、粗暴,順著最明顯的線索一杆子捅到底。
一旁如標槍般矗立的陸時,也拿起卷宗翻看了幾眼,冷峻的臉上露出一絲認同:“這三家,值得一查。”
然而,靠在床頭,臉色依舊蒼白得像宣紙的徐恪,卻連看都懶得看那三份卷宗一眼。
他隻是端起手邊溫熱的藥碗,吹了吹氣,然後問出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的問題。
“這些是‘最可疑’的,”他呷了口苦澀的藥汁,緩緩抬起眼皮,“那‘最不可疑’,或者說,賬麵上‘最幹淨’的是哪家?”
“啊?”
趙恪和陸時同時愣住了。
查案子,不查可疑的,反倒去查幹淨的?
這叫什麼路數?
這完全違背了他們浸淫了半輩子的辦案直覺。
“大人,您......您不是在說笑吧?”趙恪撓了撓頭,一臉費解。
徐恪將藥碗放下,看著眼前這兩個代表了大周軍、特最高水平的精英,忍不住在心裏歎了口氣。
他決定給自己的新團隊,上第一堂課。
“為藩王謀逆洗錢,是誅九族的買賣。”徐恪的聲音因虛弱而有些飄忽,但邏輯卻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精準地剖開了問題的核心,“如果你是主事者,你會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不等二人回答,他便自問自答:“是把自己變得‘最不像’。所以,任何與北疆、與軍方有明顯業務往來的錢莊,都可以第一個排除。那些都是擺在明麵上的靶子,是用來吸引我們這種人的障眼法。”
趙恪和陸時臉上的表情,從不解,慢慢轉為了凝重。
“真正的幽靈,不會在白天活動。”徐恪的眼中閃爍著一種洞悉人性的微光,“這種錢莊,必然有幾個‘反常’的特征。你們記一下。”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它的流水一定非常巨大,但從不張揚,甚至會刻意製造虧損的假象來掩人耳目。一個真正悶聲發大財的賭徒,絕不會到處炫耀自己的牌技。”
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它的安保力量,會和它的業務規模嚴重不匹配。你想想,一個賬麵上常年半死不活的‘小’錢莊,卻雇傭著能進大內當差的一流高手當護衛。這正常嗎?這說明,它保護的不是錢,是比錢更重要的秘密。”
最後,徐恪伸出了第三根手指,輕輕敲了敲床沿。
“第三,它的地理位置,一定極便於撤離和銷毀證據。比如,臨近穿城而過的水道,或者有多條不為人知的暗道。一旦出事,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人間蒸發。”
一番話,讓整個房間落針可聞。
趙恪和陸時呆呆地看著徐恪,感覺自己的腦子像是被一柄重錘狠狠砸了一下。
他們第一次知道,原來查案還能這麼查,不看線索,看“行為模式”。
“趙恪,”徐恪下達了新的指令,語氣不容置疑,“別管他們的生意夥伴是誰,也別管掌櫃的是誰的親戚。現在,重新篩選!”
“我隻要符合這三點——‘低調、高流水、強安保、易逃遁’的錢莊。一家一家地給我過!”
趙恪的額角瞬間滲出了冷汗,他猛地一抱拳,聲音洪亮地應道:“是!”
這一次,他再無半分疑慮,轉身帶著人,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重新撲進了那座信息的海洋。
半個時辰後,當趙恪滿頭大汗地再次衝進來時,他手中的卷宗,隻剩下了一份。
“大人......找到了。”他的聲音都在發顫,既是累的,也是興奮的,“四海錢莊。這家錢莊名不見經傳,開在城南最偏僻的巷子裏,賬麵常年微利,有時候還虧損。老板是個禮佛的富商,平日裏深居簡出,唯一的愛好就是聽戲。”
他喘了口氣,繼續道:“但我們查了它的流水,非常詭異!經常有大筆銀兩快進快出,賬麵上卻隻記一筆微不足道的‘過賬費’!而且,它明麵上的護衛隻有四個,可我們的人查到,這四個人,全是退役的邊軍斥候,手上都沾過血!”
最後,他指向京城地圖上的一點,聲音壓得極低:“最關鍵的是,它的後院,緊鄰著京城水龍會的一個站點。那下麵,是能通往護城河的排汙水道!”
所有特征,完美吻合!
就在目標被精準鎖定的瞬間,一名懸鏡司的密探神色慌張地從外麵衝了進來,單膝跪地,聲音嘶啞。
“大人!北疆密報!‘佛見愁’,三日前已秘密潛入京城,目前......下落不明!”
“佛見愁”三個字一出,連陸時那張冰山臉上都閃過了一絲凝重。
趙恪更是臉色大變:“北疆第一殺手!他來京城幹什麼?大人,此人必然是衝著您來的!必須立刻加強防衛!”
陸時也上前一步,沉聲道:“卑職讚同,我即刻調遣鳳駕親軍,將此地圍成鐵桶!”
所有人的神經都緊繃到了極點。
一個神出鬼沒的頂級刺客,就像一條潛伏在暗處的毒蛇,隨時可能發動致命一擊。
然而,就在這片緊張的氣氛中,徐恪卻猛地從床上坐直了身體,因動作過猛,牽動傷口,讓他劇烈地咳嗽起來。
他擺了擺手,製止了準備行動的陸時,眼中爆發出駭人的精光。
“不,你們都錯了!”
他看著滿臉驚愕的二人,一字一頓地拋出了那個石破天驚的結論。
“如果燕王要殺我,在我接手案子時就該動手了,何必等到現在?”
“‘佛見愁’不是來殺我的,他是來‘取東西’的!”
徐恪的目光瞬間變得銳利如鷹,死死地鎖定在地圖上“四海錢莊”的位置。
“一個能讓燕王動用他最強殺手的錢莊......裏麵藏的東西,恐怕比金山銀山還要重要!”
他瞬間將兩條看似毫不相幹的情報,用一條看不見的邏輯線死死地串聯了起來。
敵人也在行動!
而且,目標和他們是同一個!
原本一場按部就班的情報調查,瞬間演變成了一場與頂尖殺手爭奪時間的生死競速!
......
與此同時,京城南城,一間不起眼的茶館。
角落裏,一個麵容平凡、氣息沉靜的茶客,正用一塊幹淨的白布,不厭其煩地擦拭著一串烏黑的佛珠。
鄰桌的幾個潑皮無賴,本想尋釁滋事,可隻與他對視了一眼,便像是見了鬼一般,嚇得魂飛魄散,連滾帶爬地跑出了茶館。
一名夥計打扮的人,低著頭,恭敬地為他添上熱水,用隻有兩人能聽見的聲音,飛快地說道:“王爺密令。第一目標,四海錢莊後院井下的‘生死簿’,到手即毀。第二目標,懸鏡司指揮使徐恪,能殺則殺,作為掩護。時限,明晚子時之前。”
那擦拭佛珠的手指,微微停頓了一下。
“知道了。”
淡淡的兩個字,仿佛殺一個朝廷新貴,毀掉一本致命賬冊,對他而言,不過是出門買趟青菜一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