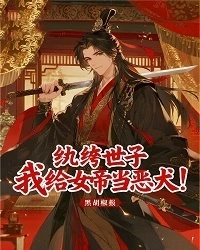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章
大周,天元十年。京城,大理寺詔獄。
最深處的水牢,連耗子都嫌棄。
齊膝深的汙水冰冷刺骨,混雜著鐵鏽、血腥與黴菌發酵後的惡臭,像是把人直接浸泡在腐爛的傷口裏。
徐恪被一道道沉重的鐵鏈鎖在十字木架上,頭無力地垂著。
高燒讓他的視野忽明忽暗,現代社畜的記憶與國公府紈絝子弟的人生走馬燈一樣在腦子裏亂撞,撞得他隻想當場去世。
原身是安國公府的三公子,一個純粹的廢物點心。可惜投胎技術再好,也頂不住全家點了一份“謀逆”的超級外賣。現在,這份外賣的賬單,算到了他這個唯一的幸存者頭上。
“吱嘎——”
沉重的鐵門被從外推開,一道光柱猛地刺破黑暗,照亮了懸浮在空氣中的塵埃。
光影中,一道身影緩步走入。
來人身著玄色龍紋常服,身姿挺拔,勾勒出驚心動魄的曲線。一張臉更是冠絕天下,美得不似凡人,隻是那雙鳳眸裏沒有半分溫度,像是淬了萬年寒冰,看過來時,如同在審視一塊待宰的死肉。
大周女帝,李青鸞。
她的身後,跟著提燈的宦官與披堅執銳的金甲衛士,冰冷的甲胄在幽暗中反射著森然的光。
徐恪費力地抬起眼皮。他知道,這位女帝陛下不是來噓寒問暖的。她隻是來確認,她最大的政敵——安國公滿門,最後一個男丁,在死前是何等絕望。
這是一場長達三年“削外戚”鬥爭的閉幕式,而他,就是那件用來剪彩的祭品。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一個尖細的嗓音在水牢中回蕩,是女帝身邊的老太監。
“罪臣徐恪,安國公府餘孽,性頑劣,行不端,附逆作亂,罪不容誅!今朕體上天好生之德,特賜其......淩遲之刑,於明日午時三刻,與安國公府九百七十三口同赴西市,以儆效尤!欽此!”
老太監收起明黃的卷軸,陰惻惻地笑了笑,仿佛已經看到了那血腥的場麵。
水牢裏死一般寂靜,隻有水滴從石壁上滑落的“滴答”聲。
李青鸞終於開了金口,聲音清冷如玉石相擊:“徐恪,你還有何話說?”
這不是詢問,是貓捉到老鼠後,優雅又殘忍的戲弄。
金甲衛士的手按在了刀柄上,似乎隻要徐恪敢說一句咒罵之詞,就會立刻讓他血濺當場。
徐恪的喉嚨幹得像要冒煙,他舔了舔幹裂的嘴唇,用盡全身力氣,擠出一句沙啞卻異常清晰的話。
“陛下,您殺我,如同親手折斷一把最鋒利的刀。”
他頓了頓,扯出一個虛弱的微笑。
“可惜了。”
一句話,讓整個水牢的空氣都凝固了。
老太監的笑容僵在臉上,衛士們也愣住了。他們預想了求饒,預想了咒罵,唯獨沒預想過這個。
李青鸞那雙古井無波的鳳眸裏,終於泛起了一絲漣漪。
是好奇。
“哦?”她向前走了兩步,裙擺在汙水上拖開細微的波紋,“一把刀?你這把刀,連握筆都嫌重,朕看是鈍刀一把,不堪一用。”
“鈍與不鈍,要看用在何處。”徐恪的聲音順暢了些,思路在死亡的刺激下變得無比清晰,“陛下,安國公府倒了,朝堂就幹淨了嗎?”
他不等女帝回答,自顧自地說了下去。
“不,恰恰相反。隻是空出了一個更大的食槽,引來了一群更餓的狼。”
李青鸞的瞳孔微微一縮。
這話,正中靶心。
徐恪繼續道:“您削平了外戚,可那些盤根錯節的文官集團,那些坐觀虎鬥的世家勳貴,還有那些遠在封地、虎視眈眈的藩王......他們現在一定很高興。他們在等著分食安國公府留下的政治遺產,等著把手伸進兵部和戶部,等著看您這個女帝,如何麵對一個更加混亂、更加難以掌控的朝局。”
“放肆!”老太監厲聲嗬斥,“竟敢揣度聖意!”
李青鸞卻抬了抬手,製止了他。她饒有興致地看著木架上的囚犯,問道:“依你之見,朕該如何?”
“陛下需要一把刀。”徐恪眼中閃過一絲精光,“一把不屬於朝堂任何派係,沒有過去,更沒有未來的刀。一把隻聽從您命令,替您去咬人、去做臟活的‘惡犬’。”
“這把刀,滿朝文武,沒人能當。丞相要顧及門生故舊,禦史大夫要愛惜羽毛清名,那些國公侯爺,更是人人屁股底下都有一攤屎。”
“隻有我。”徐恪笑了,盡管那笑容比哭還難看,“一個家族死絕、聲名狼藉、明日就要被千刀萬剮的廢人,最合適不過。”
他喘了口氣,將自己穿越前做谘詢時忽悠甲方的本事全使了出來,把自己的每一個汙點,都包裝成了獨一無二的優點。
“我是個紈絝,所以我知道京城裏哪個勳貴子弟鬥雞走狗,哪個衙內私開賭局,他們的臟事我門兒清。”
“我出自國公府,所以我明白他們是如何結黨營私,如何將田產銀兩轉到親族門下,手法我一清二楚。”
“我......更是個將死之人。”徐恪直視著女帝那雙深不見底的眼睛,“所以我無所畏懼。爛命一條,陛下給我第二次,我就能用它去咬下任何人的喉嚨,包括我自己。”
水牢裏,再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李青聊天生多疑,她不信忠誠,隻信價值。
眼前這個階下囚,一番話,精準地剖析了她的困境,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一個用後即焚的工具人。
用一個必死之人,去整頓那些她早就想動卻找不到合適下手機會的貪官汙吏。成功了,她收獲一把快刀,朝堂為之一清;失敗了,她不過損失一個囚犯,還能順藤摸瓜,把他失敗時牽扯出的勢力一並清洗。
這筆買賣,一本萬利。
許久,李青鸞的紅唇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她緩緩抬手,從腰間解下一塊通體漆黑、雕刻著猙獰異獸的玄鐵令牌,隨手一扔。
“噗通。”
令牌落入徐恪腳下的汙水中,濺起一圈漣漪。
“這是懸鏡司的指揮使令牌。”
女帝的聲音不帶一絲感情,像是在宣布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朕給你三天時間。”
“三天後,朕要看到戶部侍郎周文淵貪墨軍餉的鐵證,以及......他的人頭。”
“辦得到,你活。辦不到,西市的剮刑台上,朕會為你留個好位置。”
說完,她再也不看徐恪一眼,轉身拂袖而去。
沉重的鐵門再次關閉,光線消失,水牢重歸黑暗與死寂。
隻剩下徐恪,和他腳下汙水裏那塊冰冷的玄鐵令牌。
他活下來了。
暫時。
徐恪低頭看著那塊令牌,忍不住在心裏爆了句粗口。
三天,查一個戶部侍郎?還是鐵證加人頭?
這哪裏是投名狀,這分明是催命符!
這開局,真是刺激他媽給刺激開門,刺激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