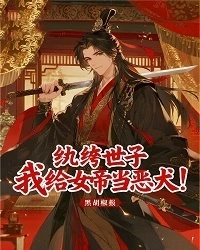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2章
女帝的腳步聲消失在悠長的甬道盡頭,沉重的鐵門“哐當”一聲合攏,水牢重歸死寂。
徐恪依然被鎖在木架上,高燒帶來的眩暈感和刺骨的汙水讓他感覺自己像一塊被泡發了的爛木頭。
然而,水牢裏的氣氛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先前那些視他為死物的獄卒,此刻正從鐵柵欄外探頭探腦,目光裏混雜著驚疑、恐懼,以及一絲不易察覺的貪婪。
他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但他們看清了女帝扔下的那塊玄鐵令牌。
那是懸鏡司的信物,是京城裏能讓小兒止啼的凶器。
沒過多久,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大理寺卿錢庸帶著兩名心腹,親自趕到了水牢。
這位掌管京城刑獄的一品大員,此刻臉上掛著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徐......公子,”錢庸隔著柵欄,小心翼翼地拱了拱手,“陛下她......可還有別的吩咐?”
徐恪費力地抬起眼皮,看著這位官場老油條,心裏跟明鏡似的。
女帝隻給了令牌,沒給“出獄”的口諭。
這老狐狸是既怕得罪女帝的新貴,又怕壞了朝廷的規矩,特地來探口風的。
“開鎖。”徐恪的聲音沙啞,卻不容置疑。
錢庸臉上的肥肉抽動了一下,為難道:“公子,這......沒有陛下的旨意,擅放重犯,下官擔待不起啊。要不,您再等等,興許陛下的口諭已經在路上了。”
一個完美的官僚主義軟釘子。
不頂撞,不拒絕,就是拖著。
徐恪差點氣笑了。
跟這幫人講道理,就是對牛彈琴。
他沒有大喊大叫,隻是平靜地看著錢庸,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大人,陛下給我三天時間辦案。現在,時辰已經開始算了。”
他頓了頓,虛弱地咳嗽了兩聲,眼神卻銳利如刀。
“你在這裏耽誤的每一刻,都是在浪費陛下的時間。這個責任,你確定要為此負責嗎?”
錢庸的額頭瞬間滲出了一層細密的冷汗。
徐恪的目光轉向他身後,悠悠道:“或者,錢大人想現在派人快馬追上陛下的鑾駕,當著滿朝文武的麵,問一句‘陛下,您是不是忘了說一句話’?”
這番話如同一記重錘,狠狠砸在錢庸的心坎上。
責任轉嫁,信息不對稱。
他不敢賭,賭輸了,女帝會覺得他是在質疑聖意,是個辦事不力的蠢貨。
“開鎖!快給徐公子開鎖!”錢庸猛地回頭,對著身後的獄卒厲聲咆哮,仿佛剛才那個猶豫的人不是他,“一群沒眼力見的東西,還不快請徐公子出來!”
冰冷的鐵鏈被一一解開,當徐恪從汙水中被攙扶出來時,雙腿已經麻木得失去了知覺。
半個時辰後,一輛不起眼的黑色馬車停在了皇城北側的一座衙門前。
徐恪換上了一身幹淨但並不合身的飛魚服,那是懸鏡司的製式官袍。
高燒未退,他的臉色依舊蒼白,但眼神卻前所未有的清明。
他抬頭看向眼前這座建築。
通體由黑石砌成,屋脊上蹲著的不是尋常瑞獸,而是兩尊呲牙咧嘴的獬豸,仿佛要將天地間一切不公與罪惡都生吞活剝。
空氣中,似乎都彌漫著一股若有若無的陳年血腥味。
懸鏡司,到了。
門口站崗的兩名緹騎,看到一個身形單薄、臉色蒼白、走路還有些虛浮的“少年”從馬車上下來,眼神裏毫不掩飾地流露出輕蔑和不屑。
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又一個靠關係空降下來的膏粱子弟。
徐恪對此視若無睹,徑直走進了那扇仿佛巨獸之口的大門。
懸鏡司指揮大廳內,氣氛森嚴。
所有在京的百戶、千戶都已聞訊趕來,分列兩旁。
他們個個身形剽悍,眼神銳利,腰間的繡春刀柄被摩挲得鋥亮,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股子血與火淬煉出的煞氣。
為首一人,身材魁梧如鐵塔,一道猙獰的刀疤從左眉一直延伸到嘴角,讓他本就凶惡的麵相更添三分戾氣。
懸鏡司北鎮撫司千戶,趙恪,人稱“活閻王”。
他代表眾人,懶洋洋地一抱拳,皮笑肉不笑地開口:“卑職見過徐......大人。不知大人前來我懸鏡司,所為何事啊?”
他故意在“大人”二字上加了重音,卻絕口不提“指揮使”,言語間的試探與挑釁,毫不掩飾。
其餘的緹騎們紛紛抱起雙臂,嘴角噙著冷笑,一副等著看好戲的模樣。
他們不信,一個從天牢裏撈出來的乳臭未幹的罪犯,能領導他們這群在刀口上舔血的虎狼。
徐恪的目光掃過眾人,沒有理會趙恪的態度,直接從懷中掏出那塊玄鐵令牌,“啪”地一聲拍在正中的帥案上。
“奉陛下口諭,查辦戶部侍郎周文淵。”他的聲音因發燒而有些嘶啞,卻清晰地傳遍了整個大廳,“趙千戶,把周文淵的所有卷宗、暗探記錄,一刻鐘內,全部搬到我的簽押房。”
開門見山,沒有半句廢話。
趙恪臉上的假笑一僵,顯然沒料到對方的路數如此直接。但他早有準備,微微躬身,滴水不漏地答道:“回大人,周侍郎乃朝廷二品大員,他的卷宗乃我司最高機密。按懸鏡司的規矩,需指揮使本人、並有司禮監掌印太監的批紅,方可調閱。您這......隻是臨時奉命,恐怕,不合規矩。”
話音一落,大廳裏響起幾聲壓抑不住的嗤笑。
這是要把徐恪架在“規矩”兩個字上,用官僚體係的銅牆鐵壁,讓他變成一個光杆司令,寸步難行。
徐恪笑了。
他環視眾人,目光從一張張或輕蔑、或看戲、或冷漠的臉上掃過,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
“規矩?”
他拿起桌上的令牌,在指尖掂了掂。
“陛下的命令,就是最大的規矩。我們的目標,不是遵守你們那些發黴的舊規矩,而是在三天之內,把周文淵的腦袋,幹幹淨淨地送到陛下麵前。各位,聽懂了嗎?”
這是第一步,重新定義目標。
用皇權壓製內部規則。
不等眾人反應,他繼續拋出重磅炸彈。
“我再宣布一條臨時規矩,隻在此案生效。”徐恪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查抄周文淵所得家產,除去按例上繳國庫的部分,剩餘的,我做主,拿出一成,作為此案所有出力兄弟的賞錢!”
“一成賞錢”!
這四個字如同一塊巨石砸入平靜的池塘,整個大廳瞬間死寂,緊接著便響起一片粗重的呼吸聲!
所有緹騎的眼睛都紅了。
他們幹的是掉腦袋的臟活,拿的卻是朝廷的死俸祿。
這套“按功分賞”、“績效獎金”的說法,他們聞所未聞,但那赤裸裸的金錢誘惑,卻是致命的!
“誰的功勞大,誰拿的就多!”徐恪加重了語氣,“從現在起,我會設一本功勞簿,誰提供了關鍵線索,誰第一個衝進周府,誰在審訊中撬開了關鍵人犯的嘴,一樁樁一件件,我都會記得清清楚楚。案子辦完,當著所有人的麵,按功勞簿兌換成白花花的銀子!”
這是第二步,引入利益驅動。將任務目標與個人收益強行綁定。
那些原本抱著臂膀看戲的百戶們,眼神瞬間就變了,從看戲變成了炙熱,甚至有人已經開始摩拳擦掌,盤算著自己手下有幾個擅長追蹤的好手。
徐恪的目光最後落在了臉色鐵青的趙恪身上。
“當然,誰要是覺得規矩比賞錢重要,比陛下的命令重要,可以現在站出來。我也不為難你,你大可以繼續抱著你的規矩過日子。”
他話鋒一轉,聲音陡然變冷。
“查案拿賞錢的事,就讓想幹、敢幹的兄弟們來幹!”
“哦,對了,”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麼,對著趙恪微微一笑,“趙千戶,你如果在一刻鐘內,拿不來卷宗。我就默認你對這個案子不感興趣,這潑天的頭功和賞錢,我就隻能交給李百戶、王百戶他們去分了。”
這是第三步,製造內部矛盾,用鯰魚效應打破平衡。
趙恪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
他能清晰地感覺到,身後那些下屬的目光已經變了。
那不再是看戲,而是催促,是警告,是餓狼看到肥肉時,對擋路者的敵意。
他建立起來的威信和秩序,在對方這套簡單粗暴的“目標+金錢+競爭”的組合拳下,已經搖搖欲墜。
他知道,如果自己再敢說一個“不”字,不用這個病秧子指揮使動手,他手下這幫為了錢能把親爹賣了的虎狼,就能先把他給撕了。
這個看似孱弱的少年,手段遠比他見過的任何一個上司都更狠、更直接。
他不跟你講資曆,不跟你論規矩,他直擊人心最深處的貪婪。
最終,在十幾道灼熱目光的注視下,趙恪從牙縫裏擠出了幾個字。
他緩緩低下那顆高傲的頭顱,沉聲道:“卑職......遵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