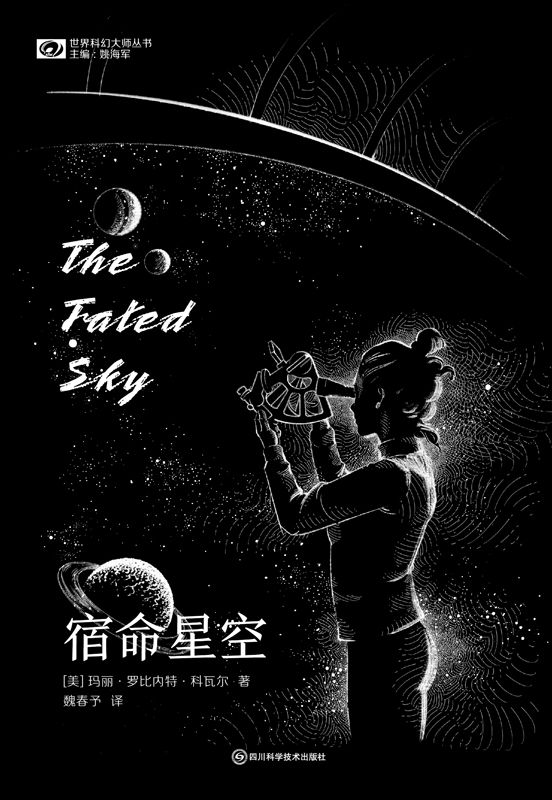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六章
意大利遭受熱浪襲擊
美聯社意大利羅馬1961年9月4日電 羅馬正在遭受意大利七十年來最嚴重的熱浪和幹旱,當地將實行供水配給製度。至少已有二十一人因高溫和隨之而來的風暴喪生,其中不乏在求生途中溺亡的人。
昨天,局部雷暴給部分高溫地區帶來了喘息的機會,但羅馬沒有。雷電造成數人和數十頭農畜死亡,並引發多起火災。羅馬自來水公司宣布了輪流配給計劃,這將導致每家每戶下周有近一天時間無法用水。
克萊蒙斯瞪著地板,脖子上的肉堆在衣領上,變成了烏紅色。他果斷地點點頭,轉身從辦公桌上抓起雪茄和雜誌,“用我的電話吧。”
“我去她家,然後——”
“拜托。”他的懇求讓我震驚,陷入沉默。克萊蒙斯把雜誌轉過來,讓我看清封麵。《時代周刊》上有一幅巨大的由藝術家創作的火星,上麵隻有一個詞:為什麼? “如果你決定不去,我需要立馬知道,因為我將舉全局之力來避免計劃流產。”
我咽了口唾沫,點點頭,但我不會打退堂鼓。他一離開房間,我就拿起他的電話,打到海倫家。我手裏繞著電話線,靠著他的辦公桌,沒坐在他的椅子上。我的分寸感有時很奇怪。
電話響了三聲,海倫才接起來。“卡穆奇家,我是海倫·卡穆奇。”
“嗨……我是埃爾瑪。”電話那頭一陣沉默,我趁此機會清了清嗓子。靜電輕微的劈啪聲回答了各種問題。“我剛剛發現他們把你調走了……但克萊蒙斯說你同意了?你……這樣真的可以嗎?”
“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雷納德在一起。”
“但你一直非常努力啊。”我靜靜地等待著,給她回應的時間,隻有她微弱的呼吸聲讓我知道電話還沒斷。“我告訴克萊蒙斯,除非你能接受被調走,否則我不會同意的。”
“是的,當然,埃爾瑪。我允許你去。”海倫一激動,她的亞洲口音又出現了。她生氣時的口音,就像大西洋中部地區貴族的口音。現在,我正和處於憤怒中的凱瑟琳·赫本1說話。
“聽著——如果你不樂意,我就退出。我是說,我已經告訴他這一點了。”
“看在上帝的分兒上!我告訴過你了,我沒問題。我允許你去。你要我說我很高興?我不高興。你是我的朋友,但你不能為了讓自己好受些要求我撒謊。”
“我——我很抱歉。我不是這個意——我會告訴他我不去了。”
“那就等於白白犧牲。”海倫歎了口氣,聲音裏流露出些許怒氣,“所有報紙上都是你的消息。如果你退出計劃,把事情鬧得沸沸揚揚,那將使人們不再支持這個計劃。我能理解這種情況,但對此我並不‘樂意’。”
“我們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我確信——隻要指出你參與訓練的時間,以及你比我更有資格的事實。”
“現實一點兒,這不是訓練的問題。”從她的話裏,我感受到了羅伊和地球至上主義者的影子,“我知道此刻我身處美國,是航天事業中的一員。如果我默默接受,他們會把我放在第二波飛船上。如果我回絕呢?他就會找借口讓我永久禁飛,直接把我換掉。我當然要選擇答應,甚至還要笑著答應。這是唯一明智的選擇。”
“那我們就好好利用我顯然無比重要這件事……我會告訴克萊蒙斯,除非你去,不然我不去。”
話音未落,我就知道這個想法不切實際——我們都知道船上的限額——但海倫替我說了出來。從她的吸氣聲中,我聽出了她的不屑。“他們不能再增加一名隊員,因為那會增加額外的資源和重量。”
“可是——”我停了下來,不知該怎麼回答。一定有辦法的。
“他們會換掉其他人,所以謝謝你,但是不必了。我不想成為把別人踢出任務的人。那樣的話,隊伍裏就會有兩個招人恨的人。”
她的話十分沉重,把我的頭壓到了胸口。“我很抱歉。”
“我知道。”這三個字包含了海倫太多情緒。我知道你很後悔。我知道你不想讓我責怪你。我知道什麼都不會改變。“我會等的。這不公平,但至少是一個慣用策略。”
而這……隻會讓我覺得更惡心。
等我再次回答“去”以後,仿佛整個IAC的宣傳部門都進入了超負荷的工作狀態。也許是他們早已計劃好了這一切,也許是雜誌的緣故。是各種雜誌。因為《時代周刊》那篇並不是唯一的負麵報道。在月球上,由於沒有人定期投遞報紙,民眾對太空計劃的抵製在我們看來並不嚴重。
不管是什麼原因,等兩個星期後,我回過神來時,已經身在洛杉磯,和斯泰森·帕克一起站在《今夜秀》2的後台了。
我在酒店房間裏吃了一片眠爾通,正對著牆壁背誦斐波那契數列,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至少現在我不會再吐了。通常來說。
1、1、2、3、5、8、13、21、34、55、89、144……
我身後,帕克繞著小圈子踱步,不停地抖手,似乎想讓血液流回指尖。一個拿著記事板的助手站在我們身邊等待,他的一隻耳朵上戴著一個巨大的耳機,仿佛他身處任務控製中心。
……233、377、610、987、1597、2584、4181、6765……
拿著記事板的人靠向我,低聲地說:“該你們上了。”
舞台上,傑克·帕爾3說:“歡迎我的下一批客人,斯泰森·帕克上校和埃爾瑪·約克博士。”
我轉過牆角,恰好看到帕克露出他那和藹可親的笑容。他示意我帶路,“女士優先。”
我臉上露出僵硬而脆弱的假笑。襯裙擦著我的腿擺動,我走進了燈光中,掌聲撲麵而來。禮堂裏,在一排排燈光和攝像機背後,坐著活生生的人們。除開他們,還有數百萬人坐在電視機前。
……10946、17711、28657……
帕爾先生和我握手,然後和帕克握手,我們經曆了必要的向觀眾微笑和揮手的環節,然後我們坐在他旁邊的配套皮椅上。一個銀色的麥克風立在我和帕克之間的地板上,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交叉雙腿,以防我的鞋撞上它。
傑克·帕爾拽了拽脖子上的招牌領帶,朝我們靠過來,仿佛房間裏隻有我們幾個人。“非常感謝兩位的加入。我告訴你們,我覺得自己一直停留在五歲的狀態。我知道這是明知故問,但……你們倆都去過月球了?”
帕克笑了。他真的很會笑。“我也難以相信。有時候我都想掐自己一把。”
“還有,約克博士……你住在月球上,是嗎?”
“是的,一年中我大約會在月球聚居地住六個月的時間。”
“那一定很有意思。”傑克·帕爾靠得更近了,他笑得像個孩子一樣,既興奮又透露著不安,“月球生活是什麼樣的?”
“比你想象的更像地球。我駕駛著其中一艘運輸船,運送地質學家和礦工到各個地點。我有一條固定的路線,所以和公交車司機沒什麼區別,真的。”
帕克在我身邊笑著說:“別聽約克博士謙虛。因為月球質量瘤4的緣故,駕駛這種船非常考驗技術。”
傑克·帕爾的眉毛幾乎抬到了發際線上,“質量牛?那是個背鍋的吉祥物嗎?”
謝天謝地,盡管這是個拙劣的笑話,但他還是把我逗笑了,否則我會對帕克的恭維目瞪口呆。“質量瘤是質量密集區的簡稱。月球上有局部重力異常區,那裏的岩石密度較大,會導致飛船意外下沉。”
“等等——月球上真的有重力比較大的地方?”
我點了點頭,“地球上也有,但影響很輕微,你很難注意到。這也是飛船無法自動繞月的原因之一,對於一台小到能安裝在飛船上的機械計算機來說,這之中的數學計算太複雜了。”我這麼說不是因為有人想聽關於數學的事。我的工作是頌揚火星計劃的優點,“但月球聚居地確實讓我們瞥見了火星聚居地的藍圖。這和早期美國人在邊境生活的感覺差不多。”
“月球聚居地上真的有一個藝術博物館嗎?”
“是的。”我笑得更燦爛了,感覺皮膚都要裂開了,“雖然展廳總共也隻有一米半長。移民者創造了一個小小的旋轉展區,擺放著雕塑、紡織品和繪畫作品。”
帕克露出了沾沾自喜的笑容,“是真的。每次去月球我都喜歡在那兒停留。它讓我意識到,人類能在星際間茁壯成長。人類最鮮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擁有藝術創造的激情。”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火星能怎樣激發藝術家的靈感。”還能再裝腔作勢點兒嗎?但這就是他們要我做的事。我的胃隨著我的每一次微笑而抽搐,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因為焦慮,還因為我被他們利用的方式。
“現在,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問一個更嚴肅的問題。約克博士,在你返回地球的途中,你的飛船被一群恐怖分子劫持了。當時情況是怎樣的?”
“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隻是一群出去打獵的人,他們……”他們用槍指著我。“他們擔心被留在地球上。”
帕克插話了,他的手肘撐著膝蓋,身體前傾,手指緊緊地貼在一起,像一個正在思考的拉比,“這就是我喜歡我們在IAC的工作的原因。我們進太空是為了給其他人鋪平道路。拓荒時代,你做夢都想不到用篷車帶奶奶橫穿全國,但現在呢?她可以去任何地方。太空也是這個道理。”
“沒錯。為了奶奶們,我們要讓太空安全起來。”我這樣胡言亂語的時候,很難看出我有物理學和數學的博士學位。但也許這是個機會,可以直接和羅伊這樣害怕自己會被拋棄的人對話。“這需要整個團隊的努力。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為太空計劃努力。例如,海倫·卡穆奇是導算師——導航計算師——她本身是亞裔。是她想出了辦法讓大家安全離開‘天鵝座14號’。”
“而你就是那個辦法的執行者。”帕克的笑容令人眼花繚亂,“你能和我們一起去火星,我們感到非常幸運。”
混蛋。
“哦,我隻是一個更大團隊中的一員。我們有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卡米拉·沙蒙和來自西班牙的埃斯特萬·泰魯紮斯,還有來自巴西的拉斐爾·阿維利諾……隻是舉幾個例子。”我想對著攝像機,直接向可能正蹲在某個監獄的羅伊呼籲,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不是隻有白人。我們所有人都在一起努力。而說出口的卻是:“這就像空中世界博覽會一樣。”
這讓觀眾們笑了起來。耶。對我來說太棒了。帕克和他們一起笑了起來,並朝傑克·帕爾靠了過去,“當然,每個去的人都一專多能。”
傑克·帕爾眉毛一挑,“哦,那你的專長是什麼?”
“任務指揮官。但我同時也是個飛行員和語言學家。”帕克朝我猛地豎起一根大拇指,“約克博士是物理學家、計算師和飛行員。她是個三麵手。她要是會下棋就好了,那她就堪稱全能了。”
我臉上保持著微笑,也跟著他們笑了起來。因為,當然了,海倫會下棋。我不會。
我們完成《今夜秀》後,我真應該回酒店繼續學習,但我怎麼能離我哥這麼近卻不去看望一下呢?出租車把我和帕克送到酒店的時候,赫舍爾和湯米已經一起在大廳裏的一張豪華天鵝絨沙發上等著了。與我們在猶太新年會麵時相比,我哥哥並沒有太大變化,但湯米似乎長高了一英尺。我想這就是十六歲和十七歲的區別。他的臉仍孩子般柔軟,但下巴卻有著和我父親一樣堅挺的線條。
我侄子跳了起來,滿臉小狗一般的笑容。赫舍爾還在擺弄他的拐杖,他已經穿過房間抱住了我。
“埃爾瑪姑媽!”湯米太熱情了,搖得我朝後退了一步。求你了,上帝,保佑我心愛的孩子永遠不會失去快樂。
我心愛的孩子。想到我的身體可能無法再孕育出孩子,有那麼一瞬間,這種想法幾乎蒙蔽了我的雙眼,我緊緊地抱住湯米,狂熱得超出必要。
“嘿,小夥子。”我鬆開他轉向帕克,轉身時,他已經停下了腳步。“請允許我介紹——”
“天!你是斯泰森·帕克!”
帕克露出了他那謙遜的笑容,“是的,我是。”他朝湯米伸出手,他們一對一地握了握手。“你一定是湯米。”
我可真是大吃一驚。據我所知,我從來沒有和他討論過我的——不,我有。死亡模擬。所有宇航員都參加過研討課,討論萬一我們在月球任務中犧牲了該怎麼辦。我們已經非常詳細地討論過要聯係誰,以及聯係的順序。所以帕克知道湯米,就像我知道他的雙胞胎男孩叫埃爾默和沃森一樣。
“是的,先生,我是。”湯米還在和帕克握手,但他的胸脯卻挺拔了三倍,他以為我提起過他。
赫舍爾搖搖晃晃地走向我們,腿部支架發出輕微的哢嗒聲,“湯米,我想帕克上校肯定還有事情要做。”
“唉,是的。”帕克收回手,露出一個逼真的苦笑,“我相信你也很想和你的姑姑在一起。”
有一個從小兒麻痹症中幸存下來的哥哥,令我注意到一些事。帕克沒有看向赫舍爾的拐杖,也沒有低頭看他的支架。大多數人都會看,然後他們會做出痛苦的表情。帕克,盡管他有很多缺點,但他給了我哥哥一份視他為常人的禮物。
帕克向湯米眨了眨眼,像最強美國英雄5一樣,從我們身邊走開了。他轉過頭笑著喊道:“別讓她熬得太晚——她有作業,明天她還要上課。”
混蛋。說得沒錯,但沒必要說。我回到湯米和赫舍爾身邊,“要不要去餐廳?我快餓死了。”我也想喝一杯。謝天謝地,餐廳保持著好萊塢的營業時間。
“聽起來不錯。”赫舍爾在我旁邊晃晃悠悠地走向大廳一側的領位台,“艾斯特姑媽向你問好,還有多麗絲。”
“媽媽不能來,因為瑞秋被禁足了。”湯米搖了搖頭,試圖裝出一副成年人的嚴肅模樣,“她在抽煙。”
“什麼?!”我十三歲的侄女在抽煙?
“湯米。”赫舍爾皺著眉頭從鏡框上沿看向他的兒子,“你不該提起這事兒。”
“隻告訴埃爾瑪姑媽。”
赫舍爾清了清嗓子,“我不知道你妹妹會不會同意。”
我們在餐廳找地方坐,我那一連串問題沒問出口。我無法想象我侄女抽煙的樣子。她才十三歲!不,十四歲。但還是無法想象。天啊……我們出發去火星的時候,她就十五歲了……等我回家的時候,她就已經十八歲了。湯米已經上大學了。
“埃爾瑪——”赫舍爾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怎麼了?”
“嗯?”我眨著眼睛回過神來,眼睛一陣刺痛,“隻是度過了漫長的一天。”
他瞟了一眼我的侄子。我不知道我該不該慶幸湯米在這裏,這樣一來,赫舍爾就不能問我一些尖銳的問題,也不會因為我不能把一切都告訴他而感到失望。但是,真的,有什麼好說的呢?納撒尼爾和我不會有孩子,所有人都不會對這個決定感到意外。更不用說哥哥了。
赫舍爾在口袋裏摸了摸,“看樣子他們有點唱機。湯米……不如給我們選首歌?”
我的侄子像兔子一樣敏捷,一把抓過硬幣,出了包間。赫舍爾立刻回過頭來,對我說:“咋回事兒?”
我歎了口氣,搖了搖頭,“你太了解我了。”
“我知道你在拖延時間。他很快就會回來的。”
“我剛剛意識到,我不在的期間,他們會長大好幾歲。”我聳聳肩,轉了轉桌上的水杯,“我之前沒算過。”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你說你沒算過。”
我對他吐了吐舌頭。我是個成年人了。顯然。“還不到三年,他們已經長這麼大了,我已經夠煩的了。還有瑞秋是怎麼回事?”
他轉頭瞥了一眼湯米,湯米顯然正在看點唱機裏每首歌的詳情。“他知道的不多。瑞秋在抽大麻。”
“你之前居然沒告訴我?”
“就是昨天的事兒。”他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梁,“有那麼個男孩,我沒殺他。”
“我來。”
他笑著說:“那你得搶在多麗絲前麵才行。總之,他是個高年級的學生,顯然長得挺帥,他有一輛車。他在樂隊練習後載她回家。”
我渾身發冷,“她沒——我是說……”
“沒有,所以他才活著。”音樂響起,赫舍爾回頭看了看,“時間到了。隻要記住,你離開期間,瑞秋可能會被一直禁足。”
我點了點頭,咽下了惡心的感覺,湯米隨著音樂的節奏蹦蹦跳跳地走了回來。他選的是《六十分鐘的男子》。我恨這首歌。
1 好萊塢六十餘年間極具影響力的女演員,一生致力於促進婦女權利。
2 《今夜秀》是NBC於1954年創辦的一台晚間談話、綜藝類節目,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強檔節目。
3 傑克·帕爾(Jack Paar,1918—2004),美國作家,廣播和電視喜劇演員,脫口秀節目主持人。
4 即月球上的質量密集區,是月球的重力異常區。
5 美國電視劇《最強美國英雄》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