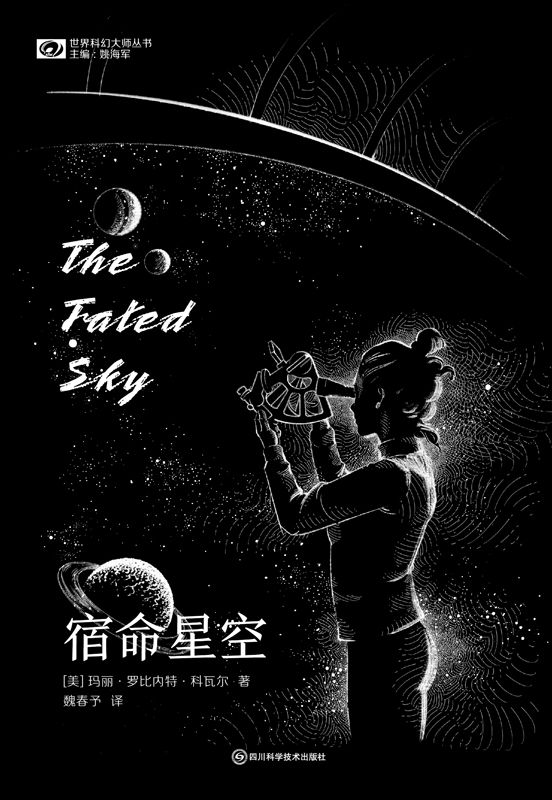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因操作失誤或機械故障 “天鵝座14號”偏離航線
堪薩斯州堪薩斯城1961年8月20日電(記者史蒂文·李·邁爾斯) 今日,一艘搭載著宇航員的“天鵝座”級宇宙飛船從IAC的“盧內塔”空間站返回地球。官方宣稱,下降過程中可能發生了技術故障或操作失誤,飛船最終降落在距原定降落地點二百六十英裏1遠的位置。雖然該飛船是太空項目早期飛船的變體,但是今日著陸的是一艘新版本的飛船,這是它的首次航行,使用了改進過的火箭和控製係統,旨在降低飛船下降和落地時的難度。
我的胳膊如有千鈞。似乎還有匹挽馬壓在我的胸口上,用蹄子狂踢著我。我努力撐開沉重的眼皮,想看看為什麼沒人把馬趕走,卻隻看到了灰蒙蒙的一片。這兒不是月球,不是……椅子在我麵前。我呻吟著轉頭,但胃裏突然一緊,一陣惡心,於是停下了動作。
一定是在某個時刻重力太大,我承受不住暈了過去。我不知道船長是怎麼讓火箭著陸的——當然,我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但看上去,我們竟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我的心臟仍舊劇烈地跳動著。雖然,在地球的重力環境下,這頭壓在胸口的挽馬不過就是我的體重罷了;但三個月來,這是我頭一遭感受到自己在地球上的體重。空氣中散發著嘔吐物和尿液的臭味。我慢慢地轉頭,檢查生命維持係統的遙測麵板。在地球環境中,麵板上的各項數值都很正常。但在有人打開艙門之前,我們都得待在這個密封罐頭中,還得遵守安全操作規範。
接著,我又轉頭去查看海倫的狀況。不出意料,她仍舊昏迷未醒,但看上去並未受傷。
我閉上眼睛,用嘴緩慢地控製呼吸,等待救援小隊登船。他們花的時間長得超乎尋常。話說回來,我並不知道我們落地有多久了,也不知道救援小隊有沒有遇到其他狀況。或許飛船的著陸輪著火了,誰知道呢?
終於,我意識到艙口有敲擊聲。有點兒尷尬的是,救援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艙門肯定是被卡住了。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南方人,我忍不住想要起身幫忙。可經年的航天航空訓練讓我第一時間想起了安全規範。
是否有煙味?沒有。氧氣含量如何?正常。是否受傷?我沒有,海倫沒有……我睜開眼,在座位上小心翼翼地轉頭查看船艙中的情況。乘客或是臉色蒼白,或是麵帶菜色,但似乎沒人受重傷。過道對麵是一位有著鷹鉤鼻的黑人男性,他是火星項目團隊中的一名地質學家,叫什麼來著?他正好迎上了我的目光,“我們要不要幫著開門?”
我不敢搖晃腦袋,隻回答道:“他們有工具。我們很安全,所以讓他們幹該幹的活兒吧。”
他點點頭,突然臉色發青,狠狠咽了口唾沫。我同情地往後縮了縮。當重力環境改變時,突然的頭部運動就會令人犯惡心。
對,他叫萊納德·弗蘭納裏。在海倫和雷納德的婚禮上,我和他曾愉快地聊起過盧瓦爾河穀。我在戰爭時期曾駕駛飛機來往於彼地,卻從未品嘗過那兒的美酒。他對此深感震驚。
伴隨著氣壓變化的噝噝聲,艙門打開了,證明我待著不動的選擇再正確不過。T-38追蹤機2的轟鳴聲從遠處傳來,響徹船艙。陽光和新鮮的空氣猛地灌進來,還混雜著橡膠燒焦的味道和生土的氣息。這些氣味之下,還有新割青草的氣味。我又閉上了眼睛。該死的,我才不要因為綠植流淚。
“都別動!”槍的扳機被扣下,發出金屬撞擊的聲音。
我不由得猛地睜開了眼睛。六個穿迷彩服的男人擠在艙門口,舉著來複槍對著我們。這些人中有黑人,有白人,還有膚色介於二者間的。他們臉上戴著各式麵具,其中一人戴著悍匪頭套,將自己捂得嚴嚴實實的,隻能看出他是個黑人。另一個古銅色皮膚的人用頭巾裹著臉,像是漫畫書中的土匪。第三個人戴著防毒麵具。其他人則戴著建築工地用的防塵麵罩。
IAC的安保人員怎麼會放過這些戴著——噢!等等……追蹤機還在上空盤旋。雖然不知道船長被迫降落在了哪裏,但我猜,這裏應該不是堪薩斯州。我的日常經驗和學到的安全規範,可都不足以應對這種狀況。
海倫在我身邊發出一聲呻吟。
“嘿!閉嘴!”戴悍匪頭套的男人操著濃重的布魯克林口音喊道。他帶著槍,衝過走道,舉槍對著海倫。
她猛地抬起頭,立馬吐了出來。由於太空生活的經驗頗為豐富,她轉頭避開了我。但膽汁還是濺到了她的大腿上。這場景隨即引起船艙另外一邊的人接連幹嘔。
我咬緊牙關,狠狠地咽了口唾沫。誰能想到,多年來應對由焦慮引發的嘔吐的經驗,會在這種時候派上用場?在重力和壓力的雙重作用下,我的心臟沉重地跳動著。來自布魯克林的男人舉著槍,什麼地方有聲音,就瞄向什麼地方。麵具後的棕色眼睛裏充滿緊張和憤怒的神色。“這都是……他們都怎麼了?”
我身後又傳來了作嘔的聲音。另一個男人大聲喊道:“別摘下麵具!你肯定不想被傳染吧!”
“太空病菌。”
或許不合時宜,但我還是禁不住“哈”一聲笑了。笑聲在船艙中回蕩,我成了焦點。但是,認真的嗎?太空病菌?聽起來像是廣播劇中才會出現的玩意兒。
“你覺得好笑嗎?”布魯克林男人逼近我,用槍抵著我的太陽穴。冰冷的金屬管壓著我的皮膚,抵住頭骨。“你覺得毒害地球是好笑的事嗎?”
“別,兄弟。別這麼做。”萊納德企圖掙脫安全帶,“你知道這樣會帶來什麼後果。別——”
“閉嘴。”布魯克林男人舉起槍指著萊納德,“湯姆叔叔3,我可沒心思聽你說話。在我們想要解決的麻煩中,你也算一份。”
“嘿!”戴著防毒麵具的男人以軍人特有的姿態大步向前,槍口微微向下。雖然隔著防毒麵具的過濾器,但他教官般的聲音在船裏回蕩,“他們有沒有病不重要,時間來不及了。我們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所以——該死的,你是那個宇航員夫人。”
我遇見過很多次粉絲,卻從未料到會在這種節骨眼上遇到。但不管怎麼說,這倒是讓我有了幾分計較。我知道該如何和粉絲交流。雖然槍管還抵著我的太陽穴,但我還是對著戴防毒麵具的男人露出一個笑容來。防毒麵具的護目鏡下 ,是雙淡褐色的眸子,其中一隻眼中有黑色的眼翳。“你肯定是‘巫師先生’的忠實觀眾吧。”
“我女兒很喜歡那節目。”他的眼睛裏流露出柔和的神色,但隻有片刻,很快他就搖搖頭,繃緊了雙肩,“不重要。不過……”他用上臂撞了下布魯克林口音的男人,“她可以。公眾會關注她。”
“我們的目標不是領航員嗎?”
“這個嘛……該死的,但是我們現在能接觸到那些領航員嗎?駕駛艙還密封著呢。不過她可是個貨真價實的名人,國寶級的人物。他們會——”
遠處,警報聲突然響起,而且聲音越來越大。布魯克林口音的男人直起身,回頭盯著艙門,“操,來得真快。”
“不然你以為呢?蠢貨。”我的粉絲向我走來,抓住我的胳膊,連我肩上的安全帶都沒解開,就想把我從座位上拖起來。
“讓我來?”我小心地舉起雙手,讓他們能看清我手上的動作,“安全帶上的扣環很多。”
他咕噥一聲,向後退開,給我讓出空間。我的手指像灌了鉛一樣沉重,笨拙地摸索著解開安全肩帶。地球的重力像是要將我壓扁,安全帶仿佛重逾千鈞。不管在月球上我花了多少時間健身,回到地球上的第一周都像身處地獄。與此同時,警報聲離我們更近了。
萊納德在他的座位上說:“別找白人女性當你的人質。你知道這會讓局勢變得更糟糕。”
我的粉絲猶豫了一會兒,隨後搖搖頭,“我們要是用黑人作人質,他們根本不會放在心上。宇航員夫人呢?那才會引起他們的重視。”
當我解開第二根安全肩帶時,我的粉絲再次抓住我的胳膊,將我拽了起來。我承受的重量陡然增加,突然之間大腦轉不過來,不知該如何應對。我隻能倚在他身上,並用手抓住了前方座椅的靠背。機艙似乎在繞著我瘋狂打轉,我勉力支撐,吐出來似乎也是條路子。
“她——”海倫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她頓了頓,但謝天謝地,還好她接著說下去了,“她頭暈。如果你不想被吐一身的話,就把動作放慢點兒。”
我胃裏沒東西。在航天飛行之前,我都不會吃東西。但我還是緩了一陣,試著找回方向,“你想要我做什麼?”
“你站到艙口去,跟他們講我們的要求。”布魯克林男人將我推到走道上,我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搖搖晃晃地走著。
在我摔倒前,我的粉絲扶住了我,“我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這樣沒人會出事。”
“好的,沒問題。”我的呼吸逐漸粗重。至於其中原因,我不太確定。可能是筋疲力盡,可能是惴惴不安,又或兩者兼有。我倚靠著我的粉絲,和他一起向火箭艙門走去。
這時候,似乎所有乘客都醒了。曾幾何時,我認識宇航員團隊中的每一個人,但現在看到的這些人中,我大概隻認得一半,對這一半中某些人,還僅僅是有個模糊的印象。不過,我知道在關鍵時刻海倫、萊納德和馬洛夫都值得信賴。艙門邊上,工程部門的塞西爾·馬盧擺弄著安全肩帶,像是想要起身的樣子。魯比·唐納森紮著孩子氣的金發辮,不過,戰爭期間她可是戰地醫生。
在前麵的駕駛室中,領航員現在在做什麼呢?他們大概已經清醒過來,並試圖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至少他們肯定知道登上火箭的不是救援隊了。後方有個對講機,但沒有攝像頭。如果我是他們,現在一定在仔細聽,以獲得更多信息。同時,我還會將這些消息轉達給任務控製中心。
我清清嗓子,“那你們六個想讓我說些什麼?”
過道盡頭,布魯克林男人攔住我說:“告訴他們,地球上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沒把地球上的問題解決好,就別去管太空。”
我緩緩地點了點頭。他們是地球至上主義者,我早該想到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來自隕石襲擊重災區的難民。來自布魯克林的這個家夥,或許已經一無所有了。而且身為黑人,他隻能在布魯克林的廢墟中自生自滅。“好。但要讓我說這番話,並不需要所有人都在這兒……”
“你就喜歡逞英雄,是吧?”
“這是件好事。”救援車隊在艙門前停下了,車燈閃爍。車隊由一輛當地的救護車和三輛消防車組成,並不是國際航空航天聯盟的車。有一輛車側停著,我能看見車的側麵寫著“麥迪遜縣”。
“我們在哪兒?”
“亞拉巴馬州。”
“哦……好吧,IAC的人趕到這兒,是得花些時間。”就算追蹤機和雷達跟蹤器已經向IAC的人反饋了我們的位置,但行程總歸需要時間。“有些人不太舒服,為什麼不讓他們去救護車那兒呢?這樣……這樣太空病菌就會被隔離。”
他們中有個人向外麵看了一眼,縮回頭說道:“急救人員朝這邊兒來了。”
“攔住他們。”我的粉絲猛地一揚下巴,防毒麵具的儲氣罐跟著晃動起來。
門邊的男人深吸一口氣,將來複槍伸出艙門,朝空中開了一槍。槍聲在客艙內回蕩,震耳欲聾。他朝艙門外吼道:“別再往前了!”
布魯克林男人將我向前一推。他的大拇指掐進了我胳膊肘上方的肉裏。但我也隻有靠他抓著我的力量,才能站得直。
我的粉絲瞥了我一眼,“你去跟他們說,讓媒體到這兒來,還有總統,還有小馬丁·路德·金博士。”
“還有聯合國秘書長。”其中一個裹著頭巾的男人補充道。他是這群人中皮膚最黑的,竟然有一口英國口音。我認識些英國黑人,但我本以為地球至上主義者都是美國人。
“你們知道……知道這是不——”不可能的,但我意識到這麼說太過直接,改了口,“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的。”
英國人揚起眉毛說道:“救護車來得就很快。”
“救護車是當地的。”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學過數學和駕駛宇宙飛船,但對於綁架人質事件的了解,則全部來自電影。而且我敢肯定,《突然》4絕不是什麼好例子。這些人中,絕對沒有一個人會將玩具槍當作真槍。我也根本找不到機會用電擊槍電他們。見鬼,我連站都站不穩。穩住他們、乖乖合作是現在看起來最可行的方法,“我會跟他們講,但你們確實做好等待的準備了吧?”
英國人說:“輪不到你來跟我們講要做什麼。”
“我明白。我隻是想確定一下,你們是不是真的清楚情況。從堪薩斯到這兒,要坐五個小時的飛機。你們知道嗎?我隻是想說這個。”事實上隻需要兩小時,不過我想多些時間總是好的……我是說,雖然他們能將總統塞進一架T-38,在二十分鐘內把他弄到這兒來,可真這麼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轉過身對著門,眯起眼睛看著室外的陽光,“他們會問你們為什麼要見這些人。”
“可以等他們到了再聊,不是嗎?”我的粉絲指指艙門,“媒體、總統、金博士,還有聯合國秘書長。別的什麼也不準說。聽明白了嗎?”
布魯克林男人沿著過道衝了回來,用槍指著海倫,“以防萬一。”
現在還能支撐我的,除了腎上腺素,就是幾十年來掩飾焦慮的經驗了。我能感覺到,衣料之下的皮膚緊繃,膝蓋隨著快速的心跳打戰。不知怎麼地,我最終點了點頭,走向艙門。
我用手抵著門框。我想顯得自信些,但顫抖的手指削弱了我的氣勢。消防員站在消防車旁邊,顯然是在商量該怎麼辦。救護車司機打開了無線電廣播,正跟什麼人說話。有個消防員看見了我,輕輕地用肘部推了推另一個消防員。
為了能大聲喊出綁匪的要求,我深吸一口氣。未經過濾的空氣滿載著泥土、花粉和燃燒後燃料的氣味,激得我一陣咳嗽。我緊緊抓住門框,彎下腰去。彎腰倒不是因為咳嗽,僅僅是為了別暈過去。有人一手扶著我的胳膊,一手撫著我的背,支撐著我。
“你還好嗎?”我的粉絲把門框當作擋箭牌,蹲下身子。
我點點頭,隨即後悔不迭。我咬緊牙關,咽了口唾沫,等待這陣眩暈過去,“可以扶我站起來嗎?慢一點兒。”
他點點頭,防毒麵具隨之上下抖動。他扶我站直,一隻手仍抓著我的胳膊。他用那雙淡褐色的眸子盯著我,直到我小心翼翼地吸了口氣。在我咳嗽的時候,急救人員情急之下,又不自覺地走近了些。
我看向他。那是個二十出頭的白人青年,有一頭抹了發蠟的金色鬈發。“這些人想要媒體過來,還要和總統、聯合國秘書長、小馬丁·路德·金博士對話。”
“誰?”一個虎背熊腰、兩頰蒼白、長著雀斑的消防員從人群中走了出來,“他們想要什麼?”
我向一側瞥了一眼,我的粉絲搖搖頭道:“告訴他們,等總統到了,他們就知道了。”
就我對政府的認知而言,這意味著他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了。
過道另一側,布魯克林男人的槍仍舊指著海倫,我隻好重複了一遍剛剛的話。然後我向後退進陰影中,“我能坐下嗎?”
我以為他們會因滿腹怨氣而拒絕我,但我的粉絲將我帶回了座位。當我們走近布魯克林男人時,他壓低了槍口。海倫癱倒在地,仿佛那把槍是支撐她的架子。
盡管我隻想一屁股坐下,可不得不謹慎地慢慢來。我的粉絲在旁邊幫我,就像我是位老太太,而非人質。現在為了一點兒水,我願意花大價錢。我清了清嗓子,“我想我們或許能聊聊,等總統到了你們想讓我說些什麼。你們剛剛提到地球上的問題……”
我的粉絲和布魯克林男人交換了一下眼神,走到我身後又使了個眼色,或許在和其他綁匪合計。過道另一邊,萊納德向我們這邊傾著身子,聽我們談話。我在前麵的時候,他就已經解開了安全肩帶。
我的粉絲眯起眼睛打量著我。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發現,不過最終他點點頭道:“地球上的民眾被甩下了。所有的錢都投進了太空項目,而不是用在收拾流星帶來的爛攤子上。人們住在擁擠的公寓中。十年了,難民還不能返回家園,因為保險公司聲稱‘天意難違!’,還說政府部門正按需‘分配資源’。”他怒氣衝衝,雙眉倒豎,“就像我們看不到資源都被分配到哪兒去了,不知道是哪些人被無視了似的!”
我在航空航天部門待得太久了,和我共事的人都深知流星撞擊會對地球氣候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很容易便忘記了許多人有更為迫切的需求。“如果全球氣候繼續按照氣象學家所預測的那樣持續變暖,全人類都會遭殃。除非我們能在別的星球上建立新家園。這……太空項目正是為了地球上的人而啟動的。”
“得了吧。這種事兒我們見多了。太空屬於精英,其他人都會被放棄。”
我搖頭道:“不,事情不是這樣的。”
“看看你周圍!”
我照做了。我小心地轉頭,不讓自己更加不舒服。綁匪們沒聚在一起,有兩個站在客艙後方,三個在艙門處,這裏隻有我的粉絲和我。所有乘客的臉色都帶著幾分灰綠,我分辨不出是因為重力,還是因為眼下的狀況,可能兩者都有影響。海倫雙手交叉放在膝頭。她的臉上掛著一副下象棋或者做計算的時候才會有的凝重表情。萊納德的兩手夾在腋窩下,看著我們這邊,咬著下嘴唇。魯比·唐納森的右膝抖動著,而範德比爾特·德比則咬著大拇指上的皮。
“唔,我看大家都挺狼狽的。”
“再看看。這些人中,有幾個和我一樣?”
我看向走廊對麵的萊納德,他避開了我的眼光。我發誓,總有一天在這種事情上,我能反應得快些。這艘全是宇航員的火箭上,隻有一個黑人男性,一個亞裔女性,剩下的三十個都是白人。或者說是二十九個白人加一個猶太人。這要看你把我歸到哪一類了。“這麼說的話,倒也不能算錯……”
他舉起了手中的槍,“但你們還是要繼續太空項目。”
“太空項目才剛剛起步。”像《巴克·羅傑斯》5那樣的電視節目,給觀眾帶來太空生活豪華舒適的錯覺。事實並非如此。“你聽我說……我一年要在月球上住六個月。我們沒有自來水,睡在睡袋中,也沒酒可喝——”絕大多數時候沒有,畢竟,也沒有什麼好吃好喝的,“能吃的隻有罐頭食品。一個小小的失誤就能讓聚居地中的所有人喪生。現階段,隻有擁有某方麵專業技能的人才能前往太空。我猜,現在在船艙裏的人,不是碩士就是博士。”
我的粉絲俯下身,麵具後,他的眼睛裏流露出憤怒,“你以為黑人就沒有學位?”
走道另一邊的萊納德清了清嗓子,“顯然,我們中也有——”我的粉絲轉身麵向他,他打住了話頭。
防毒麵具一抖,我的粉絲哼了一聲,“讓我們聽聽你要說什麼,湯姆叔叔。”
萊納德翻了個白眼,“他們招人時要求的學曆,光憑努力可得不來。還需要錢和人脈。順便提一句,雖然你這麼做挺蠢的,但我認同你的出發點。”
宇宙飛船有個大問題,船艙是密封的。雖然艙門開著,可地球上的氣候悶熱潮濕,艙內空氣不怎麼流通。現在是八月,我們還身處南方。而且,還記得降落時許多人吐了一地嗎?
我們等了四個小時,氣溫升高,臭味漸濃。如果沒發生意外,此刻我們都已經漂浮在國際航空航天聯盟適應中心的水床上了。但現實中,我們被迫承受著地球的重力,在充滿了汙濁空氣和嘔吐物的悶熱房間中直直地坐著。
海倫伸出手來,把手放在我的腿上,然後她開始用食指輕敲。真是個聰明的女人。她敲的是摩斯電碼。我將手放在她的手上,我倆仿佛在互相安慰,其實我也在通過敲擊回複她。
在一串長長短短的敲擊中,她拚出了:
利用他們對病毒的恐懼。
我在她手上回敲,問她:
怎麼做?
我裝死。她停下,用眼角的餘光看了我一眼。你來說。
說來奇怪,我知道她“裝死”裝得可像了。在宇航員訓練中,有一門課程叫作“死亡模擬”。在課上,我們會模擬宇航員死亡的場景。通常情況下,抽到“死者”身份卡的宇航員隻是和其他人分開坐而已,但海倫真的會把她的“死亡場景”表演出來。在倒地死亡之前,她會發出令人驚恐的嘎嘎聲,又以極其詭異的姿勢蹣跚而行。
鬼知道這方法行不行得通,但總統不可能來這兒……如果他不來的話,誰也說不準這些人會做出什麼事來。我坐直身子,環顧四周,尋找我的粉絲。他叫羅伊。我是在那個布魯克林男人問他廁所在哪裏時聽到的。
羅伊可能是飛船上唯一一個稍稍覺得舒服點兒的人,因為他戴著防毒麵具。我舉起手,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奇跡中的奇跡,他徑直走了過來,“我一直在思考你們的目的,我有個提議。”
“那我真是要洗耳恭聽。”
海倫身體前傾,猛地甩頭,吐在了羅伊的鞋子上——這真能算得上我所見過的最英勇的行為之一。我們初回地球時,為了防止嘔吐而小心避免的所有動作,她在一瞬間做了個遍,而且動作標準極了。
羅伊跌跌撞撞地退開,撞在萊納德的椅子上。就算隔著防毒麵具,也能看出他的臉因厭惡而抽搐扭曲。
其他綁匪立刻警惕起來,雖然還沒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已舉起來複槍指著我們。海倫顫顫巍巍地抬起手,用沙啞的聲音說:“太空……”接著一陣咳嗽,“病菌。”
然後,她癱倒在我腿上。雖然我早有準備,但還是被嚇得不行,不由自主地朝後退去。我把手放在她的喉嚨上。她的脈搏跳得又快又猛。我抬頭看著羅伊,試圖讓他相信我:“她情況很糟。”
羅伊身後,萊納德前傾身子,說道:“如果一船的宇航員都死了,還有誰會聽你們說話?你覺得金博士會支持你們這麼幹?”
我的手還放在海倫的脖子處,我哀求道:“求你了,就算是為了表露些誠意,讓病情嚴重的人先下火箭吧。”
“你的意思是說,讓我們主動扔掉自己的籌碼?”
“讓生病的人得到他們現在急需的治療,顯示你們的同理心,對你們有好處。”然而他不為所動,態度絲毫沒有軟化。“我會留下做你們的傳話人。”
緊接著,通信部門的多恩·薩巴多斯幹嘔起來。這讓一個淺色皮膚、裹著頭巾的人驚惶失措。他衝著羅伊搖頭道,“要不算了吧……趁著我們還沒感染。”
羅伊戴著防毒麵具,十分安全。他朝自己的同夥一個個看過去。布魯克林男人雖然戴著悍匪頭套,但還是用手捂住了口鼻。他稍稍抬起手說道:“照她說的做吧。”
“好吧。”羅伊走到我身邊,抓住我的胳膊,“你得跟他們交代清楚情況。”
我將海倫從我腿上移開。跟模擬課程時一樣,她裝死裝得像模像樣,任由自己的一隻胳膊垂到地上。羅伊扶我站起來。一起身,又是一陣天旋地轉,周圍的景象黯淡下去。我抓到了什麼——我猜可能是椅背——等穩住身子,我才跌跌撞撞地踏上過道。
快到艙門的時候,我停了一下,轉身麵對羅伊道:“他們出來的時候,急救人員得接他們。大部分人都虛弱得站不起來了。”
那個英國人靠在門框上,端著來複槍。他抬起頭說:“讓他們兩個兩個地來?”
羅伊點點頭,“別逞英雄。”
我走向艙門,“我明白。”英國人伸出一隻手扶著我。太陽已經西沉,給世間萬物塗上了唯美的金暉,交替閃爍的紅藍兩色應急燈光突兀地閃爍著。更多的救護車到了,警車也增加了。綁匪想要的媒體也已到場。看上去,三家電視台和幾家廣播電台都已經架設好了機器。
當然,媒體和我們隔得不算近。軍隊繞著火箭拉起了一圈警戒線,媒體都在警戒線之外。當我踏出艙門,所有的槍都舉起來瞄準我。我咽了口唾沫,才開口說話:“他們願意放些宇航員出來,以示誠意。一次兩個。急救人員可以上前來接宇航員。”
話說完,他們就將我拖進了艙門。我雙腿一軟,摔倒在飛船的地板上。英國人抓著我,將我拽了起來。他動作太猛……好吧,我暈過去了。
等我醒來,這艘散發著嘔吐物臭氣的、陰森恐怖的飛船上,隻剩下我和綁匪。
1 英美製長度單位,1英裏約等於1.6093公裏。
2 追蹤機是一種在飛行中追蹤目標飛機、航天器或火箭的飛機,目的是進行實時觀察並拍攝目標飛行器的照片和視頻。
3 典出《湯姆叔叔的小屋》,含貶義,指對白人卑躬屈膝的黑人。
4 1954年上映的美國犯罪電影。
5 1939年環球影業製作的科幻係列電視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