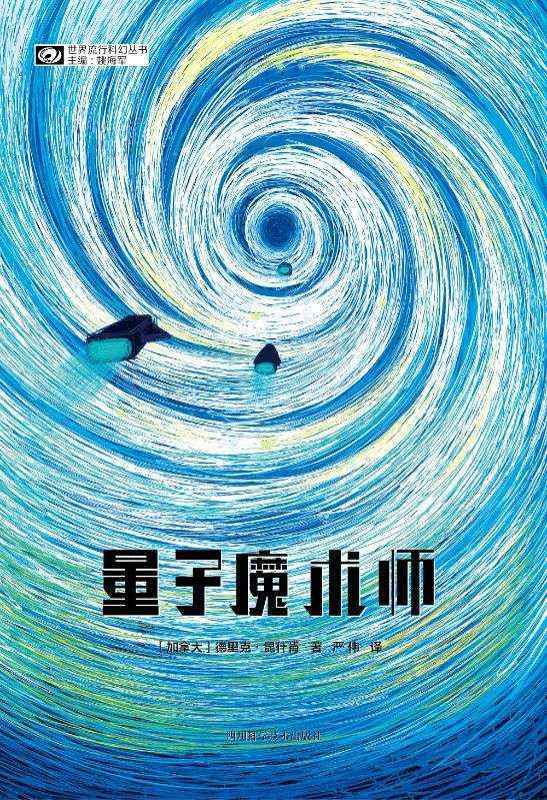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一
這世上的騙子很多,但是把自己的騙局跟量子世界作類比的,或許隻有貝利撒留·阿霍納個。當你考察頻率問題的時候,會發現電子似乎是一種波。而當你考察動量問題的時候,又會發現電子似乎是一種粒子。比如一樁房地產騙局,如果有黑幫的人想要插手分一杯羹,最後他一定會發現那個賣家原來過得很窮苦。再比如一場假拳賽,如果有哪個凱子想要下注賺上一票,到頭來他就會發現自己看好的拳手一碰就倒。大自然會給觀察者提供必要的線索,方便他把量子世界轉變成真實的事物。而貝利撒留也會給他的凱子們提供必要的線索,來引導他們把自己的貪婪轉變成代價高昂的錯誤。有時候,他得在槍口下這樣做。準確地說,伊夫林·鮑威爾這當兒正跟他說著話,膝上擱著一把手槍。
“幹嗎擺臭臉啊,阿霍納?”她問道。
“沒擺臭臉。”他陰鬱地回答。
“我會讓你發大財的。你再也不需要靠這個怪胎秀來混口飯吃了。”她一邊說,一邊誇張地揮舞著手。
這是一座釉磚砌成的大井,也是他的偶人(1)藝術展館。他們坐的地方是幽暗的井底。一根柱子直插在展館中央,支撐著旋轉樓梯和一級級平台。磚砌的壁龕中陳列著繪畫、雕塑和無聲電影展品。要欣賞它們,得隔著三米的距離看,那正是樓梯到牆壁之間的距離。貝利撒留正在籌劃一個偶人藝術博覽會,這種展會能得到偶人神權聯邦的批準,可是有史以來頭一遭。氣味、燈光和音響都會對偶人宗教體驗產生美學意義上的影響。展館入口高高在上,旁邊懸掛著一條鞭子,時不時地甩得劈啪作響。
“我喜歡偶人藝術。”他說。
“那等你有錢了就多買點兒。”
“蹲了大牢可就買不成藝術品了。”
“我們不會被抓到的,”她說,“別害怕。在這兒要是能成,在我的賭場就也能成。”
鮑威爾是來自巴塞羅那港的一位賭場老板,身材健碩。她穿越禁運區來到矮行星歐樂,就是為了親眼看一看:黑道上瘋傳的貝利撒留的那些神奇事跡到底是真是假。她用槍管輕敲著自己的膝蓋,貝利撒留的眼睛也不由得盯著槍口一起移動。
“但你沒完全跟我說實話,阿霍納。我還是不相信你真的黑進了一個福爾圖娜(2)A.I.。這事兒我知道有人試過,我也正花錢找人在試。而你,就憑自己一個人,待在這麼個地方,周圍隻有一圈偶人,可你竟然能做到——這種可能性有多大?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任憑她沉浸在自己的想法裏,她剛剛說出這個判斷一共呼吸了兩次,用時8.1秒。然後,他低垂目光,來迎合她的預期,也為自己多贏得了一秒鐘她的耐心。
“沒有人能黑進福爾圖娜A.I.,”他承認道,“我也沒做到。我破解的是安全程序移植過程,悄悄添進去一小段代碼。我不能放太多東西進去,不然A.I.的其餘部分就會注意到。但這個微小的改動可以在A.I.的統計期望計算中增加一個因子。”
鮑威爾盯著他,暗自思忖:這就是打敗福爾圖娜A.I.的秘密?這種可能性有多大?經過這番篡改移植之後,不堪一擊的賭場有多少?貝利撒留到底做了什麼改動,才破解了安全移植過程?
統計期望是福爾圖娜A.I.的核心。賭博過去曾是一種機會遊戲,賭場可以借此輕易掏光主顧們的口袋。但時至今日,科技已有了飛躍式的發展,從前那種日子早已一去不複返。借助技術進步,任何主顧都有可能在一家沒有安全保護的賭場作弊出老千。因此,一家賭場要想順利開張,就必須裝備一套福爾圖娜A.I.。隻要有一套先進的監測係統與之配合,A.I.就可以監視各種異動,包括超聲、光、無線電、紅外線、紫外線和X射線。它還能實時計算賠率和連勝次數。對於客戶而言,它是賭局公平的證明。對於賭場而言,它是防止有人出老千的保護手段。
“安全程序移植同樣是牢不可破的,”鮑威爾說,“我也找了人在試。”
“未必。隻要插入代碼的人動作足夠快,能夠在傳輸期間攔截補丁程序,並且做的改動也足夠小,那就可以做到。”貝利撒留說道。
如果按照鮑威爾的思路,福爾圖娜A.I.的確是“牢不可破”的。所有A.I.都是,因為它們已經發展成熟。它們隻能演化,或者通過小型程序移植來打補丁。
鮑威爾考慮了一會兒貝利撒留的說法。
“我的人接近成功了,但是我們還沒找到一個係統去測試,”她說,“利用體溫的確是天才的想法。”
展館高處,鞭子聲再度響起。隨之響起的是一聲錄製好的、傳達出宗教狂喜的偶人的呻吟。
“我的人說你非常聰明,”她說,“他們說你是個量人(3)。是真的嗎?”
“你的線人消息很靈通。”他說。
“那麼,一位超級聰明的量人,跑到這個文明最破落的地方來幹嗎?”
“量人要看到量子事物,得吃藥。那藥我吃了反應很大。”他說,“所以我被開除了。銀行不想為一個廢物付錢。”
“哈!”她說道,“廢物。我懂了。操蛋的銀行。”
貝利撒留擅長說謊。他有完美的記憶力,而且每個量人都必須能夠同時運行多條思考線。大多數時候,哪一條是真實的並不重要,隻要這些思考線沒有混在一起就沒問題。
“我們開工吧。”他最後說道,指了指她手心裏的藥丸。
“你肯定不會給你的新搭檔下毒,對吧?”她咧嘴笑道。笑容背後卻隱隱有種冷酷。
“願意的話,你大可以從你的人那兒搞到幹擾素。”他說。
她搖搖頭,把那兩片藥吃了下去,“我是經過強化的,不至於發個燒就燒死了。”
這倒可能是真的。他的大腦開始運轉,計算劑量和毒性,盤算著黑市增強藥物可能對她產生的作用。他讓自己大腦的某一部分忙於這些計算。他並不羨慕她抵抗發燒的能力,反正這類增強藥物對他也沒什麼效果。
鮑威爾很快就會開始發燒。他已經將整個騙局給她過了三遍,所以她現在應該已經懂了。鮑威爾發燒會導致體溫升高兩度,這並不會觸發賭場的安全程序,但這兩度體溫差將會激活安全補丁中的統計算法。福爾圖娜A.I.將預期她會贏得更多,所以當她真的贏得更多,就不會有警報出來。而這正是她不遠千裏來到偶人自由城的目的。
“走吧,”她說,呼吸在空氣中變成了霧氣,“你這個展館讓我心驚肉跳。”
他們走上旋梯,經過那些怪異的展品。展品的排列能輕易激發起貝利撒留那經過工程改造的大腦的興趣,就是負責探索模式、規律的那部分,卻又不至於觸發更深層次的數學反應。複雜的騙局也有相同的效果。
街上比裏麵冷。他們步行了9.6分鐘,時間足夠讓鮑威爾發燒,體溫上升。走著走著,街上的裝飾變得稍微悅目起來。偶人自由城是一個擁擠的貧民區,由歐樂星球冰凍地表之下掘出的洞穴組成。這些洞穴有些砌上了磚;有些則隻有冰,上麵殘留著食物和飲料的汙漬。許多隧道的光線十分昏暗,街頭隨處可見凍結的大塊垃圾。
整個自由城都喜歡賭博,從小聚賭點和街頭賭攤,到可以自稱賭場的地方。布萊克摩爾的賭場是唯一一個有福爾圖娜A.I.的地方,所以能吸引到有錢的賭徒,而那裏冰凍的街道也得以保持相對幹淨明亮。街道上,每片光滑的冰麵上都反射著燈光,花哨的綠色與柔和的藍色混雜在一起。貝利撒留很喜歡這裏的樣子。
沿著廢棄的公寓和商店的兩側,化緣的偶人站在胡亂搭建的玩具箱和假籠子之中,伸出雙手。他們看上去很像人類,膚色蒼白,很像過去歐洲人的後裔,隻是身體縮到了一半大小。一個瘦弱的女偶人身邊竟然有張折疊桌,桌上擺著一個真正的奶油泡芙,早已幹癟。貝利撒留扔給她幾枚硬幣。鮑威爾朝他做了個鬼臉,一腳將折疊桌踢翻在女偶人身上,那女人朝他們喊叫出一大串汙言穢語。
“她不是應該謝謝我嗎?”鮑威爾狂笑道。
“偶人並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完全沒有幽默感,阿霍納。”她說道。兩人來到布萊克摩爾賭場的入口。那裏有人類保安用檢測棒掃描顧客,令這家賭場相對於那些使用自動掃描的場子更平添了一分格調。“放鬆點吧。”
安全掃描花了9.9秒,對他的大腦而言,漫長得仿佛永恒。他開始思考相似性和模式來自娛自樂。能量從高能量分子向低能量分子作梯度流動。錢在賭場的逐級流動也遵循同樣的方式。生命就存在於這種能量梯度之中:植物在太陽和石頭之間找到位置;動物位於植物和死後腐爛之間。犯罪分子則深入賭場,就像藤蔓總是纏繞著樹木。
任何地方,隻要有錢流動,就會有人動歪心思要抽上一筆。即使在幹淨的賭場,趨同進化(4)也會令新人不斷湧現,隨時準備朝賭場或其客戶下手,實施欺詐。發牌員可以被收買,賭徒可以跟賭場老板勾結,老千在不斷發明新的騙術。福爾圖娜A.I.因此至關重要。缺少了福爾圖娜牢不可破的信念,誠實的錢就無法流動。
鮑威爾從他身邊擠過去。他跟著她上了一台花旗骰(5)賭桌。這張台子的督察(6)是他們的人,籌碼耙手(7)也是。鮑威爾和他昨天在展館已經秘密地見過這兩人。鮑威爾等待著,輪到她的時候,她下好注,托著骰子的手掌伸到貝利撒留麵前。他翻了個白眼,吹了口氣。她那張大臉紅撲撲的,笑容滿麵,頭一擲就是七點(8)。但這些隻是比較容易的部分。
其他三位玩家也下了注,選了點數。耙手把鮑威爾的一百聚合法郎(9)賭注推到十二點的位置上,又給她發了一副新骰子。這副骰子是貝利撒留設計的,裏麵有嵌入式液態納米元件。骰子內的透明液體輕微受熱,就會發生構象變化,單數點的那麵就會變重。骰子剛才已經在賭台督察身旁的白熾燈下放置了一會兒,現在又握在鮑威爾發燒的熱手之中。
鮑威爾擲出了一對六,圍觀的人群發出一陣歡呼(10)。
下一位玩家用冰冷的手指拿起骰子,呼出一口霧氣,以求好運。一對七點。她出局了。再下一位玩家擲出的是三點,周圍的人群又是一陣歡呼。最後一位玩家擲的是十點,也出局了。
鮑威爾活動活動手指,又把手夾在腋下取暖。她衝著耙手揚了揚下巴,示意他把自己的賭注繼續押在十二點上,然後伸手要骰子。耙手把骰子推了過來。她用一雙發熱的手握住骰子好幾秒鐘,閉上眼睛仿佛在祈禱,然後擲了出去。
又是一對六,圍觀的人群再次歡呼。
鮑威爾朝他綻放出笑容。賭台督察似乎以為福爾圖娜A.I.會被觸發,但他還是轉向賭桌,朝耙手點了點頭。貝利撒留裝出一副很高興的樣子。賭桌上的骰子涼下來了。如果說把賭場開在這個冰窟窿裏的城市有什麼好處的話,這也算是其中之一。僅存的一位玩家下了個聯合注,但擲出的是九點。出局。所有的注意力都落在鮑威爾身上。
“十二點。”她說,把一個籌碼遞給督察。督察吃驚地瞪大了眼睛。一萬聚合法郎,一筆巨款,追加到她剛贏得的那筆較小的款項之上。
“悠著點兒。”貝利撒留低聲說,“你不想再等等?”
她拿起骰子,緊緊握了十秒鐘,然後將它們丟進賭台。兩個六。人們揮手歡呼,鮑威爾放聲大笑,環顧周圍。但她的臉突然僵住了,揮舞的雙手緩緩垂下。
一個年輕的偶人祭司從人群後麵走了出來。她的皮膚是舊時歐洲人的蒼白,頭發也是同樣的顏色。她的身高按照成年人類的比例縮小了,隻有八十五厘米,長袍外覆蓋著鎧甲。她的身邊拱衛著十幾名主教士兵,他們身披重甲,讓身高平添了十厘米。他們端著槍,槍口對準鮑威爾和貝利撒留。賭場裏的人群緩緩後退,有些人尖叫著逃向大門。貝利撒留和鮑威爾被困在了中央。
貝利撒留猛然向賭場後部狂奔而去。祭司拔出一把手槍,火光一閃,槍聲巨響,回蕩在賭場裏。人們尖叫起來。貝利撒留身體一側的外套爆裂開來,迸出血液和煙霧。他倒在冰麵上,身下那攤血跡不斷擴大,又被凍結。他望著鮑威爾,眼裏盡是乞求之情,但是她已經嚇得呆若木雞。其他顧客紛紛矮著身子跑向出口。祭司和主教士兵沒有理會其他人。
“伊夫林·鮑威爾,你被逮捕了,罪名是瀆神。”偶人祭司說。
鮑威爾驚愕地張大嘴,瞪大了雙眼。“什麼!”她說道。
“在布萊克摩爾的賭場出千就是褻瀆神明。”偶人說。
鮑威爾無助地看著天花板,福爾圖娜A.I.就在那裏。照理說,如果它監測到賭局中有人搗鬼,就會有些動靜出來。她朝上指了指,“我沒出千,隻是運氣好!”
就在這時,警報響了起來。一束燈光投下來,罩住了鮑威爾。她無聲地嘟噥著,任由一名主教士兵反剪她的雙手,收繳了她的武器。其他士兵又花了九十六秒時間,驅散驚恐的賭徒,關閉了賭場。
“恩裏克,”貝利撒留爬起身來,搓著雙手說道,“你們這兒的地板真涼啊。”
橄欖膚色的督察從賭台後麵的位子上跳下來,“那就別躺下唄。”
在英西國(11)財閥政府治下,恩裏克厄運連連,欠下了一屁股債,不得不流落到這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在這裏,他在布萊克摩爾賭場找到了工作。有的時候,他會幫貝利撒留一把。貝利撒留解開外衣,拿掉身上的裝置,上麵是配合空彈炸開的孔洞。假血還在從孔洞中往外流淌。
“幹得漂亮,羅莎莉。”貝利撒留說。
羅莎莉·約翰斯十號還沒當上祭司。作為一名剛入教的新人,她還有一兩年學業要完成。但在這個地方,所有偶人都無精打采,逃避工作,就算她偶爾打扮成祭司,雇幾個不當班的主教士兵來充充門麵,也不會有人在意。她猛捶了一下貝利撒留的手臂。她夠不到多高的地方,但勁頭著實不小。
辦公室裏走出來一個男人和一個偶人。那個偶人是這塊聖地的守護者。之所以是聖地,因為彼得·布萊克摩爾在這兒賭博過。偶人用布萊克摩爾的名字命名了很多地方,隻有這一處名副其實。那個男的則是英西國的調查員,受雇於福爾圖娜公司。他和貝利撒留握了握手。
“在英西國的法律體係下,我們絕無可能抓到鮑威爾。”調查員說。
“這要感謝新教友約翰斯十號和偶人瀆神法令。”貝利撒留說,指了指她。
“別謝來謝去了。”恩裏克一邊說,一邊推開調查員,將籌碼遞給貝利撒,“咱們分完鮑威爾的錢,還是趁早離開這兒為妙。”
恩裏克把自己的平板電腦遞給貝利撒留。貝利撒留轉了兩千法郎給他。恩裏克咧嘴笑了。羅莎莉也遞上了她的平板電腦,貝利撒留給她轉了三千法郎。她得付錢給那些士兵、幫了他們的假商人、偶人警區的片警,加上主教的什一稅。
“你還有什麼新活兒嗎,老板?”她問道。
貝利撒留搖了搖頭。真的沒有。這個騙局不錯,能讓他分分心,但手頭的其他項目都隻是些雞零狗碎的小把戲,沒有什麼值得讓他的大腦忙碌起來的事情。“找活兒需要時間,等我拿到下一個活兒,就會打電話給你。”
賭博聖地的守護者給他們每人倒了一杯酒。他很高興,賭場的聲譽將會再一次提升。賭場雖然算不上最好的生意,但偶人目前受困於禁運令,這項生意對他們非常重要。
恩裏克溜了,調查員也走了,賭場主人回去收拾場子。貝利撒留和羅莎莉隨便挑了個雅座包廂,用新到手的錢把暖氣調高,又買了些更像樣的酒水。從某種角度說,他們倆有點淵源。她是偶人,更準確的拉丁文名稱是Homopupa;而他是量人,也就是Homoquantus。羅莎莉年輕,有見地,充滿好奇心。
“那家夥真是福爾圖娜公司派來的嗎?”她好奇地問。
“如假包換。”他說,“你以為我是怎麼讓做了手腳的骰子不觸發警報的?”
“我還以為你真的黑掉了A.I.。”她難為情地說。
“沒人能做到那個。”他把玩著手中的酒杯。他不喜歡對她撒謊,因為她是那麼單純,那麼信任別人。“福爾圖娜知道鮑威爾的人打算黑掉他們的安全補丁,眼看就要成功了,而他們還沒找到解決方案。他們急不可耐地想幹掉她,寧肯匆匆忙忙地在布萊克摩爾臨時安裝一個不完善的A.I.。以後當然會再裝一個新的,得花好多天。但對他們來說,這是值得的。”
羅莎莉又問了幾個關於騙局的問題。不算這次給鮑威爾設的圈套,她已經協助貝利撒留做了四票這種買賣,但對她而言,這種事仍然像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話題閑散地變換著,最後落到了神學上。一談起這個,羅薩莉的話匣子就打開了。
她極力用邏輯為偶人的瘋狂表象辯護,一說起神學就滔滔不絕。貝利撒留隻好跟她深入探討人類本性的問題,而他的邏輯常常又會啟發羅莎莉的思考。到了午夜,他們已經喝光了兩瓶酒,討論了三種克雷斯頓主教早年闡述的道德模型。貝利撒留覺得說的話和喝的酒都夠多了,於是起身回家,但心中卻隱隱覺得不盡興。
他那永不停歇的大腦計算著拱廊的石頭個數,度量著牆壁、房子和屋頂連接處的角度誤差,尋找逐漸惡化的失修之處。他細胞中的磁性細胞器感覺到了附近電流的不平衡,於是他的大腦又迅速計算出了各種服務故障的理論概率。他的大腦經過了生物工程的改造,有著十分旺盛的好奇心。做個小局蒙騙一下其他星球來的人,這點兒事情無法令他滿足,否則他就不會還有餘力進行這些計算。那些活兒的確來錢很快,但它們實在太容易,太微不足道了。
他走進展館,他的植入體接收到了展館A.I.的說話聲:“有人找您。”
(1)一種新的人類物種,拉丁文名稱的字麵意思為“玩偶人”。(本書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所加。)
(2)古羅馬神話中的運氣和機會女神。
(3)原文為拉丁文,字麵意義是“量子人”。是經過生物工程改造的人類。
(4)不同的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由於適應相似的環境而呈現出表型上的相似性。
(5)一種賭場十分流行的賭博遊戲。使用兩粒骰子,投骰後根據點數結果決定輸贏。
(6)賭場職員,賭桌上的主持人,負責監視莊家及整張賭台,並檢查擲出骰盒的骰子。
(7)賭場職員,手持耙子,在賭局中負責分發和收回籌碼和骰子。
(8)首擲七點可以贏錢。
(9)聚合是指未來世界的星際組織,其通用貨幣和語言分別是法郎和法語。
(10)一對六加起來正好是十二點,與前麵下注時選擇的點數相同,就可以贏錢。
(11)本書虛構英國和西班牙合並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