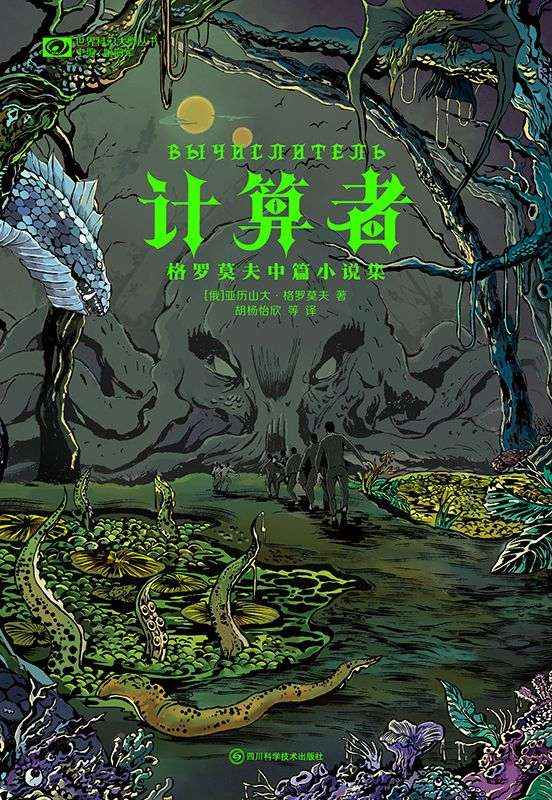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四章 還剩九人
篝火一下就點著了——幹脆的枯枝束剛靠近打火機的火苗,就被火舌卷起,劈裏啪啦地燒了起來,潮濕的水藻在火焰下噝噝作響。顯然,這些在火焰中抽搐的褐綠色的灌木枝條裏富含油脂。
夜幕降臨,所有人都筋疲力盡,無論是厄溫和克莉絲蒂,還是尤斯特一行人。七人在二人右手邊行進,連成約兩百米的鏈條。他們看來是吸取了教訓,沒有再像呆頭鵝一樣一個接著一個地拖著走,而是排成梯隊,完全忘了要循著前麵的人在藻毯上留下的小徑走,把浮毯踩成了一片泥潭。他們腳下原來結實柔韌的浮毯很快變成了一攤黏膩的爛泥,隻要踩下去,水鞋就會被粘住。從泥濘中將腳拔出,大量的氣泡隨之慢慢爆裂,散發彌漫出一股腐爛的惡臭。沼澤麵上出現了一個個顯眼的泥濘“窗口”。
中午的時候,厄溫看到了第一條蛇,並指給克莉絲蒂看。這個小生物一米長的身軀油光水滑。蛇並沒有發起攻擊,而是輕巧地繞過兩人,穿過他們前路,滑到水藻底下,消失了。不久之後,南邊的遠處出現了一群生物。它們以驚人的速度移動著,像是在沼澤上滑行。突然間,舌怪的觸手在空中揚起,疾速地畫了個圈,然後消失了。至於這個獵食者有沒有抓住什麼——沒能看清。
又過了一小時,克莉絲蒂彎腰拾起了一根泡在泥漿裏的布條。可以看出,這是背包背帶的一段。到這裏為止,還沒有碰到任何其他的人類蹤跡。
距離過夜的地方還有最後幾千米——那是一片細長而顯眼的淺灘,上麵長著些灌木叢,甚至還有些幹枯的小樹紮了根。克莉絲蒂完全是機械地行走著,隻想著一件事:扔掉沉重的木杆,忘記一切。她也這麼做了,隨即,她腳下的浮毯不再輕晃。她不想說話,不想動,也不想活。
然而一個小時後,她醒了過來,並驚奇地發現,自己不想再躺著了。浸透水藻的泥水算不上冷,但她還是打起了寒戰。在她五步開外的厄溫將一堆腐爛的水藻撩到一起,似乎是要用來當床鋪。篝火不時發出劈啪的細響,升起帶著樹脂香氣的煙霧,十分誘人。
“來取下暖。”厄溫建議道,克莉絲蒂感激地在靠近篝火的地方坐下。很快,她的衣服被烘得升騰起蒸汽。他們能聽到在遠些的地方,同在一片淺灘上的尤斯特一群人的交談和窸窣響動。那邊也燃起了篝火,而且似乎更亮些。
“實際上,在沒有迫切需要的情況下,最好不要做這樣的實驗。”厄溫往火裏拋了一小把柴火,說,“萬一我們身邊剛好有沼氣泡冒出來呢?‘哧’的一聲——我們就隻剩下箱子了。”
“我不介意。”克莉絲蒂低聲應道。
“但我介意。”厄溫麵色嚴肅地反駁道,“你不習慣。這很難,我明白。但還會有更難……和更危險的狀況。我能保證。但我決定了要去幸福群島,這意味著我一定要到達。我要活下去。因此,你也還有機會。”
“我想吃東西。”
“想象自己吃了,我也想象一下。明天會有吃的,我保證。這裏沒多少蝌蚪,不值得去捉,特別是在晚上。”
“你記得嗎?岸邊有很多……”
“當然!不知道它們能吃的犯人沒有去抓,而知道它們能吃的犯人還不餓。它們沒辦法當儲備糧,而且隻有餓得獸性都出來了的時候才能吃得下去。當然,這裏也能捉到蝌蚪……淺灘很方便。木柴還沒燒完,真讓人驚訝……”
克莉絲蒂在箱子上動了動,讓自己的另一側轉向火焰。她把一縷黏結在一起的頭發從臉上撥開。
“怎麼到你這裏,一切總是那麼合乎邏輯……”
“你很驚訝?”
“不怎麼驚訝。你今天幾乎沉默了一整天,是在估計我們的勝算嗎?”
“包括這個。想得不多。更多是在消遣。”
“怎麼消遣?”
“算數。恒星動力學著名的三體問題。聽說過嗎?給出質量,比方說,一,三,或者五,給出初始速度的向量,然後是微分方程的數值解,計算在相互間萬有引力的作用下每個天體的運行軌跡。最後,其中一個天體——通常是質量最輕的那個,會被拋出三體係統,見鬼去。我試著找到一個初始條件,使得在這個條件下係統丟出的不是最輕的天體,而是最重的天體。”
“然後呢,找到了嗎?”克裏絲蒂嘲諷地問。
“還沒有。”
“怎麼,你是數學家?”
“我沒拿到學位。是的,說實話,我從來不需要學位。但我擅長計算。”
“那你最好算一算怎麼我們才能不在這沼澤裏咽氣!”
“早在我們還在岸邊的時候就算過了。當然,新數據不斷出現,要不斷進行更正,其中一些不得不重新計算……但通常並不困難。有標準的數學方法,我自己研究出來的。”
“撒謊。”克莉絲蒂肯定地說。
“你可以不信。”
“也就是說……你選我做搭檔,是基於數學計算?”
“可以這麼說。”厄溫點了點頭。
“我還是不相信你。”
“對此我毫不懷疑。”
“你之前在外麵到底是做什麼的?犯罪集團的大腦核心?”
“類似。我是蘇克哈達裏揚總統的顧問。在政變後的第三天,我被抓了。”
“你?”克莉絲蒂聲音嘶啞地大笑起來,“你是深淵星總統的顧問?”
“想象一下。”
“我從來沒聽說過你。”
厄溫歎了口氣。
“糟糕的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從新聞節目裏汲取信息,比如你……但的確有很多位不同的顧問。記得三年前‘絕對統治’集團的破產嗎?雖然,你無從知曉……是我讓他們變得身無分文。他們支持錯了人。出擊的是蘇克哈達裏揚,所以沒有人知道這是誰的手筆,而我隻是算到了該在什麼時候朝哪裏出擊,拳頭才不會被擋回來……說起來,這並不難。在過去六年中,總統一步步按著我的計算走,而他似乎對此並不後悔。”
“然後,想必是出現了什麼沒有考慮到的因素……”克莉絲蒂撲哧一笑。
“並不是。當然,唯一沒有被考慮到的因素足以讓整個局麵重新洗牌——計算者的任務就在於此,確保在任何始料未及的情況下,係統仍保留著足夠的‘安全邊際’。更不妙的是,總統在鋸斷自己所處的那根樹枝。隻有一次蘇克哈達裏揚沒有聽我的,隻因普賴是他自畢業以來的好友。如果這個好友正好在災禍中死去,蘇克哈達裏揚現在就不會被軟禁,也不會咒罵著自己曾經的重情心軟,等待自己死於‘心臟病發’。而我現在也不會坐在這個箱子上。”
“難道你是計算機嗎?”
厄溫哼哼幾聲,搖頭。
“這是你自己說的……行了,我不會生氣。難道你真的認為,蘇克哈達裏揚不能像別的政客一樣,給自己籌集擁有最尖端電腦和龐大編製的分析中心嗎?他選擇了我,這並沒有讓他付出的代價更少些。但他從不後悔。”
篝火快要燒盡了。厄溫似乎不準備讓它整晚燃燒。
“機器在千萬種情形中勝過人類。但總會有起碼一個人類,會勝過機器。”
“你不再多砍些柴火了嗎?”克莉絲蒂問。
“不了。”
克莉絲蒂瑟瑟發抖,她環抱著自己的肩膀。沼澤上濃霧層層,濕氣又把剛剛才烘幹的衣服浸透。小月亮不見蹤影,大月亮被模糊成朦朧的圓點。
“我還是不明白,怎麼能計算出人的行為。在我看來,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是一大群人……”
“人群恰恰更容易計算。”厄溫應道,“總之,很久以前已經研究出了不少計算個人以及任何大型群體行為的方法。通常來說,它們由於引入不可靠的信息,都是無效的。恰好機器不會從真話中識別出謊言。而我更擅長此道。”
“他們是怎麼抓到你……這樣足智多謀的人的?難道你沒有想到該擔心一下自己嗎?”
“我在政變前夕逃跑了。”厄溫不情願地承認道,“那個計謀……可以說,是我的驕傲。摻雜著在預期風險之內的偶然。因為零跳躍前出現的輕微故障,我回到了深淵星。在著陸前的最後一個晝夜,我在飛船上的圖書館裏讀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關於馬尾藻沼澤的記載。而最困難的還在後頭:我要讓自己被判處最高刑罰,而不是在試圖逃跑時被從背後射來的光束殺死。”
“你被指控的罪名是什麼?”
“與非法政權共謀,還能有什麼。說得像是還有‘與合法政權共謀’一樣……”
“你怎麼不算算自己怎麼才能被無罪釋放呢?”克莉絲蒂挖苦道。
“我不算不可能的事情。”
一聲長歎從沼澤傳來。有什麼巨大的東西在迷霧的掩蓋下在泥沼中翻騰,靠近淺灘西邊——那正是尤斯特一行人不久前落腳的地方。克莉絲蒂跳了起來。“坐下。”厄溫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她聽話地坐回了箱子上。
有什麼在沼澤裏嗚咽,撲哧作響,翻來覆去了一會兒,又銷聲匿跡。
“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厄溫答道,“我沒有讀到過相關記載。順便說一句,這裏可能有人類還不知道的生物存在。沒有誰真正地研究過馬尾藻沼澤。”
他又緊張了一會兒,然後又稍稍放鬆下來。
“好吧。”等驚嚇過去後,克莉絲蒂說,“假設說,我相信你。這對你的計算有影響嗎?”
“無足輕重。”
“那這次過夜你也是提前算好的嗎?”
“淺灘不是。我怎麼知道有這麼塊淺灘?”
“現在呢?”
“我們還有半個晚上。然後就會開始漲潮,灘塗會被淹沒,到時我們最好離開。而在這之前,我們最好睡好睡足……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尤斯特和他的小無賴們不會追上我們,他們可累壞了。”
“我們不用輪流睡嗎?”
“不用。值得冒險。我們需要休息,明天會是艱難的一天。”
他們躺在一攤濕漉漉的水藻上,試圖靠緊緊依偎對方來保持溫暖,時而深陷夢境,時而醒來,驚惶不安地側耳聆聽沼澤裏似真似幻的聲音。朦朧的月華緩緩向西邊遊移。隨著時間的推移,沼澤裏的小生物開始發出細小的叫聲——這邊嘰嘰喳喳了一頓停了下來,那邊又開始吱吱地應答。以尤斯特為首的一行人過夜的地方也傳來了微弱的聲響:尚未燃盡的篝火劈啪的脆響、水藻摩擦的沙沙聲,時而夾雜著半睡半醒的人們的咳嗽聲和低低的呻吟。
一聲刺耳的號叫將兩人震了起來——這令人悚然的哀號發自男性,聲音拖得很長,充滿痛苦和恐懼。發出這樣尖叫的人可能被大型猛獸捕獲,隻是不知為何這隻野獸磨磨蹭蹭,叼著痛苦的受害者,沒有利落地合上口。
“等著,一步也不要離開這裏!”厄溫抓起了長鞭。
“不!”克莉絲蒂緊緊攥著他的衣袖,不住地搖頭。
“放開……我很快就回來。”
他踏著泥沼,不見了蹤影。滾滾濃霧淌過淺灘。女人顫抖著將自己縮成一團,試圖讓自己變得更渺小和不顯眼,像是霧中馬上就要衝出一張血盆大口,將她吞吃入腹。
尖叫聲,揚鞭聲。暗影躍動。尤斯特嘶啞的指揮聲和矮胖女人刺耳的尖叫清晰可聞。之後,尖叫聲弱了下去——而身邊的篝火則變得吵鬧起來。
過了一會兒,厄溫回來了。
“是蛇,”他粗喘著氣,解釋道,“被篝火的光吸引過來的,就像我之前說的。大概五條,不超過這個數。但是很粗。刀子能對付它們,但鞭子更好使。其中一條纏住了瓦連京,剛才叫起來的人就是他。沒事,他會醒過來的。如果能及時地把這畜生殺掉,你就隻會被刮掉點皮,但不會死。”
“他還能走嗎?”克莉絲蒂一邊問,一邊試圖控製自己的顫抖。
“愚蠢的問題,抱歉我這麼說。他跟你一樣想活下去。順便說一句,他輕而易舉地就脫身了——他想到了要往篝火裏滾。蛇很快就把他鬆開了。”
回籠覺沒有睡成:潮水把灘塗變成了難以涉足的淤泥堆,厄溫指明,沒有必要在一攤爛泥裏等待天明。淺灘能讓流放者免受舌怪之類的喜靜生物的攻擊,但避不開蛇,也避不開在這一路上還沒遇到的其他嗜食人肉的沼澤生物,這些生物更慣於主動出擊,而不是守株待兔。厄溫朝霧那邊大喊,告訴他們自己要走了,幾乎是話音剛落,尤斯特的人就忙亂起來,收拾東西準備上路。
月亮朦朧的光點在霧中漸漸熄滅。克莉絲蒂驚異於厄溫竟然能辨別方向,保持著向東行進。他們走得很慢,用杆子試探出一條路。尤斯特的人悄無聲息,也不見蹤影。有一次,克莉絲蒂腰部以下都陷進了沼澤,厄溫用一個沾滿汙泥的大鉤子將她拖了出來。還有一次,克莉絲蒂沒保持好平衡,摔了一跤,在離她大概十五到二十步的地方,有什麼拚命地發出尖銳刺耳的叫聲,在泥沼裏胡亂竄動,然後有什麼猛地抽了一下濕漉漉的水藻,這些聲音又靜了下去。
黎明破曉前再也沒發生什麼。臨近早晨,霧氣漸薄,然而天空蒙上了一層濃密的灰色,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開始遇到更深的水窪,在這些水窪上,用繩子係在厄溫身上的箱子不再被拖得窸窣作響,而是像方舟一樣慢慢悠悠地安穩漂流。浮毯晃動得更厲害了,水一路沒過膝蓋。
很快,厄溫也像克莉絲蒂一樣陷入了泥沼。他及時趴在了木杆上,喊了一聲自己能應付,然後用盡全力將自己從泥沼裏拔了出來,還丟了右腳的水鞋。他不得不從包裏拿出一隻備用的。
他們像昨天一樣,把箱子拖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然後在上麵休息。尤斯特和他的人仍然不見蹤影,但據肉眼估量,沼澤的能見度不超過半千米。
“他們不會迷路了吧?”克莉絲蒂讓厄溫喘了口氣,才問道。
“很有可能。地圖上顯示距離幸福群島還有三百千米——實際上如果在五百千米以內就算我們走運了。迷失了方向,就會原地打轉……像昨天那樣的晴天,在這裏是很罕見的。”
“你還沒迷失方向嗎?”
“我覺得還沒有。當然,或多或少會有偏差。但還是知道大概的方位。大致在那邊。”厄溫擺了擺手,“當我不是很確定的時候,我會說的。”
直到蒙蒙細雨將霧氣完全吞噬,他們才動身離開,也因此發現了右方不遠處緩慢挪動的一隊人。跟之前一樣,還是七個。厄溫從水窪裏抓了約十隻被克莉絲蒂稱為“蝌蚪”的小生物,第一次嘗起了本地吃食。食物的味道極其糟糕,如果是前天吃到這樣的早餐,克莉絲蒂會忍不住吐出來,昨天料想也會是一樣,但今天,饑餓感終於占據了上風。他們將蝌蚪平分,然後往唯一的小碗裏灌了些半鹹水,輪流喝了個夠。吃完早餐,七人的隊伍變得越來越近,並且越來越偏向左邊,顯然意圖打破兩支隊伍平行的關係。
“啊哈,”厄溫說,“我想也是。”
“你想了什麼?”
“尤斯特還是有那麼點頭腦的。他當然不會走在我們前麵,但我也告誡過他不要慢騰騰地跟在我們後麵。現在他以為我們麵臨的是一樣的狀況。”
“難道不是嗎?”
厄溫撓了撓後腦勺。
“七個人一起對付蛇似乎比兩個人要容易。但你看,根本不關人多人少的事……這樣說吧,假設舌怪待在沼澤底的哪個地方,這樣龐大的軟體動物,就這麼等著……在泥炭和水藻的遮蓋下。它根本不需要視力和聽力。當它感覺到在自己觸手能到達的範圍內的浮毯微微晃動時,它就會發起攻擊……我不知道事實是不是這樣,也沒有人知道,但若果真如此,那麼七個人走成一列——簡直愚蠢至極……”
一條蛇從下方朝他發起進攻,把藻毯衝出了個窟窿。他根本沒有時間解開鞭子。克莉絲蒂尖叫了一聲。厄溫揮手擋住這隻衝向他麵部的野獸,與此同時,他的手被這條發光的蛇的重量帶得沉了下去。它看起來更像是一條一米半長的水蛭,也正像水蛭一樣緊緊地吸附在他身上。衣袖對它而言並無阻礙作用,衣料隻剩碎片在飛動。
弄死這條蛇花了不少時間——必須將它一點一點地從手上刨下來,但即使被削去一半,它仍掛在那裏,吸附著,啃噬著……厄溫呻吟著將它剩下的部分從自己身上扯了下來,在它完好的蛇腹上發現了兩排圓孔,孔裏鑲滿一粒粒褐色的牙,其中一些還在張張合合地向中間合攏。
他很走運:蛇的牙齒還沒來得及紮紮實實地咬下去,遭殃的隻有袖子,小臂上有一塊圓形的地方在出血。但隻有一處。厄溫將已經被撕開的、濕透的袖子整個扯了下來,克莉絲蒂幫他將胳膊包紮起來。
“該走了。”厄溫眨眨眼,說。
“痛嗎?”克莉絲蒂關心地問。
“不,我很好。我喜歡被活生生地吃掉。那是極致的愉悅。”
“對不起……如果你願意的話,我來背包?”
“不用……你還記得方向嗎?喏,向前。”
兩人繼續走,沼澤的表層仍然被他們踩得變形,像是已經腐爛的、不甚結實但仍有彈性的蹦床。細雨未停。尤斯特一行人在右方大概百步遠的地方走著。他們仍然走在一起,但沒有像昨天早上那樣一個跟著一個地走,也不像昨晚那樣排成一個梯形,而是排成了兩個梯隊:最前麵是兩個人,在他們的側後方是三個人,再後麵還有兩個人。尤斯特走在第四個。
“看來他們學到了些東西。”克莉絲蒂沒有惡意地說,“再多一些,他們就能想到分成三隊分開走。”
厄溫沒有立刻回應——他的一隻腳被粘住了,他在努力地讓自己把腿拔出來的同時不弄掉水鞋。
“就算他們想到了,領頭的也不會允許。到時候誰替他前前後後作掩護呢?”
“也許,他們會反抗……”
“除非尤斯特對他們來說比沼澤還可怕。隻是這不太可能。”
他們沉默了整整一個小時。在這一個小時裏,如常率領著一行人的萊拉沉下去了兩次,矮胖女人陷下去了一次,並發出了眾人習以為常的尖叫。這時,克莉絲蒂就在沒有厄溫指令的情況下停下來,兩人一起等著尤斯特的隊伍拖出陷入沼澤的人後繼續上路。危機四伏,但右方的危險在某種程度上會少些。
當萊拉第三次陷入沼澤,喬布和揚·奧伯邁爾用早已不再潔白的繩子使勁地將她從泥沼裏拉了出來之後,尤斯特大喊起來,吸引厄溫的注意:“哎,呆子!你那裏有沒有備用的水鞋?借來用一會兒。”
他把手舉過頭頂,遲疑地揮著一包壓縮幹糧包,可能這就是他們剩下的最後一包,但厄溫不打算回答。克莉絲蒂也沉默不語。
等到糊滿汙泥的萊拉回到了隊伍的最前麵,他們也繼續行進。又過了半個小時,在比尤斯特一行人的位置更靠右的沼澤裏拱起了一個渾圓的丘體,伴隨著嗚嗚的聲音,一根不長但十分靈活的紫色舌頭衝破了丘頂,衝向細雨蒙蒙的天空,它轟然倒在喬布和海梅之間,頃刻便摸索到了繩子,猛地一拽……尖叫四起。
海梅第一個及時地把自己身上的繩子解開了。喬布在水藻和泥裏被拖行,但他應付得來,他巧妙地用刀子割開了繩子,而沒有割到自己的大腿。淡紫色的舌頭縮了回去。有那麼一瞬間,它好像就要將繩段拖走,暫時還人們一個安寧,但這個潛藏在水底的巨型軟體動物並沒有人們所希望的那麼愚蠢。
舌怪扔掉了繩子,又抽打起來,橫掃水麵,像龍卷風一樣席卷至還在泥濘中撲騰的喬布上方,然後閃電似的轉回了海梅周圍,不湊巧的是海梅剛來得及站起。它猛地一拽,頃刻被拋到空中的不僅是海梅,還有一邊嚎叫、一邊割著把自己與不幸係在一起的繩子的瓦連京。浮毯劇烈顫動。
瓦連京撲通一聲跌落在泥濘中,砸得腐爛的海藻碎屑四濺而起。被拋到沼澤上方的海梅扭動著、大喊著,揮刀亂砍那舌頭一樣的觸手。但舌頭絲毫沒有注意到這些小東西,它伸直成方尖碑1的模樣,迅速地縮回泥潭裏。最後一聲絕望的哀號、拍擊水麵的巨響,還有周圍人們的尖叫聲,清晰可聞。
六人朝厄溫和克莉絲蒂這邊跑來,其中一人怎麼也站不起來,急切地想要逃離死亡,於是手腳並用地爬行著。萊拉又陷進了沼澤,她幾乎是反射性地迅速向兩邊伸出手,倚靠著起伏搖曳的藻毯。與她連在一條繩上的揚·奧伯邁爾冒著自己也要沉下去的危險,原地踏步,高聲吟唱,或許是堅信無處不在的主亦潛藏在這噩夢般的生物上,以自己最糟糕的位格2出現。
淡紫色的舌頭沒有再探出來,不再在自己四周搜索其他的獵物。人們漸漸恢複了冷靜自持。矮胖女人停止尖叫,轉而抽噎起來。尤斯特怒聲嗬斥,給了她幾記耳光,整頓起秩序。喬布試圖把自己跟瓦連京綁在一起,笨拙地打著航海結。綽號骷髏的揚·奧伯邁爾蠕動著嘴唇,無聲地祈禱,並用枯瘦如柴的手掌撫平腐爛的水藻。作為無處不在的主的傳教士,沒有念珠和其他宗教用具他也能做得很好。被從泥裏拖出來的萊拉,大膽地悄悄爬近海梅沾滿汙泥的木杆,將他救了回來。紫色舌頭在藻毯上擊穿的孔洞漸漸地合攏了。再也沒有什麼能泄露出潛伏在暗處的猛獸的蹤跡——在它已經吃飽的時候。
1 古埃及建築,外形呈尖頂方柱狀,由下而上逐漸尖狹。
2 基督教教義中“三位一體”的教義認為,上帝有“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和一個“本體”。三個“位格”各自具有理智和意誌,能各自活動,相互區別,但在本性和實體上毫無差異,共享一個“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