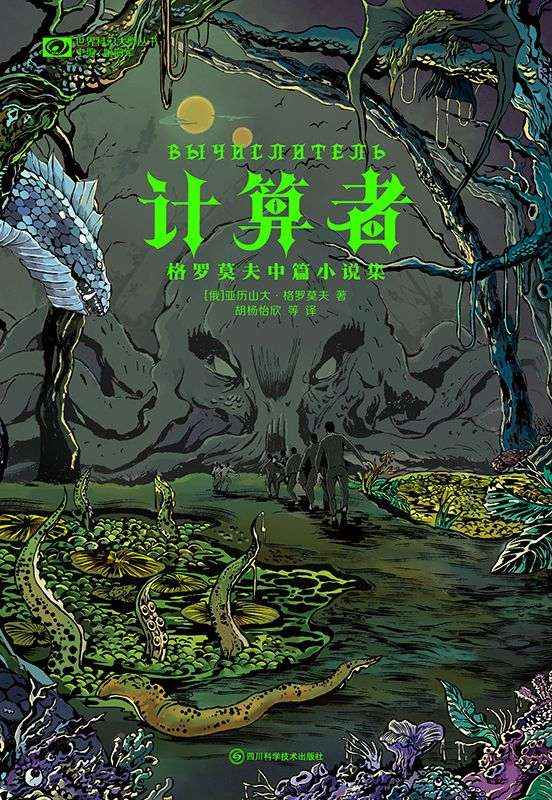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亞曆山大·格羅莫夫:人是這樣的生物
[俄]葉夫根尼·哈裏托諾夫
最出乎意料的是,那條人類將在公元2100(3000?4000?)年之前完全滅絕的預言根本沒有成為現實。
這也是最合理的。
——亞曆山大·格羅莫夫《虛空之王》
我們所有的英雄要麼已經自我了結,要麼正在自我了結的路上。
——亨利·米勒《北回歸線》
1
與之前不甚樂觀的預測相反,優秀的古典科幻文學在我們的文學史中幸存了下來。來自莫斯科的科幻作家亞曆山大·格羅莫夫的作品證實,科幻文學並沒有過時,在這個類型中仍能誕生全新的情節,形成探討某一主題的故事線。在我看來,比起時下流行的奇幻文學,科幻文學所涵蓋的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以及觀點和話題的自由度都要高得多。
有趣的是,亞·格羅莫夫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非常傳統的作家,他繼承了從俄羅斯哲學散文到蘇聯科幻、從斯特魯伽茨基兄弟到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和美國作家羅伯特·海因萊因的文學傳統。總而言之,他寫的是俄羅斯文學中十分常見的主題——社會科幻。
但矛盾在於,作家表麵展現出的傳統性、“與時代脫節”,恰恰與現在人們所定義的科幻傳統並不相符,而是更合乎當代科幻的標準。正因如此,作者稱其作品具有獨創性。事實上,格羅莫夫在現代俄羅斯科幻“新浪潮”中是公認的局外人:他不寫動作小說(盡管他的故事劇情起伏,不乏緊張刺激的情節),對奇幻文學也興味索然。人們尊重他在寫作上的成就,嘖嘖稱讚,卻沒有體現出在雜誌上對他的作品發表評論的熱情。而亞·格羅莫夫的作品的確值得認真細致地加以分析。
但在繼續談論格羅莫夫的作品之前,我們先整體談談俄羅斯當代的科幻作品。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們的科幻文學呈現出一種相當奇怪的景象。
蘇聯知名科幻作家基爾·布雷喬夫在《烏拉爾探路者》1雜誌上答讀者問時曾說道:“我相信,比起現實主義文學,科幻文學能更準確地反映社會狀況。”這個觀點準確而公正。可以補充一點,科幻文學不僅反映了社會狀況(這裏也可以指社會上的外部因素),還反映了社會的趨勢走向。科幻小說的方向變化反映了社會思潮的演變。仔細追蹤俄羅斯科幻文學的曆史軌跡,很容易注意到一條規律:一切都在重複。文學也不例外。在社會麵臨災難和重大變革的時期,烏托邦(更常見的是反烏托邦)成為文學的主線。18世紀,以“理想國”為主題的作品層出不窮;血腥的1905年2後誕生了一批反烏托邦作品;1917年3後,烏托邦作品出人意料地蓬勃湧現,同時反烏托邦作品也還占有一席之地,因為當時,一些人受浪漫主義的革命思潮所鼓舞,眼中看見的是俄羅斯乃至全世界的光明未來,另一些人則看到了可能的不良後果,並試圖發出預警。改革為人們帶來了曙光,但也教給人們一個簡單的道理:革命並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因此,在產生新變革的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一批反烏托邦作品應時而生。
俄羅斯的命運是一個令人擔憂甚至痛苦的主題。而這一直是我們文學的重要母題。我們的人民展望未來,迫切地尋求“神的國度”的種種跡象。然而,這類探尋引發的隻有一種悲觀的信念,即俄羅斯的未來充滿疑慮,往好處說,也是迷茫不清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無從預料的,這種情況以往從未出現過。人類遲早會放棄烏托邦文學。
列昂尼德·蓋勒4在《超越教條的宇宙:蘇聯科幻小說》一書中說道:“烏托邦小說是不必要的,因為它消除了兩麵性,麵向未來而無視現實。它的危險性在於,直接入侵‘禁區’,描繪了未來的具體麵貌。”
然而,一切並不像表麵看起來那樣簡單。我們開始害怕“預測出的”未來(更何況,不幸的是,大部分反烏托邦作者都極具遠見卓識)。
過去俄羅斯的社會進程的不可理解性、晦澀性和不可預測性,在作家們(此處特指科幻作家們)心中激起了建立另一種秩序的衝動——在神秘而神聖的或然世界尋找一個理想中的“神的國度”(在每人眼中都各不相同)。作家試圖逃避可怖的客觀現實,逃離現實社會中的現實問題。在俄國,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取代了18世紀“過度社會化”的啟蒙運動者,將藝術與現實“劃分為截然不同的領域”(引自塔·阿·切爾內紹娃5),使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浪漫主義者喜歡描述轉變、破壞性的事物及生命的本真。”(引自納·別爾科夫斯基6)浪漫主義者斷然拒絕亞裏士多德美學的基本原則——模仿自然。“如果現實和藝術相矛盾,還應該模仿現實嗎?現實需要被重塑,被改進,隻有這樣才能被稱之為藝術!”(引自塔·阿·切爾內紹娃)對現實的重塑正是浪漫主義藝術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俄羅斯科幻作家——謝爾蓋·盧基揚年科、H. L. 歐迪、尼克·佩魯莫夫、謝爾蓋·伊萬諾夫,以及一些“無意識”信奉浪漫主義人生觀的奇幻作家,同樣遵循這一原則。
莫斯科作家安德烈·謝爾巴克-茹科夫高明地將新一代俄羅斯科幻作家(25至30歲)稱為“信息時代的浪漫主義者”。我們這代的科幻作家又重新開始理解世界、追求19世紀藝術的目標——藝術高於現實,改造而非模仿,虛構而非現實,個人而非社會。新一代作品的主角也深具浪漫主義色彩,通常是隻身對抗世界的獨行俠、騎士,將永遠不會被磨滅的夢想——在這個可怕的、抵禦著邪惡化身的善之世界中的無限可能——化為現實。推崇奇幻文學(至少是在俄羅斯社會中)是一種對不可理解的社會的正常自衛反應,是將社會問題拒之牆外、消除自身恐懼的渴望。另一個世界甜蜜而迷人,它吸引著你,使你開始相信,自己可以從蘇聯社會中碌碌無為、飲盡生活苦水的“一具斷線傀儡”變為宇宙中“來自地球的主宰”(盧基揚年科小說名)。作者把角色與自身聯係起來。飛升和易形的主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幻想文學中尤其豐富。
將幻想文學引入我們的文學土壤,本就有著深刻的社會和心理基礎。鐵幕的“拉開”使西方幻想文學湧進俄羅斯,成為長久發展中的進程的催化劑。畢竟20 世紀的科幻作家與19 世紀的作家的心境極為相似:“……我們現在最好忘記一切,陷入睡眠,在幻想的夢境中狂歡。”
在我看來,如今的俄羅斯幻想文學中,有兩種世界觀已經基本成熟:脫離現實的理想浪漫主義(主要以奇幻作家為代表)以及唯物的悲觀主義(比如亞·格羅莫夫)。兩個主要的主題——建造一個幾乎是田園牧歌式的烏托邦或然世界,轉向神話式的過往(主要是奇幻小說);或是另一個還在不斷發展的主題:災難後的地球世界,回到反烏托邦的傳統(例如亞·格羅莫夫的《軟著陸》)。人類的生存問題在當下再次變得迫切起來。我們在20 世紀90 年代的情況也並不樂觀。國家的解體、兩次“失敗”但不乏血腥的革命、民族衝突、經濟混亂、強盜和黑手黨猖獗……我們能生存下來嗎?我們要去向何方?我們會麵臨什麼?
作家亞曆山大·格羅莫夫試圖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