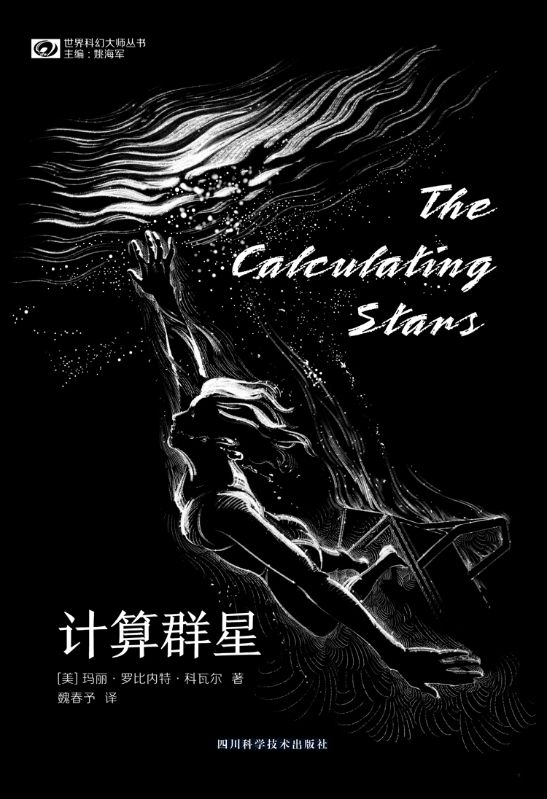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五章
潮汐波侵襲委內瑞拉
美聯社委內瑞拉加拉加斯1952年3月4日電政府今日公布,隕石撞擊北美洲海岸時引發巨浪,海浪襲擊了科羅港口,造成了嚴重損失。據稱,停泊在委內瑞拉西部港口的船隻被毀,海濱地區的房屋被夷為平地。目前還不清楚傷亡人數。
我肯定是不知不覺地在沙發上睡著了。納撒尼爾碰了碰我的額頭,我才醒來。廚房的燈光照進黑暗的客廳,爬上了他身上的白色襯衫。他身上很幹淨,已經洗過澡了。有那麼一刻,我暈頭轉向,以為這一切都是我在做夢。
“嘿……”他笑著把我額前的頭發往後梳了梳,“你想睡在這兒還是去臥室?”
“你什麼時候回家、回來的?”我坐起來拉伸了一下僵硬的脖子。林德霍爾姆太太的針織毛毯被拉到了我肩頭,電視機像是角落裏的黑暗幽靈。
“就剛才,林德霍爾姆少校帶我回來的。”他朝廚房點了點頭,“他正在做三明治。”
“你吃過了嗎?”
他點了點頭,“會議期間管飯。”
納撒尼爾伸手拉我,幫我站起來。夜幕降臨,白天的傷口、酸痛和淤血這會兒都來找我了。每走一步,我的小腿肚都在灼燒。折毛毯時,就連我的胳膊都在抗議。現在再吃一片阿司匹林的話,服藥間隔時間會不會太短?“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快到午夜了。”
如果他真的是剛剛才回來,那情況就不容樂觀了。昏暗的燈光下,他的麵孔有些模糊,看不真切。廚房裏,林德霍爾姆少校正拿著刀,跟盤子幹架。我放下毛毯,“回臥室吧。”
他跟著我穿過昏暗的大廳,來到林德霍爾姆太太為我們安排的房間。這房間原本屬於她的大兒子阿爾弗雷德,他去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工程學學位了。不過房間裏還掛著他高中的“豹子”三角旗、拚了一半的樂高建築套裝和《儒勒·凡爾納全集》,和我兒時的房間如出一轍。房間裏其他東西不是格紋的就是紅色的,我猜這是他母親的手筆。
關門後,納撒尼爾伸手去開燈,但我攔住了他。我想在黑暗中再多待一會兒,黑暗能給我安全感。這裏隻有我們倆,沒有收音機提醒我們,我們正寄人籬下。丈夫將我抱在懷裏,我靠著他,臉頰緊貼著他的胸膛。
納撒尼爾用下巴抵著我的頭,雙手穿過我還沒幹透的頭發。他身上有一股不熟悉的薄荷香皂味。
我依偎著他問道:“你在基地裏洗澡了?”
他點了點頭,下巴摩擦著我的後腦勺,“我在桌子上睡著了,他們隻能暫停會議。我衝了個澡才清醒一點兒。”
我往後一點兒抬頭看他。他的黑眼圈似乎更深了。那些混蛋。在他今天經曆了這麼多事以後,他們還讓他熬夜?“他們為什麼不送你回來?”
“他們是有這個打算。”他捏了捏我的肩膀,再慢慢地鬆開。他解開襯衫扣子,緩緩朝床走去,“我擔心如果我離開,帕克上校會做出什麼蠢事來,他真做得出來。”
“他就是個傻子。”
納撒尼爾襯衫脫到一半時停住了動作,“你之前說你認識他。”
“他在戰爭期間是個飛行員,指揮著整個中隊,非常非常非常厭惡女人駕駛他的飛機。可以說是痛恨,而且他占有欲很強。”
事後看來,我不該把最後那一點告訴我老公。至少不該在他精疲力竭的時候提起。他噌地站起來,我還以為襯衫都要被他扯破了,“什麼?!”
為了安撫他,我舉起雙手,“不是對我,也不是對我小隊裏的任何女性。”呃,在我和我爸談過之後才沒有。我聳了聳肩,“身為將軍的女兒的優勢。”
他哼了一聲,接著去脫他的襯衣,“那很多事就說得通了。”他的背上傷痕累累,“我想我已經說服他這不是原子彈爆炸了,但他堅持認為是俄羅斯人瞄準了那顆流星。”
“俄羅斯人甚至還沒有離開地球。”
“我提了。”他歎了口氣,“好消息是,雖然他想讓我們以為指揮鏈已經斷裂,但事實並非如此。艾森豪威爾將軍正從歐洲飛回。實際上,明早他應該就到這兒了。”
我從納撒尼爾手上接過他的襯衫,掛在椅子的靠背上,“這兒?是指萊特-帕特森,還是指美國?”
“就是這兒。這兒是距離撞擊點最近的完整的基地。”
數字靜靜地擋在我們和撞擊點之間,距離大概是五百多英裏。
一大早我就首次瞥見了我們的老年生活。納撒尼爾幾乎無法獨立下床。地震時大部分磚石沙礫都砸到了他身上。他的背上滿是血腫和挫傷,比仿真人體模型更適合成為母親的醫學教學案例。
我也好不到哪兒去。記憶裏隻有一次比這次還難受,是我患流感的那個夏天。盡管如此,我還是能自己站起來,而且我相當肯定,隻要讓我四處走動走動,我的情況就能好很多。
納撒尼爾嘗試了兩次才勉強在床邊坐好。
“你該好好休息。”
他搖了搖頭,“不行,我可不想讓艾森豪威爾將軍被帕克所左右。”
我的傻老公伸出一隻手,我把他拉了起來,“我感覺艾森豪威爾將軍不是那種會被白癡左右的人。”
“如果陷入恐懼,即使天才也會犯蠢。”他站著咕噥了一聲,沒給我帶來任何信心。但我了解我的丈夫,他是那種會工作到死的人。他伸手去拿襯衫,疼得一縮。
我拿起他借來的浴袍遞給他,“你要先衝個澡嗎?也許能讓你放鬆一下。”
他點了點頭,讓我幫他穿上浴袍,慢吞吞向大廳挪動。我去廚房找林德霍爾姆太太。還沒走進廚房門,就聞到了培根的香氣,絕對不會錯。
我已經準備好每頓飯前都要聊天了。他們都是善良的人,如果不是他們,我們就得露宿田野了。嗯……這也許有點兒誇張,準確地說應該是睡在飛機上,但睡在飛機上也遠沒有現在好。接著我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培根變得無關緊要了。
“……忍不住想到那些和我一起上學的女孩們。珀爾就在巴爾的摩。”林德霍爾姆太太哽咽著。
“那裏現在……”
“抱歉——我真是個傻瓜。你想在吐司上加覆盆子醬還是草莓醬?”
等話題不再那麼嚴肅時,我走到了拐角處。林德霍爾姆太太在料理台前忙碌著,背對著我,擦了擦眼睛。
林德霍爾姆少校坐在廚房的桌子旁,右手鬆弛地扶著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他的左邊放著一份報紙,但他正眉頭緊皺地看著他的妻子。
他環顧四周,見我走進廚房,換上一副僵硬的笑臉,“希望我們昨晚沒有吵醒你。”
“納撒尼爾吵醒我了,不過這也沒什麼,不然我早上醒來的時候,脖子肯定僵硬得不行。”他遞給我一杯咖啡,我們進行了必要的寒暄。
一杯現煮咖啡帶來的快樂還需要我解釋嗎?我的嘴唇還沒碰到第一滴充滿誘惑力的微苦的咖啡,杯子裏冒出的濃濃香氣就已經喚醒我了。咖啡不隻是苦澀,這深色的液體還令人清醒,帶來撫慰。我歎了口氣,放鬆地坐在椅子上,“謝謝。”
“早餐想吃什麼?雞蛋?培根?吐司?”林德霍爾姆太太從櫥櫃裏拿出一個盤子。她的眼睛有點兒紅,“我還有葡萄柚。”
佛羅裏達州的柑橘園距離海岸線到底有多遠?“雞蛋吐司就行,謝謝。”
林德霍爾姆少校折起報紙,推到一邊,“那就對了。默特爾說你是猶太人,是戰爭期間過來的嗎?”
“不是,先生。哦——”林德霍爾姆太太把一盤雞蛋和吐司放在我麵前,我抬起頭來。雞蛋和著培根的油脂煎過,聞起來很香。該死的。我隻能用給吐司抹黃油的動作來整理思緒,“我們家在1700年代就舉家搬遷過來了,定居在查爾斯頓。”
“是嗎?”他嘬了一口咖啡,“戰前我從沒見過猶太人。”
“哦,你可能見過,隻是他們隱藏得很深。”
“哈!”他拍了拍膝蓋,“有道理。”
“實際上,我的祖母……”吐司和黃油需要我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我的祖母和她的姐妹們在家裏依然講意第緒語。”
林德霍爾姆太太坐在我旁邊的椅子上看著我,仿佛我是博物館裏的展品。“嗯,我從來不講。”皺起的眉頭加深了她額上的皺紋,“她們……呃,你提到查爾斯頓,她們有南方口音嗎?”
我操起我本來在華盛頓學著淡化的口音,“丫們想過猶太新年嗎?行,祝丫幸福。”
我用明顯的查爾斯頓口音說完了我知道的所有意第緒語,他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小時候我從不覺得這種口音聽起來奇怪,我以為那就是意第緒語的發音方式,直到我們開始去華盛頓特區的猶太教堂。
納撒尼爾出現在門口,他行動稍微自如一點兒了,“聞到好東西了。”
林德霍爾姆夫人跳了起來,給他安排了一個盤子。少校和和氣氣地寒暄了一番。我們所有人都拚命地假裝一切正常。但桌上的報紙印了一張紐約的照片,沒有窗子的摩天大樓矗立著,街道一片汪洋,儼然像是一座扭曲的威尼斯。
最後,林德霍爾姆少校看了看掛鐘,8點50分了。他挪開凳子,“哦!我們該走了!”
納撒尼爾跳了起來,“謝謝您的早餐,林德霍爾姆太太。”
“樂意效勞。”她親吻了丈夫的臉頰,“能和人交談而不是對著報紙背麵,真是太好了。”
他笑了,不難看出她為什麼會愛上他。“兩位女士今天有什麼安排?”他問。
“嗯……”她收起他和納撒尼爾的盤子,“我打算帶約克太太去城裏逛逛。”
“購物嗎?”我拿起其他盤子,跟著她走向料理台,“我一直計劃著和納撒尼爾一起去。”
她轉頭盯著我看,好像我剛剛突然說了希臘語一樣,“但你們倆都需要買新衣服。你的衣服我雖然洗了,但真的沒法兒再穿了,除非是收拾院子的時候。”
納撒尼爾肯定看見了我煎熬的表情,但搞不懂原因。我不是擔心錢的問題,世界剛完蛋,我卻被拉去逛街。“沒關係,埃爾瑪。在我們把我的雇傭狀況理清楚之前,帕克上校會給我們一筆衣服津貼。今天休息一下,去逛街吧。畢竟,你在基地也沒事可幹。”
問題就在這兒。我無事可幹。
林德霍爾姆太太把她的奧茲莫比爾汽車停在達頓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門前。店麵的遮陽篷有一條裂痕,商店的櫥窗裏展示著一條醒目的珠光色裙子,玻璃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沙塵。我下了車,看了看街上過著各自的生活的人們,仿佛昨天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不——這麼說並不準確。竊竊私語的人們三五成群,彼此站得異常的近。隔壁理發店降了半旗。到處都與商店玻璃一樣蒙著沙塵。我打了個冷戰,抬頭看著天空中古怪的土黃色薄霧。
林德霍爾姆太太看出我在顫抖,會錯意了,“快進屋,不然死神該來找你了。”
“哦,我很擅長死裏逃生。”
林德霍爾姆夫人臉色發白,“抱歉!我知道你經曆了什麼。”
有時候我的幽默並不能化解尷尬,這就是實例,“沒事,真的,沒關係。那隻是……我才應該道歉。那個笑話真沒品。”
“不,是我的錯。”
“說真的,別這樣,你沒什麼好道歉的。”
“我太欠考慮了。”
“我——”我頓住了,眯起眼睛,“我得提醒你,我是南方人。和我比禮貌,您永遠贏不了。”
她大笑起來,路上的人們紛紛側目,仿佛她在公眾場合罵街似的。“停戰嗎?”
“當然。”我指向門,“我們進去吧!”
她帶著笑意推開門,商店的鈴鐺叮當作響。女售貨員是一位六十來歲的黑人婦女,有一頭幹淨的白發。她站在一台收音機旁,專心地聽著。鈴鐺響起,她環顧四周,但眼神總是瞟向收音機。
“……昨日隕石襲擊引起的大火已蔓延三百五十平方英裏……”
她笑了,好像她剛想起該怎麼做,“有什麼我能幫您的嗎?”她把目光落在我身上,皺起了眉,不太明顯——隻能從她緊張的微笑裏發現端倪。
我的衛衣臟兮兮的,滿是怎麼洗也洗不掉的頑固汙漬。我看起來肯定很像流浪漢。媽媽會以我為恥。我咽了口唾沫,想回到車上去,但那樣會給林德霍爾姆太太帶來麻煩,所以我就隻好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前。
林德霍爾姆太太指著我說,“我朋友昨天在東部。”
在東部。聽了這種委婉的說法,女售貨員睜大了雙眼,憐憫地挑起了眉,“哦,可憐見的。”接著,好奇心隨之而來,仿佛被鮮血吸引的掠食者一樣。“你當時在哪兒?”
“波科諾斯。”
林德霍爾姆太太從架子上取下一件海軍藍的連衣裙比畫著,“除了身上的衣服,她啥也沒有。”
一名中年白人婦女出現在一排排衣服之間,“你當真在那裏嗎?你看到流星了嗎?”
“是隕石。流星在撞擊前就破裂了。”說得好像有人在乎科學的準確性似的。我想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糾正別人。“隕石,”怎麼看怎麼古怪的英語單詞,聽起來還挺可愛,“但我們沒在那兒,我們距離那兒還有三百英裏。”
她盯著我的臉,似乎我臉上的傷口和瘀痕能給她一張確定我位置的地圖,“我有家人在東部。”
“我也是。”我從架子上抓起一件衣服,逃進更衣室。百葉門在我身後關上了,隔斷了她們的視線,卻無法隔音。癱坐在矮矮的軟凳上,每一次呼吸都在抗議著要發出聲音,我用雙手捂住了自己的嘴。3.141 592 65……
“她和她丈夫昨晚飛過來的。據我所知,她的親人都死了,隻剩下一個哥哥。”
“太慘了。”
……3 589 793 238 4……每個人都可能認識某個“東部”的人。我不是唯一失去家庭的人。
女售貨員說:“我聽到新聞消息,由於萊特-帕特森在這裏,這裏還會湧進更多的流星難民。”
流星難民,說的就是我。隻不過我是這裏的人見到的第一個難民。忍了這麼久,眼淚終於還是掉下來了,非得在服裝店裏失控嗎?
“我老公也這麼說。”林德霍爾姆太太似乎就在我的更衣室門外,“我今天晚些時候要去基地醫院做誌願者。”
“你人真好。”
誌願者,我也能做。我可以開飛機運送東部的難民,可以包紮繃帶,或者別的什麼。戰爭期間我就做過這些,現在沒理由不重整旗鼓,重操舊業。
“你是不是在聽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台?”
我擦了擦眼睛,站了起來,伸手去拿我隨手帶進來的衣服。波點的,尺寸大小更適合瘦竹竿,而不是我。
“嗯……新聞裏剛說他們找到了一名幸存的內閣成員。各位女士不介意的話,我把聲音調大點兒。”
鏡子裏的我,仿佛食屍鬼來逛商店了。我以為我看上去像流浪漢,但實際上,我看起來似乎還沒真正逃離災難。我的雙眼發黑,臉上、手臂上布滿傷口。有什麼東西打中了我,發際線正下方還留著擦傷。但我還活著。
“……潮汐波淹沒了加勒比海地區,當地許多國家斷水斷電。據說死傷人數高達數十萬……”
我打開更衣室的門,試圖忽略收音機的聲音,“我太傻了,拿錯尺碼了。”
那位女售貨員過來幫我,我們就著新聞播報的背景音,討論起了衣服尺寸和當下的時尚,仿佛事不關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