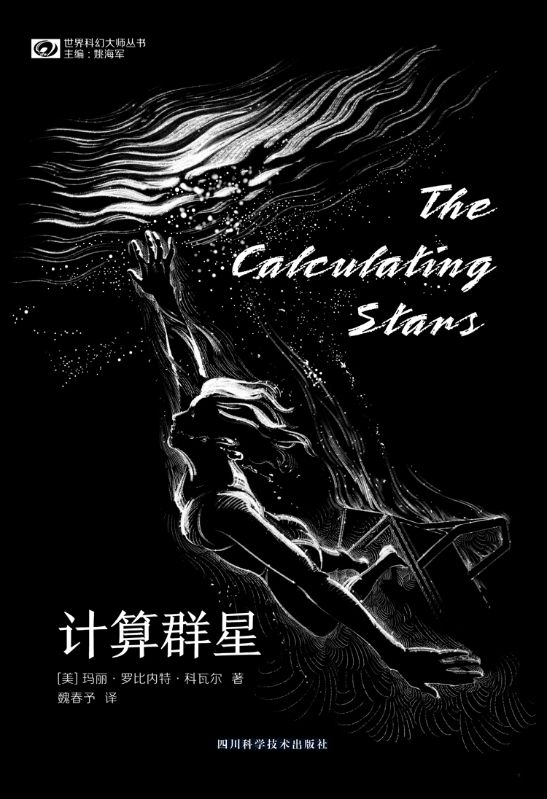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四章
伊朗地震造成九十人死亡
路透社伊朗德黑蘭1952年3月3日電伊朗南部的拉裏斯坦和巴斯塔克發生地震,造成九十人死亡,一百八十人受傷。德黑蘭廣播台今日宣布,地震是由北美洲的隕石墜落引發的。
太陽在鮮豔的朱紅色、赤銅色和暗金色的條狀晚霞中落山。看著頭頂這火紅的天空,我們仿佛被傳送到了火星。萬物都鋪上了紅潤的光,甚至連林德霍爾姆少校家的白色尖木柵欄看上去都像是浸滿了鮮血。
一般來說,我討厭給別人添麻煩,但是帕克惹惱了我。而且,我太累了,說真的,累到無法思考,我很感激有個人能告訴我該去哪兒。再說,他們後麵還需要用TLF接納難民。
納撒尼爾還在忙著開會。不過他為了勸我離開,已經溜出來好長一段時間了。我呢,也確實沒有留在基地的理由——除非我確信,一旦離開,我將再也見不到他。這些理由都沒法兒大聲說出口,至少不適合在今天這樣的日子裏說。
我下了吉普車,衣服上汙漬的顏色似乎加深了。我仿佛能聽到我媽的嘮叨:“埃爾瑪!人們會怎麼想?”
我緊緊抓住吉普車的門,忍住悲傷。至少我洗過臉了。我直起身來,跟隨林德霍爾姆少校穿過柵欄,沿著整齊的小路來到前廊。我們拾級而上時,門開了,一個穿著粉藍色連衣裙的豐滿女人走了出來。
她的膚色不比納撒尼爾夏天的時候深,五官給人一種柔軟、圓潤的感覺。我有點兒驚訝地意識到我以前從未拜訪過黑人的家。林德霍爾姆太太將一頭鬈發梳得蓬蓬鬆鬆,勾勒出她淺棕色臉頰的曲線。眼鏡後的雙眼因憂慮而泛紅,還透露著不安。
她拉開門,一手按在胸前,“哦,可憐見的,快進來。”
“謝謝您,女士。”地麵鋪著嶄新的仿磚油氈。我的鞋太臟,已經看不清本來的顏色了,“我還是把靴子脫掉吧。”
“沒關係的。”
我就著台階坐下脫鞋。媽媽要是知道我滿身汙垢地進別人家,她會為我感到羞恥的。“我老公待會兒帶進來的汙垢就夠我們清掃的了。”
她聞言笑了,“看來天下老公都一個樣兒?”
“我還在這兒呢!”林德霍爾姆少校在我旁邊的台階上停住腳步,“不過如果您需要什麼,請告訴我們,任何需求都行。我保證約克博士會平安無事地回到這裏。”
“謝謝。”如果再讓我多看看他善意的麵孔,我的情緒就會徹底失控。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隻靴子上。我的襪子很臟,腳也幹淨不到哪裏去。
林德霍爾姆太太走了幾步來到前廳,“我有三個兒子。相信我,這點兒汙垢不是事兒。”
我沒有流淚,至少目前還沒有。短促的呼吸阻止了我“洪水泛濫”。我咽下淚水,抓住欄杆,赤腳站起來,“我真的感激不盡。”
“哦,我什麼都還沒做呢。”她抬手靠近我的背,卻沒真正碰到我。她領我進了屋,“現在……我猜你最想做的事就是洗個熱水澡。”
“這種時候我想衝個冷水澡。”
前門正對著她的起居室。所有的家具都整整齊齊地按照直角擺放,甚至小擺件兒的位置也跟架子和桌子的邊緣對齊。空氣中散發著家具清潔劑的檸檬味,還混合著肉桂香。
“要洗冷水澡,你該待在軍營裏。”林德霍姆太太從客廳匆匆走過大廳,打開了右手邊的第一扇門。一個帶爪形支座的浴缸占據了浴室的大部分麵積。
“我有泡泡浴液,薰衣草和玫瑰的。”
“我還是想先衝個澡。”
她扶了扶眼鏡,看了看我衣服上和裸露皮膚上的汙垢,“嗯……好吧。但衝完以後,你要好好泡一泡,聽到了嗎?不然明天你指定會渾身酸痛。”
“好的,夫人。”她說得沒錯。鑒於目前的情況,明天能順利起床才怪。
“好了。這是你的毛巾,還有一套我大兒子的睡衣。”她把手放在一套紅色法蘭絨睡衣上,“我的睡衣對你來說太寬鬆了。把你的衣服放在櫃子上就行,我來洗。”
她忙忙碌碌地走出房間時,我對她點了點頭,希望她能明白我的謝意。
我確實需要她幫我洗衣服,不然我就沒有衣服穿了。不是像名媛淑女初次亮相那種難以抉擇的“沒有衣服穿”,而是字麵意義上的客觀事實。我們是難民。我們的家,我們的工作,我們的銀行,我們的朋友,在隕石撞擊的瞬間,一切都毀了。
如果納撒尼爾不是一名火箭科學家——如果帕克不需要他——我們又會在哪裏?我想到過跟戈德曼先生結局一樣的人,但從沒想過逃過一劫的人該何以為繼。處於毀滅邊緣的成百上千的人又該何去何從?
我穿過雲霧般的蒸汽,走出浴室。穿著借來的法蘭絨睡衣躡手躡腳地走過客廳。這褲子很適合我,因為我腿還挺長,不過睡衣袖子一直垂到了我的手指。我邊走邊挽起袖子,手指上數不清的劃痕摩擦著柔軟的布料。我的大腦仿佛一片空白。
我想我還處在震驚中,意料之內的事。不過至少這種震驚不再體現為身體發抖了。就好像所有的東西都被棉花包裹起來了。
起居室裏,電視開著,但調低了音量。林德霍爾姆太太把椅子拉到靠近屏幕的地方。她弓著身體,眼睛緊盯著新聞,雙手緊緊攥著一塊手帕。
在忽明忽暗的黑白畫麵中,愛德華·R.莫羅手指夾著香煙坐在新聞桌後,談論著今天發生的事。
“……今日隕石襲擊後的最新死亡人數為七萬,預計該數字仍會增長。據報道,馬裏蘭州、特拉華州、賓夕法尼亞州、紐約州、新澤西州、弗吉尼亞州,一直到加拿大,甚至東部沿海的佛羅裏達州,已經有五十萬人無家可歸。這些圖像是在災難發生大約五個小時後通過飛機拍攝的。女士們,先生們,您現在看到的地方,曾是我們國家的首都。”
屏幕上出現了一片水域,像間歇泉一樣不斷冒泡。鏡頭轉向地平線,水域的範圍變得清晰起來,我不禁猛地吸了一口氣。黑色土壤形成了一片直徑數百英裏的環狀焦土。在沿海地區,切薩皮克灣的河岸不是被淹沒,而是完全不複存在了。我看著大海。
大海熱氣蒸騰。
我深吸一口氣,仿佛有人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
林德霍爾姆太太坐在椅子上轉過身來,我感覺得到,她正在收拾自己的震驚,整理好悲傷的情緒,這樣才能繼續做好一個女主人。“哦!你看起來好點兒了。”
“我——是的……”我朝電視走近一步,既驚駭,又被新聞所吸引。
“東海岸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陸軍、海軍、空軍和紅十字會已經開始行動,援助有需要的難民。”
鏡頭切換到救援人員組織難民的畫麵。背景中,一個胳膊被燙傷的小女孩正跟在母親身旁蹣跚地走著。畫麵又一轉,轉到一片曾經是小學的廢墟。孩子們的屍體……隕石一定是晨間休息時撞擊地球的。我以為我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會比現實更糟。簡直大錯特錯。
林德霍爾姆太太關掉了電視,“到此為止。你沒必要看這個。你需要的是一頓晚餐。”
“哦,我不想給您添麻煩了。”
“瞎說。你要是個麻煩的話,我就不會叫尤金帶你來了。”她起身時將手帕塞進了裙子的腰帶裏,“到廚房裏來,我給你整點兒吃的。”
“我——謝謝你。”作為不請自來的客人,我的禮貌本能與應該吃些東西的簡單事實相衝突,雖然我還不餓。而且,萬一她的觀念跟我媽有所相似——我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萬一她的觀念跟我媽有所相似,那麼拒絕她的食物就會顯得我有些不近人情。
我赤腳踩在地上,廚房的油氈地板很涼。牆壁被漆成了薄荷綠色,幹淨整潔的台麵上懸著純白的吊櫃。是他們告訴她我要來她才打掃了房間,還是這裏一向這麼整潔?她打開冰箱時,我想答案應該是後者。
她肯定有一個賣特百惠的朋友,也可能是她自己在賣。食物全部放在顏色相配的保鮮盒裏。要不是我剛才注意到她看電視時眼睛裏的震驚和憂傷,我會覺得她剛剛從通用電氣的廣告裏走出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火腿芝士三明治怎麼樣?”
“哦……能隻要芝士嗎?”
“在經曆了這樣的一天以後嗎?你需要補充點兒蛋白質。”
媽媽說結束話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講一句:“我們是猶太人。”
她站直身子,揚起眉毛,“真的嗎?嗯……我不知道該怎麼招待你們比較合適。”
她本是好心,我知道的。我必須相信這一點,因為我在她家做客,又無處可去。我咽了口唾沫,露出微笑,“呃,隻要芝士就可以了。”
“那金槍魚要嗎?”
“聽起來很棒,如果不會太麻煩你的話。”我和納撒尼爾其實都來自不忌口的猶太家庭,但是戰爭爆發後,我就不再吃豬肉和貝類了。這些猶太教教規,別的方麵不說,至少能幫我認清自己,還能告訴我認清自己有多重要。
“一點兒也不麻煩。”她從冰箱裏拿出一個淡粉紅色的保鮮盒,“尤金午餐總是要吃金槍魚,我習慣多做一些備用。”
“我可以幫你做些什麼嗎?”
“坐著就行。”她又拿出一個綠色的保鮮盒,“比起一樣一樣地說明東西擺放在哪兒,直接動手做要來得輕鬆得多。”
冰箱旁的牆上掛著一部暗棕色的壁式電話。不知怎麼的,我一看見它就好像被滿載愧疚感的磚塊砸中了似的,“我可以……我不想打擾你,不過我可以借你的電話用一下嗎?我想打個長途,但是……”我越說越小聲,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報答她。
“當然,需要我回避嗎?”
“不用,沒關係。”我在說謊。事實上我非常看重隱私,但我已經得到太多,不想再麻煩她了,“謝謝你。”
她把三明治配菜隨意地扔在台麵上,指著電話說:“這不是同線電話,你不必擔心有人會聽到。留在少校家的好處之一,對吧?”
我走向電話,多希望它安裝在房子的另一個房間,或者希望我有勇氣告訴她真相。撥號以後我又聽到那該死的忙音。我盡量控製自己不罵臟話。嗯……至少不大聲罵。
我又試了一次,這回電話撥通了。
我如釋重負,所有的力量都被抽走了,隻好靠著牆。電話鈴每響一聲,我都會祈禱:請一定要在家。請一定要在家。請——
“你好,這裏是韋克斯勒家。”我哥的聲音既平靜又沉穩。
我的聲音有些嘶啞,“赫舍爾?我是埃爾瑪。”
聽筒裏傳來一聲粗喘,接著是長途電話特有的劈啪聲。
“赫舍爾?”
我從來沒聽過我哥哭,甚至在他膝蓋骨折的時候也沒有。
背景聲音裏,我聽到他的妻子多麗絲在詢問什麼——問的可能是“怎麼了?”
“是埃爾瑪。天哪!她還活著。哦!感謝上帝。她還活著!”他的聲音回到了聽筒裏,“我們看到了新聞,他們……爸媽怎麼樣?”
“不知道。”我用手遮住雙眼,額頭抵著牆。身後的林德霍爾姆太太做著三明治,出奇地安靜。我不得不從喉嚨裏擠出話來,“當時,納撒尼爾和我出城了,爸媽在家。”
他的呼吸在我的耳邊顫抖,“但你和納撒尼爾還活著。”
“你知道……查爾斯頓情況如何嗎?”
“潮汐波襲擊了查爾斯頓,不過很多人都成功撤離了。”接著他回答了我真正想問的問題,“我們沒有收到奶奶的消息,也沒有姑媽們的消息。”
“嗯……我也是花了些時間才打通電話的。”
多麗絲說了些什麼,赫舍爾的聲音低沉了片刻,“什麼?好……好,我問問。”
他的妻子一向比較有條理,甚至在他們戀愛的時候也是如此。我笑了,默默地想象著她可能正在羅列的問題清單。
“你在哪兒?需要什麼幫助?受傷了嗎?”
“我們在俄亥俄州的萊特-帕特森基地。嗯,實際上是在林德霍爾姆家裏,他們今晚收留了我們,所以沒什麼需要擔心的,他們很照顧我。”我回頭看了一眼。林德霍爾姆太太將三明治切成整齊的四塊,還削掉了麵包皮。
“其實我該掛電話了,因為我用的是她的電話。”
“下回你打被呼叫方付費的那種。”
“我明天再打,如果不占線的話。替我向多麗絲和孩子們問好。”
我掛斷電話,頭靠著牆,似乎薄荷綠的塗料可以讓我頭腦冷靜。我想我隻靠了一小會兒。
一張椅子吱吱作響,或許是林德霍爾姆太太坐下了。於是我收拾好情緒,站直身子。爸爸常說,對於一名軍官或一位女士來說,舉止儀態很重要。“謝謝。我哥一直很擔心。”
“換作是我肯定也會的。”她把三明治放在一個亮青色盤子上,然後把盤子放在了餐墊中間。盤子旁邊放著一杯水,杯壁掛著凝結的水珠。
簡單樸素的廚房、牆上滴答作響的時鐘、發出嗡嗡聲的冰箱、眼前這位親切的女性,還有她的三明治、餐墊和法蘭絨睡衣,似乎與我這一整天的世界格格不入。電視上那些被灼燒的孩子們的畫麵就像是在火星上拍攝的一樣。
我坐下時椅子嘎吱直響,我的關節因挫傷而疼痛。正如我被教養的那樣,我把餐巾鋪在腿上,拿起了第一塊切開的三明治。我是幸運的,有一架飛機,有一條活路。
“三明治還行嗎?”
不知不覺中我已經吃掉一塊了。嘴裏隻有死魚和變質醬菜的味道。我朝女主人微笑道:“美味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