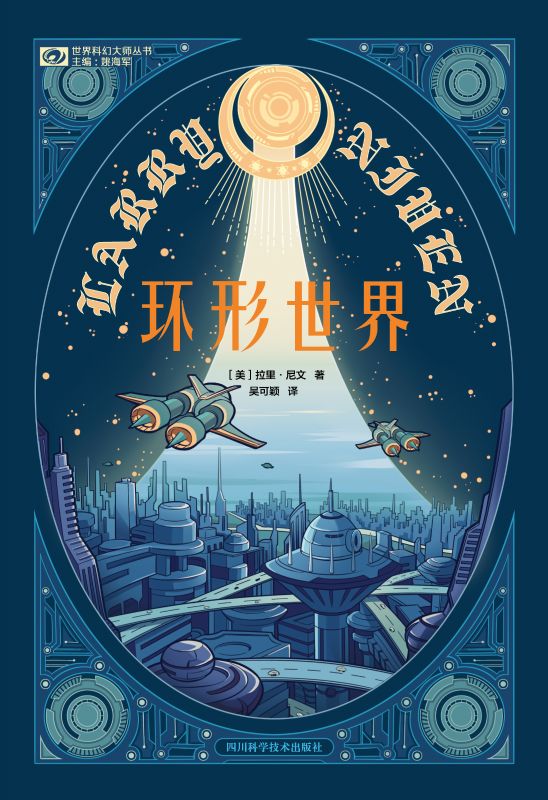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他和他的雜牌軍
路易·吳知道,有的人用傳送亭時會閉上眼睛,因為景物的跳躍轉換會讓他們眩暈。在路易看來,這麼做很荒謬可笑。但話說回來,他有的朋友要比這怪誕多了。
他撥號時睜著雙眼。身邊盯著他看的外星人瞬間就不見了。突然他聽到有人喊:“嘿,他回來了!”
門口聚集起了一堆人。路易用力推開他們,大聲罵道:“你們這些沒腦子的!都還沒有回家啊?!”他張開雙臂去擁抱他們,然後又像鏟雪機一樣向前擠,把人們往後身推,“別堵著門,你們這些土鱉!我還有客人要進來呢!”
“好極了!”一個聲音灌入他的耳朵。不知誰抓住了他的手,塞給他一個圓酒杯。路易剛剛張開雙臂,就立刻擁抱了七八個請來的客人,同時用微笑表示歡迎他們。
從遠處看,路易·吳長著一副東方人的模樣,淺黃的皮膚,筆直的白發。他那顏色鮮亮的藍袍子隨意地拖垂著,看起來礙手礙腳的,但實際上並沒有。
如果走近了看,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是假象。他的皮膚並不是淺淺的黃褐色,而是光滑的鉻黃,漫畫書中傅滿洲(1)的那種膚色。他的辮子很粗,白頭發也不是因為上了年紀的緣故,而是呈現出一種絕對幹淨的白,其中夾著一絲難以察覺的藍色,那是矮星光芒的顏色。像所有的平地人一樣,路易喜歡用化妝品打扮自己。
他是個平地人,你一眼就能認出來。他的五官既不像白種人、黃種人,也不像黑人,卻帶有這三個人種的痕跡:好多個世紀才能形成這種均勻的混合外形。在這顆重力加速度為每秒9.98米的地球上,他的站姿十分自然,毫不刻意。他正握著一個酒杯笑眯眯地看著身邊的客人。
湊巧的是,他笑意盈盈的目光正對上了一雙銀光閃閃的眼睛,那雙眼睛離他僅有一英寸遠。
一個叫蒂拉·布朗的女人不知怎麼就跟他鼻子碰鼻子、胸口頂胸口了。她有著藍色的肌膚,身穿銀線針織網眼衫;發型像熊熊燃燒著的篝火;眼睛則像一對凸麵鏡。她才二十歲。路易以前跟她說過話。她談吐膚淺,全是陳詞濫調,而且特別容易激動;不過人倒是非常漂亮。
“我得問問你,”她屏住呼吸說,“你是怎麼弄來一個泰諾克人的?”
“別告訴我他還在這裏。”
“哦,他已經不在了。他的空氣用完了,不得不回家。”
“你撒了個善意的謊,”路易指出,“泰諾克人的呼吸儀能管好幾個星期。不過,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這事,我可以告訴你。你所指的那個泰諾克人曾經是我請來的客人,他在我這裏滯留了幾個星期。他的飛船覆沒在已知空間的邊緣,船上的其他夥伴也全死掉了,我不得不把他護送到馬格雷夫星球,在那裏他們可以建個環境箱讓他存活。”(2)
女孩的眼中閃爍著愉悅和好奇。路易發現他們兩人的眼睛在同一高度上,這讓他感到既奇怪又開心;原來蒂拉·布朗那柔嫩的美貌讓她看起來比實際上要嬌小。突然,她的目光越過路易的肩膀,眼睛睜得大大的。路易咧嘴笑著轉過身去。
隻見傀儡師涅索斯從傳送亭匆匆走了出來。
當他們離開克魯申科斯飯店時,路易就料到會有這種情形。他曾試圖說服涅索斯多跟他們講講有關探險目的地的事,但涅索斯擔心飯店有間諜電波竊聽到他的話。
“那就到我家來談吧。”路易向他提議。
“可你有客人啊!”
“我的辦公室裏沒有客人,而且我的辦公室是絕對防竊聽的。想想看,如果大家還都沒回家的話,你出現在派對上將引起多大的轟動啊!”
這效果正是路易求之不得的。傀儡師那“啪嗒-啪嗒-啪嗒”的蹄聲成了房間裏唯一的聲音。接著,在他的身後,動物對話官的身影也突然閃現出來。麵對傳送亭周圍那一張張人臉的海洋,這克孜人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慢慢地咧嘴露出了他大大的獠牙。
有人把剩下的半杯飲料倒在一個栽著棕櫚樹的花盆裏。這是一個誇張的姿態。樹枝上有一隻甘米吉蘭(3),它生氣地吱吱叫起來。傳送亭外的人們向後退開。有人說:“你沒醉。我也看到他們了。”
“醒酒藥?讓我看看口袋裏有沒有。”
“他搞的這個派對真他媽牛,對吧?”
“好啊,路易,你這個老東西!”
“你知道那玩意兒叫什麼嗎?”
他們不知道該對涅索斯作何反應。大多數人都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他們不敢議論他,怕說出傻話。他們對動物對話官的反應則奇怪得多。克孜人曾經是人類最危險的敵人,但眼前這個克孜人受到人們的恭敬對待,像個英雄似的。
“跟我來。”路易對傀儡師說。要是大家運氣好,那克孜人應該也會跟上他們倆。“對不起,讓我們過去。”路易一邊大聲說著,一邊在人群中撥開一條路。人們或激動或迷惑地提出各種問題,他都隻是神秘地咧嘴一笑。
他們總算到了路易的辦公室,這下子安全了。路易關上門,打開防竊聽裝置,“行了。誰想來點兒喝的?”
“如果你能熱點兒波旁威士忌,那我可以喝點兒。”克孜人說,“但如果你熱不了,我也能接受。”
“涅索斯,你呢?”
“什麼蔬菜汁兒都行。你有溫的胡蘿卜汁兒嗎?”
“真難伺候。”路易應道,但他還是吩咐吧台做了幾杯溫熱的胡蘿卜汁兒送過來。
涅索斯盤坐在後腿上休息,克孜人則重重地跌坐在一個充氣坐墊上。依他的重量,那坐墊早該像個小氣球一樣爆開了。這個人類第二古老的敵人,現在端坐在一個對他來說實在太小的坐墊上,樣子既古怪又可笑。
人類與克孜人之間發生過無數戰爭,血腥而殘酷。所幸當年在第一場戰爭中克孜人就輸掉了,否則在餘下的無盡歲月裏,人類就隻能當他們的奴隸和食材了。而且,在接下來的所有戰爭中,克孜人吃盡了苦頭。他們總是喜歡不備而戰,完全沒有耐心,沒有憐憫心,也沒有戰爭範圍的概念。每一場戰爭都會讓他們數量大減,作為懲罰,還要搭上幾個星球的領地。
克孜人已經有二百五十年沒有進攻人類的空間了,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跟人類較量了。人類也有二百五十年沒有進攻過克孜人的世界了,卻沒有哪個克孜人能理解這是為什麼。人類總讓他們摸不著頭腦。
總之,他們是粗暴而強悍的種族。而涅索斯,他來自一個公認膽小的種族,卻竟敢在一個餐廳公然侮辱四個彪悍強壯的克孜人。
“你們傀儡師一族的特點就是小心謹慎吧?這是眾所周知的,對吧?”路易說,“再跟我講講這些,我忘了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路易,也許這對你不夠公平,因為我沒有徹底跟你交底。我的族人都認為我瘋了。”
“哦,沒關係。”路易端起杯子吸了一口,那杯子是剛才不知誰塞到他手裏的,裏麵是伏特加,兌了漿果汁和刨冰。
克孜人的尾巴不安地甩來甩去,“憑什麼我們要跟一個自認是瘋子的人同船?你竟然想跟一個克孜人同船,那一定是瘋到家了。”
“你不用這麼大驚小怪,”涅索斯說道,他的聲音溫柔而有說服力,好聽到讓人受不了,“在人類遇到過的傀儡師中,從來沒有哪個不是被他的同類視為瘋子的。從來沒有外來種族見識過傀儡師的世界,也從來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傀儡師會把自己的命交托給飛船那不可靠的維生係統,或是跑到一個可能有致命危險的未知的外星世界去。”
“一個瘋子傀儡師,一個凶猛的成年克孜人,還有我。我們的第四位隊員最好是一個精神病醫生才行。”
“是啊,可不就得這樣?”
“我可不是隨便挑的。”傀儡師用一張嘴吮吸著杯子裏的飲料,用另一張嘴繼續說,“首先,這個隊必須有我本人。這趟探險是為了我族利益,因此必須包括我們的代表。這個代表必須瘋狂到敢於麵對一個未知的世界,但同時又有足夠的理智,能靠他的智慧生存下來。我,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傀儡師,瘋狂和理智都恰到好處。”
“我們要挑一個克孜人也是有道理的。聽著,動物對話官,我現在跟你說的可是機密。我們觀察你們族類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我們甚至在你們進攻人類以前就知道你們的存在了。”
“那時沒露麵算你們幸運。”克孜人咕噥道。
“毫無疑問,我們知道你們的存在。開始我們推斷克孜是個既沒用又危險的物種。我們進行了許多的研究,就想看看是否可以安全地滅絕掉你們這個種族。”
“看我不把你脖子擰成一個蝴蝶結。”
“相信你不會使用暴力的。”
克孜人站了起來。
“他是對的。”路易說,“坐下吧,對話官。殺死一個傀儡師,你也用不著站起來啊。”
克孜人坐了下來。那個充氣坐墊依然沒有爆。
“那些研究項目後來被取消了。”涅索斯接著說,“我們發現人類與克孜人的戰爭已大大地限製了克孜人的擴張,使你們的危險性大打折扣。但我們對你們的觀察仍在繼續。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你們一共進攻人類世界六次。六次都被打敗了,每次戰爭你們都會損失大約三分之二的雄性人口。需要我點評一下你們展現的智力水平嗎?不需要?但不管怎樣,你們從來都沒有瀕臨滅絕。你們的雌性缺乏感知,基本上沒受到戰爭的影響,因此下一代的數量很快就能夠彌補上一代的損失。盡管如此,你們還是在不斷地失去領土,那是你們經營了數千年才建立起來的帝國的領土。
“在我們看來,很明顯克孜人是在快速地進化。”
“進化?”動物對話官問道。
涅索斯突然用英雄語大吼一聲。路易跳了起來。他完全沒料到傀儡師的喉嚨居然可以發出那樣的吼聲。
“是的。”動物對話官應道,“我想你剛才說的就是那個詞。但我不知道它在這裏的意思。”
“進化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在幾百個克孜紀年的進化過程中,因適應環境而生存下來的是那些有智慧的或者能夠克製情緒、不跟人類交戰的成員。結果顯而易見,那就是克孜和人類之間的和平已經持續兩百個克孜紀年了。”
“但這毫無意義!我們一場戰爭都沒贏!”
“但你們的祖先並沒有因此止步不前。”
動物對話官吞了一大口熱波旁威士忌。他粉色的尾巴光溜溜的,像老鼠尾巴,一個勁兒地甩來甩去,躁動不安。
“你們種族的數量已經大大消減了,”傀儡師道,“如今活下來的全是那些在交戰中沒死的克孜人的後代。我們有人推測,或許克孜人現在已經具備了必要的智慧,或者同理心,或者自我約束力,可以跟不同於他們的外星種族來往了。”
“所以你才敢冒著生命危險跟一個克孜人去旅行?”
“對,”涅索斯答道,渾身哆嗦了一下,“我有很強烈的動機。如果我能證明我的勇氣是有價值的,它可以為我的種族提供有價值的服務,我就將會被允許生養後代。”
“這可算不上一個信得過的理由。”路易說。
“我們要帶上一個克孜人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將會麵對陌生的環境、潛在的各種危險。誰能保護我呢?有誰能比一個克孜人更能勝任保鏢這一職位呢?”
“保護一個傀儡師?”
“這聽起來很荒謬嗎?”
“的確如此。”動物對話官說,“荒謬得使我發笑。那麼這位又是怎麼回事?這位路易·吳是幹嗎的?”
“我們跟人類的合作受益很多。自然我們就會選擇至少一名人類。路易·格裏德利·吳,別看他自在隨性、膽大妄為,他可絕對是適者生存的典型,這一點確鑿無疑。”
“他的確是自在隨性、膽大妄為,居然敢找我單挑。”
“如果赫羅斯沒有出來道歉,你真的會接受他的挑戰嗎?你真的會傷害他嗎?”
“然後惹出一場種族衝突,顏麵掃盡,被遣送回家嗎?我又不傻。所以這些都不能說明問題。”克孜人強調道,“你覺得呢?”
“我恰恰認為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你看路易還活著。你現在該明白光靠恐嚇是鎮不住他的。這個結果很能說明問題。”
出於謹慎,路易·吳始終一言不發。如果傀儡師想誇獎他有冷靜思考的能力,他何必反對呢?
“你已經說了你的動機了。”動物對話官說,“現在該說說我的了。加入你們的航行,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他們這才切入正題,談起了生意。
在傀儡師的世界,量子二號超光速引擎沒什麼大用。不過它可以驅動一艘飛船在一又四分之一分鐘內飛過一個光年,而一艘傳統的飛船得用三天時間才能走完這段距離。但傳統飛船卻有巨大的貨艙。
“我們把這個引擎裝到了一艘‘眾品四號’(4)的船體上,這是我們公司造出來的最大的飛船。可是當我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完工的時候,才發現船體內部幾乎被那個超光速引擎占滿了,所以我們這趟外出旅行開著它,你們一定會覺得船裏的空間非常狹窄。”
“這麼說它是艘實驗性的飛船。”克孜人說,“它經過試航?”
“這飛船曾往返過銀河係中心。”
但那是它唯一的一次飛行。傀儡師不能親自試飛,他們也找不到其他族類的人幫他們試飛;那時他們正處在遷徙的途中。盡管這艘飛船的直徑超過一英裏,卻一點兒貨物都不能裝載。另外,它隻有先返回正常空間才能減速。
“我們已經不需要它了。”涅索斯說,“但你們需要。我們打算把這艘飛船連同該船的設計圖送給我們的船員,這樣你們就能多造幾艘了。毫無疑問,你們還可以改進它。”
“這船能為我掙得一個名字。”克孜人說,“一個名字啊!我一定得看看這船開起來是什麼樣兒的。”
“在這趟飛行中你自然會見識到。”
“族長會因為這艘船給我一個名字的。我堅信他一定會這麼做的。我應該選個什麼名字呢?要不就叫……”克孜人提高嗓門嚎叫起來。
傀儡師用同樣的語言回應他。
路易不耐煩地換了個姿勢。他聽不懂英雄語,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他想,就讓他們倆聊下去好了。就在這時,他有了一個更好的主意。他把傀儡師那張全息照片從口袋裏掏出來,打水漂似的把它撇了過去,照片飛過屋子,落在克孜人毛乎乎的大腿上。
克孜人靈巧地用他那長著肉墊的黑指頭將它拿了起來。“這看著像是一顆帶環的星球。”他一邊端詳一邊說,“這是什麼東西?”
“這跟我們要去的地方有關。”傀儡師回答道,“我不能跟你多說,至少現在還不能。”
“看你搞得神秘兮兮的。好吧,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估計也就是幾天的事情吧。我的代理人還在尋找第四位隊員呢。”
“那我們就等他們找到人再說吧。路易,我們可以去找你的客人玩玩嗎?”
路易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沒有問題,我們這就去給他們一個驚喜。不過,對話官,去之前,我想提個建議,別把這看成是侮辱你的尊嚴。這隻是個想法……”
派對上的人分成了幾撥:有看三維電視的,有打橋牌和撲克的,有成雙成對的情侶或紮堆兒的情侶,有講故事的,也有百無聊賴的。在室外的草坪上,清晨朦朧的陽光下,窮極無聊的人們和愛湊熱鬧的人們混坐在一起,其中包括涅索斯、動物對話官、路易·吳、蒂拉·布朗,還有一個累壞了的酒吧服務生。
草坪是按照英國古典花園打理的:從最初播下的草籽到現在已經過了五百年。這五百年的曆史被一場股市崩盤中斷了,之後路易·吳就發了財,而某個封了爵位的古老世家卻破了產,於是這草坪就到了路易·吳的手裏。草綠油油的,顯然是貨真價實的天然草;從來沒人動過它的基因去搞什麼不靠譜的改良。在那一片綠色的斜坡下麵是一個網球場,遠遠望去,一些小小的身影在跑動跳躍,用力揮舞著手裏超大尺寸的“蒼蠅拍”。
“運動真美妙。”路易說,“我可以坐在這裏看一整天。”
蒂拉大笑起來,讓他吃了一驚。他不由得地想起許多她從沒聽過的笑話——很老很老、老到不再有人講的笑話。在路易熟記於心的幾百萬個笑話中,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已過時了吧。過去和現在的笑話都在記憶中混為一體了。
酒吧服務生飄到路易身邊,彎腰站著。路易的頭枕在蒂拉的大腿上,他不願意坐直身子敲鍵盤,這姿勢讓服務生不得不傾斜著身子。他敲鍵要了兩杯摩卡咖啡,咖啡從槽中落下來,他及時抓住,將其中一杯遞給了蒂拉。
“你很像我以前認識的一個女孩。”他說,“聽說過寶拉·切倫科夫嗎?”
“是那個漫畫家嗎?波士頓人?”
“是她。她現在住在‘安抵星’(5)上。”
“她是我的高曾祖母。我們曾經去看望過她一次。”
“她曾讓我心如刀絞。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你跟她長得就像一對雙胞胎。”
蒂拉咯咯地笑起來,全身顫動著,這顫動沿著路易的脊椎傳遞開來,令人愉快。她說:“我發誓絕不會讓你‘心如刀絞’,不過你得告訴我那是怎麼回事。”
路易回想了一下。“心如刀絞”這詞兒是他自創的,僅僅為了向自己描述當年的遭遇。他不常使用它,也從來不需要解釋它。人們總是能明白他想表達的意思。
這是一個安靜祥和的早晨。如果他這會兒去睡覺,他可以一覺睡它十二個小時。然而,過度疲勞卻像毒藥,讓他在精疲力竭中興奮到頂點。再說,他的頭枕在蒂拉的大腿上還是怪舒服的。路易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女人,在某些年月裏,她們當中的一些人曾經是他的妻子或者情人。在派對的第一階段,他私下裏跟三個女人慶祝了他的生日,這三個女人曾經對路易非常重要,路易對她們也是如此。
三個?四個?不對,應該是三個。現在他好像對那種“心如刀絞”的感覺有了免疫力。二百年的時光給他留下了太多的傷疤。此刻,他正無所事事、舒舒服服地把頭枕在一個跟寶拉·切倫科夫長得一模一樣的陌生人的腿上。
“我那時愛上她了。”他說,“我們已經認識好幾年了,還約過會。有一天晚上我們在一起聊天,突然‘嘭’的一下,我墜入了愛河。我以為她也愛上了我。
“那天晚上我們沒有上床——我的意思是,沒有一起上床。我請求她嫁給我,可她拒絕了我。她那時正是打拚事業的時候。她說,她沒有時間結婚過家庭生活。但我們還是安排了一個旅行計劃,去亞馬孫國家公園,為期一周,算是代替蜜月旅行吧。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簡直像坐過山車。首先是興奮,我拿到機票了,也訂到了旅館。你有過為某人神魂顛倒的時候嗎,覺得自己根本配不上她?”
“沒有。”
“我那時太年輕了。我花了兩天的時間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我是值得寶拉·切倫科夫愛的。我還做了些事情證明這點。然而她卻打電話過來取消這趟旅行。我都記不得是為什麼了,總之她說了個能成立的理由。
“那個星期我帶她出去吃了幾頓飯,但這並不能讓她改變主意。我盡量克製自己,以免給她造成壓力。她卻連想都不想我當時所承受的壓力。我的情緒就像悠悠球一樣忽高忽低。這時她重重地給了我一擊,讓我徹底失去了幻想。她說她欣賞我,我們在一起很快樂,我們應該永遠是好朋友。
“但我不是她喜歡的類型。”路易道,“我還以為我們在戀愛呢。或許她也曾這麼認為過,但隻持續了一周。她並非冷酷無情。她隻是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你剛才說的‘心如刀絞’又是什麼呀?”
路易抬頭看著蒂拉·布朗。那雙銀色的眼睛茫然地看著他,路易意識到,她壓根兒一個字都沒聽懂。
路易跟外星人打過不少交道。憑借直覺或通過訓練,當有些概念太陌生、太異質而無法理解或交流時,他是能察覺出來的。眼下就是一種類似的情形——他們之間有一種無法逾越的隔閡。
這是多麼巨大的鴻溝啊!它就橫在路易·吳跟一個二十歲的女孩之間。他真的老得那麼厲害嗎?如果真的如此,那他路易·吳還算是人類嗎?
蒂拉眼中一片空洞茫然,等待著路易的啟迪。
“沒天理啊!”路易罵道,一骨碌爬起來。泥點從他的袍子上慢慢滑落,沿著袍子的下擺掉下去。
傀儡師涅索斯在滔滔不絕地大談倫理道德。他暫停下來回答路易的詢問(不誇張地說,他是同時用兩個嘴在說,這讓崇拜他的聽眾大為高興)。他說,他的代理人還沒有任何消息。
動物對話官同樣也被一群人圍著,他四腳八叉地攤在草地上,像一座橘紅色的小山似的。兩個女人在搔撓著他耳朵背後的毛。這克孜人的耳朵很怪,它們可以像粉紅色的中國油紙傘那樣打開,又可以折疊起來平平地貼在頭上,此刻它們撐得大大的。路易能看見每隻耳朵的表麵有著精心設計的刺青圖案。
“怎麼樣?”路易對他喊道,“我的主意不錯吧?”
“的確不錯。”克孜人甕聲甕氣地回答,躺著一動不動。
路易心裏暗暗發笑。克孜人是一種可怕的野獸,對不對?但是有誰會害怕一個被人搔耳朵的克孜人呢?這一招讓路易的客人感到放鬆,也讓這個克孜人感到放鬆。任何一種智力水平高於田鼠的動物都喜歡讓人搔耳朵。
“他們輪流著給我撓呢。”克孜人低沉著聲音說,“剛才有個女的在給我撓耳朵,一個男的走過來看了一會兒,說他也想享受這樣的待遇。於是他們兩個就一起走了。另一個女的就走過來接替她。在這個種族中,兩個性別都是有智慧、有感覺的,能身為其中一員,得是多麼有趣啊。”
“但有時這會把事情弄得複雜得不得了。”
“真的?”
克孜人左肩旁的那個女孩有著太空般黝黑的皮膚,上麵裝飾著星星和星係的圖案,她的頭發像一條彗星的尾巴那樣發著白色的寒光。她停下手裏的活兒,抬起頭。“蒂拉,你來接替我吧。”她快活地喊道,“我餓了。”
蒂拉二話不說,過來跪在克孜人那顆橘紅色的大腦袋旁。路易說:“蒂拉·布朗,這位是動物對話官。希望你們兩個……”
附近傳來一陣不和諧的音樂聲。
“……一起玩得愉快。那是什麼聲音?哦,是涅索斯。你在說什麼?”
那音樂聲來自傀儡師神奇的喉嚨。隻見涅索斯粗魯地把路易和蒂拉分開,擠進兩人中間,“你是蒂拉·簡羅娃·布朗嗎?身份號碼‘IKLUGGTYN’,對不對?”
女孩吃了一驚,但並不害怕,“這是我的名字。我記不住我的身份證號碼。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到地球上來已經快一個星期了,就為了找你。現在無意中跑來參加個聚會,居然碰到你了!我可得好好說說我那些代理人。”
“啊,不是吧。”路易輕聲說道。
蒂拉笨拙地站起來,“我又沒有躲起來,既沒躲你,也沒躲任何其他的……外星人。現在,請你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等等!”路易站到涅索斯和女孩之間,“涅索斯,蒂拉·布朗顯然不是一個探險的料,你還是挑別人吧。”
“但是,路易……”
“等一下。”那個克孜人站了起來,“路易,別多管閑事,讓那個食草動物挑他自己的隊員好了。”
“可你看看她嘛!”
“還是先看看你自己吧,路易。身長還差一點才到兩米,哪怕是在人類當中,也算偏瘦的。你覺得你是個探險的料子嗎?涅索斯又是嗎?”
“該死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蒂拉追問道。
涅索斯迫不及待地說:“路易,讓我們回到你的辦公室去。蒂拉·布朗,我們得向你提出一個請求。你沒有義務必須接受,也沒有義務必須聽,但你會覺得我們的請求很有意思。”
爭論在辦公室裏繼續。“她符合我所要求的條件。”涅索斯堅持說,“我們必須考慮聘用她。”
“她又不是地球上唯一一個符合條件的!”
“你說得沒錯,路易,當然不是。但是我們一直無法聯係到其他的人。”
“你們到底考慮聘我做什麼啊?”
傀儡師開始跟她講起來。結果蒂拉·布朗對太空一點兒也不感興趣,她連月球都沒去過,而且從來就沒有要去已知空間之外的打算。那個量子二號超光速引擎也引不起她的貪欲。當她臉上出現煩惱和迷惑的樣子時,路易再次插進話來。
“涅索斯,你說說蒂拉為什麼那麼符合你的條件吧。”
“我的代理人一直在尋找那些生育權彩票贏家的後代。”
“我要退出。你就是個瘋子。”
“別急,路易。我的命令都來自‘幕後人’,他是我們所有人的最高統帥。他的神誌非常清醒。聽我解釋好嗎?”
對人類來說,控製生育從來都很簡單。現在隻要把一個小小的晶片插到人前臂的皮膚下麵就行。這個晶體需要一年時間才能溶化分解。在那一年裏,插了晶片的人是無法懷孕的。在早先那些世紀裏,使用的則是一些比較笨拙的方法。
在21世紀中葉的時候,地球人口已經穩定在一百八十億左右。地球生育管理局是一個聯合國的下屬機構,負責製定和推行生育控製方麵的法律。五百多年來,這些法律規定一直保持不變:一對夫婦隻能生兩個孩子,但具體情況由生育管理局裁判和調整。管理局有權決定一個人可以生幾個孩子。也就是說,管理局可以允許某對夫婦多生一個孩子,也可以禁止另一對夫婦生孩子,這一切都取決於那對夫婦的基因是人類需要的還是不需要的。
“不可思議。”克孜人說。
“這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球已經變得擁擠不堪了,一百八十億人就困在這個技術原始的星球上。”
“如果我們的族長想在克孜星球推行這樣的惡法,我們就會將他斬草除根,誰叫他這麼蠻橫不講理。”
但人類畢竟是人類,不是克孜人。五百年來,這些法律執行得非常好。然而,兩百年前的時候,出現了一些謠言,說生育管理局有欺詐行為。這個醜聞最後導致了生育控製法的巨大改變:
現在,任何人類都有權生一個孩子,不管他的基因情況如何。除此之外,符合以下條件的可以自動獲得第二和第三個孩子的生育權:智商測試高分者;擁有某種實用的超自然力量者,如高原眼(6)或者絕對方向感,或者具有有利於生存的基因,如心靈感應能力、自然長壽、擁有完美的牙齒等等。
你也可以花錢買生育權,一百萬星際幣可以生一個孩子。為什麼不呢?要知道掙錢的能力也是對生存有利的重要因素,這是久經考驗了的。再說,這樣也減少了行賄。
你還可以通過在競技場上的競爭來獲得生育權,隻要你第一個孩子的生育權還沒有用掉。勝利者將得到第二、第三生育權;失敗者將失去第一生育權,還會失去他本人的生命。這樣就扯平了。
“我在你們的娛樂節目上看過這種比賽。”動物對話官說,“我還以為他們是打著玩的呢。”
“不是,他們是當真的。”路易說道。蒂拉咯咯地笑起來。
“那生育權彩票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玩意兒是近年來才有的。”涅索斯說,“盡管人類發明了‘補生精’(7)來抗衰老,可地球上每一年死亡的人數還是比出生人數多……”
於是,每一年,生育管理局都會統計該年的死亡人數和移民到外星球去的人數,再減去那一年出生和移民到地球來的人數,得出多少,就做多少生育權彩票,放到新年這一天來賣。
任何人都可以購買生育權彩票。如果運氣好的話,你可以生十個甚至二十個孩子——如果這叫好運氣的話。甚至連罪犯也可以買生育權彩票。
“我本人有四個孩子。”路易說,“其中一個就是中生育權彩票出生的。如果你們早來十二個小時,就會見到其中的三個。”
“這聽起來既奇怪又複雜。當我們克孜人的人口增長太多時,我們就……”
“你們就進攻離你們最近的人類世界。”
“根本不是這樣的,路易。我們就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我們的人口越稠密,一個克孜人冒犯另一個克孜人的機會就越多。我們的人口問題就是這樣自行調節的,所以同一個星球上的人口數量從來也沒達到過你們那種二乘以八的十次方(8)這個數量級!”
“我覺得我現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蒂拉·布朗說,“我的父母都是中生育權彩票出生的。”她有點緊張地笑起來,“否則我是不會出生的。這麼想起來,我的祖父……”
“你前麵五代的祖先都是因為贏了生育權彩票才出生的。”
“真的嗎?這我都不知道呢!”
“相關資料記載得非常清楚。”涅索斯向她保證。
“問題依然沒解決。”路易道,“那又怎麼樣?”
“那些傀儡師艦隊的統治者認為,地球人的運氣也是可以遺傳的。”
“哈!”
蒂拉·布朗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傾,無比好奇的樣子。毫無疑問,她從沒見過一個瘋了的傀儡師。
“想一想那些彩票,路易。想一想進化。七百年來,你們人類是按數字限製來繁殖的:每個人有兩個生育權,一對夫婦兩個孩子。時不時地,有人贏得第三胎的彩票,有人被拒絕生育第一胎,隻要依據充分:糖尿病基因或諸如此類。但大多數的人類都有兩個孩子。
“然後生育法變了。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在每一代人中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三的人是因為贏得生育彩票出生的。什麼決定了一個人可以存活下來並繁育後代?在地球上,當然靠的是運氣。
“而蒂拉是六代生育權彩票贏家的女兒!”
(1)英國推理小說家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於20世紀初創作的係列小說《神秘的傅滿洲博士》(The Mystery of Dr Fu Manchu)中的邪惡天才式的人物。這個形象是西方人腦海中“黃禍”想象的化身,反映了那個年代西方人對神秘中國的想象以及恐懼。
(2)地球上的空氣對泰諾克人來說相當於毒氣,會導致死亡。相關背景可參見作者196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有潮汐》(There is a Tide),故事中,路易到已知空間的邊緣探險,跟泰諾克人相遇。在跟路易搶奪一個古文明遺留物的過程中,泰諾克人的船被潮汐撕裂,路易救下了唯一幸存的船員並把他送到了附近的一個人類殖民星球“馬格雷夫”。
(3)作者虛構的外星種族,是甘米吉星上的一種動物,也是富人們喜歡的裝飾品。這種動物的特點是固著在樹枝上不動,等待機會,捕食經過的飛蟲。
(4)眾品公司是傀儡師一族的產品製造公司,其最成功的產品就是眾品船體,分別有一號、二號、三號、四號四個型號,眾品船體在各個種族中都很暢銷。
(5)原文“We Made It”,直譯“我們成功了”,是作者虛構的繞小犬座α星運動的一顆行星。人類首艘殖民飛船曾在該星上緊急降落,該星因此得名。該星球重力約為地球的五分之三,其自轉軸與軌道平麵幾乎重合,這一點與天王星類似,所以該星球地麵上每年有一半的時間都有時速800公裏的狂風,迫使人們居住在地下。該星球的居民被稱為“墜星者”,個子很高,很多人都患有白化病。
(6)作者杜撰的一種超能力,具有這種能力的人可以讓人對他視而不見,甚至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第一個被發現有這種能力的人住在高原星球上,此超能力便因此得名。
(7)作者杜撰的一種可以延長人類壽命的藥,是居住在金克斯星球的生物學家發明出來的。
(8)原文“two times eight to the tenth”應該是“two times eight to the tenth power”的省略。數學上有“2×10的8次方”的說法(two times ten to the eighth power),但沒有“2×8的10次方”的說法。作者這裏可能是故意用這種錯誤的說法來嘲笑這個克孜人對數學的半懂不懂,也有可能克孜人使用的是八進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