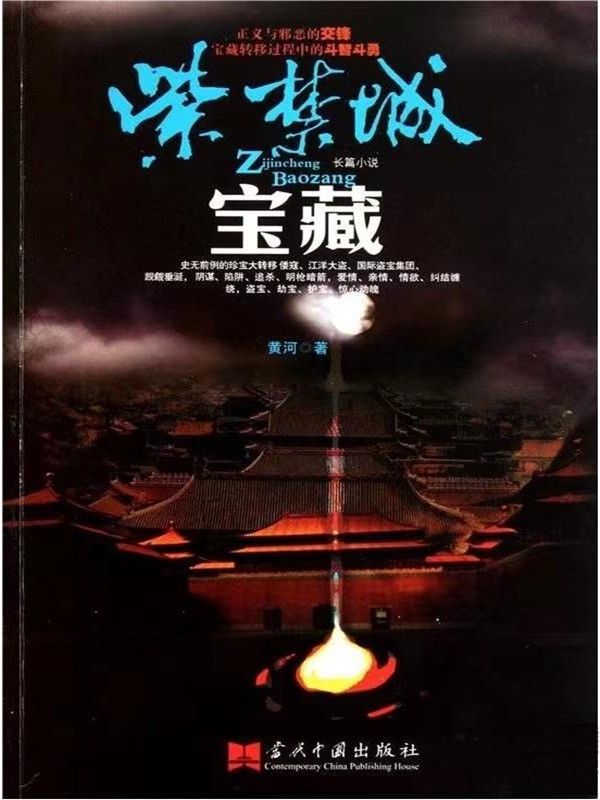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二、警世人懸寶市政廳 思紅顏壯士生去心
清晨,北京市政府,樓頂,段祺瑞政府的旗幟在晨風中有氣無力地擺動。朝暈未斂的天空,沒有陽光的蹤跡。
市政大樓前的街道上,車輛、人群熙來攘往。正是上班的時候,市政廳大門口,腋下夾著公文包、穿著白襯衫和老式長衫短褂的工作人員魚貫而入。
北京警察局,局長辦公室裏警察局長唐仁和正在接電話:“是……知道了,昨晚……在那邊剛鬧開當口,下邊就報告上來了……是,好的好的,明白,我明白……”
唐仁和放下電話,轉身惡狠狠瞪了眼恭恭敬敬立旁邊的陸警官,煩躁地扯開衣扣,急促地踱了幾步,吼:“奶奶個熊!警察局的臉都丟盡了!老子的臉都讓你們這些廢物丟盡了!飯桶!統統都是飯桶!”一拍桌子,朝立門邊的心腹歐陽遠崗吩咐,“抓起來!歐陽,你給我把昨晚在養心殿東套院值班的那幫家夥統統抓起來!”
歐陽遠崗:“是!”轉身而去。
唐仁和:“回來!”扭頭斜了眼木立一旁的陸警官,一咬牙氣惱地,“還有他,抓起來!先把他給我抓起來!”
歐陽遠崗:“局長,這……”
陸警官慌忙上前扯了唐仁和衣袖:“姐夫,不是我不盡職,實在是……實在是……”
唐仁和摔開小舅子,朝歐陽一瞪眼:“愣著幹啥?還不把他給我關牢子裏去!才多大會兒?市府那邊都驚動了,一個個都他娘象被窩裏著火樣往我這打電話,保不準再過一時半會兒,總執政都要來親自過問督辦了呢!奶奶的!禁宮盜案迭起,你們這幫廢物守也守不住,破也破不了,讓我咋向上頭交待?”
陸警官:“姐夫,那飛賊來無蹤去無影,實在厲害呀!還有……還有前清那些王公舊臣、太監宮女,他們熟悉宮內地形,了解珍寶存放情況,同內外烈強、綠林大盜勾結起來,實在讓人防不勝防呀!”
唐仁和:“住口!你讓我拿這些屁話去搪塞市府和總執政?抓起來!”
歐陽遠崗走陸警官麵前:“陸兄,那就隻好委屈你了。”說罷,抓住陸警官一條胳膊向門口走去。出了門,複湊陸警官耳邊輕聲道,“放心,局長這是在保護你呢,作個樣子而已!”
陸警官:“歐陽兄,你可得拉兄弟一把,去給我表姐透個信兒。”
歐陽遠崗點頭:“一定!”
市政廳大樓前,街道上行人明顯增多,大樓門口趕上班的人明顯減少。街邊,一職員夾著公文包從黃包車上跳下來,小跑著穿過樓前停車場,蹦上大門前石級。一個身穿月白綢衫的職員從門內匆匆出來,在石級上撞了夾公文包的一膀子,公文包落地,遲來的職員彎腰拾起,抬頭瞪撞他的人。穿月白綢衫的忙向他道歉,他卻將目光越過對方頭頂,望著大門前敞廳頂驚詫地嚷:“嗬,廳簷上那是啥?看,快看,那裏吊著個啥包兒!”
進出人等一齊抬頭望,隻見廳簷邊懸下個黑布包袱,包袱上掛著張尺半長紙條,上書幾行黑字。都不知鬧的啥名堂,驚詫莫名的興奮,一齊望了亂紛紛嚷嚷不休。
街上行人紛紛駐足,慢慢圍上來。人堆裏有人念那包袱上字條:
監守自盜實猖狂,內外勾結狽與狼;今朝奪贓告天下,來日斬賊慰四方!
眾大嘩,吵吵嚷嚷,議論紛紛:
“喂,沒聽說嗎?昨夜紫禁城裏的珍寶又被盜了!”
“飛賊?又鬧飛賊了!”
“不那麼簡單吧?沒見那紙條上寫的啥?那意思夠明白的了,守護禁宮的那幫子中,有人內外勾結,監守自盜呢!”
“唉,國難妖魔多喲!”
圍觀者越來越多。市政廳一門衛爬上敞廳頂要取下那懸廳簷上的包袱,被憤怒的人群喝住,破鞋爛襪瓜果石子從人群中紛紛飛向廳頂那門衛,門衛遮擋著倉惶退下。一記者變換著角度哢嚓哢嚓照相。
一輛小轎車馳到市政廳前岔道口,車頭一掉,遲遲疑疑駛入市政廳前停車場。車門開處,市長韓一夫鑽了出來,立即被人群包圍。
群眾亂擠亂擁,嚷嚷著要市長談談昨夜盜案,要市長解釋監守自盜所指為誰。兩名記者撥開人群,擠到韓一夫跟前。一瘦且高戴眼鏡的記者,一手捏本一手握筆盯著韓一夫問:“請問市長,昨夜禁宮盜案損失有多少?昨晚禁宮方向槍聲大作,警盜兩方可有傷亡?政府和警方對此又將采取何種對策?”
手舉相機的記者:“韓市長,禁宮外有警備司令部軍士巡邏警戒,內有警察局大隊警察駐守,可謂防範森嚴,而盜案連連,今又出此奇案,實令人疑竇叢生,請市長就此……”
韓一夫抬起一隻手,打斷記者的提問道:“盜案自然歸警局管,你們為何不去問警局?”道罷,抽身走,在工作人員和趕來的市府警衛護衛下擠向石級。
眼鏡記者不肯罷休,追著直嚷嚷:“市長留步!市長留步!請問‘監守自盜’所指何為?禁宮盜案連連,據說所失珍寶為數驚人,價值更是無法估算,為何不見警方和市府有何舉措?為何有人將贓物懸於市政府大門而不掛在警局或警備司令部門前?莫非與市府某人有關?”
正在此時,警笛聲鬼嘯而至。兩輛站滿身著黑色製服、荷槍實彈警察的卡車飛馳而來。卡車在市政廳前大街“吱兒”一聲刹住,大群警察餓狼樣撲向市政廳前人群,轟趕人群。槍托、警棍亂雨般落在人堆裏,人群大亂。
韓一夫在石級頂站下來,喝止警察:“住手!都給我住手!不許傷害市民!”
警察停止轟趕。一警官跑向韓一夫,為難地:“韓市長,你看這……”
韓一夫不睬他,示意市府警衛取下廳簷上包袱,朝人群揚揚手高聲道:“諸位,諸位市民同胞,都回去吧!忙自己的正事兒去吧!禁城珍寶失竊,軍警兩方和鄙人各有防範不嚴、治理不善之責。然恰逢這亂世初治之時,有幾個小毛賊亦不足為怪!至於賊人將贓物懸於市府大門,當是賊人匪黨玩的小把戲而已,乃為亂我人心,亂我秩序之詭計,諸位不可受其蠱惑!本市長將立即敦促警方全力偵破此案!案破之時,即是水落石出之日,不惟諸位心中疑惑迎刃而解,匪黨賊人的詭計亦不攻自破!更多的,恕本人不便在此多說了!”道罷,轉身就要進門。
此時,那市府警衛已爬上門廳,正探手抓住係包袱的繩子。突然寒光一閃,人群中飛出一把匕首,割斷了繩索!包袱從韓一夫肩後落下,掉石級上散開,珍寶撒得滿地都是。
韓一夫一驚,回頭看著滿地珍寶驚異異常。
一警察站石級上向匕首飛來的人堆處一指,大叫:“抓住他!是他放的匕首!他就是飛賊!”
人堆裏,一個黃包車夫打扮,頭上斜扣一頂黑黢黢小草帽遮去半邊臉的漢子,聞聲扭頭朝人堆外擠。幾個警察嚷嚷著撥開湧上來的人群擠過去,但更多的人又湧了上來。領頭的警官跺腳罵娘,拔出手槍朝天開火,人群炸窩,鬼哭狼號亂紛紛逃散。一群警察遠遠咬著放匕首那漢子屁股追上去。
印刷廠內,印刷機忙碌著,工人們忙碌著,一張張飄著油墨清香的報紙從機頭上吐出來。
報紙上醒目的大黑體字標題:
禁城珍寶有驚無險 義俠懸贓市府大門
京城街頭。熙熙攘攘的行人,鱗次櫛比的商號酒館,五花八門的雜貨攤兒。一報童遊魚般從人縫裏鑽出來:“咳!看報看報!大盜夜闖紫禁城,警匪槍戰景山腳呀!咳!看報看報,特大新聞啦!”
一行人叫住報童,掏錢買報。一群人圍上來,報紙很快被搶購一空。
街邊人行道上,一頭戴瓜皮帽,鼻架金絲眼鏡的白須老者捧了報紙邊走邊搖頭晃腦念。
街上,兩個學生模樣的青年邊走邊對著報紙上指指點點地議論。瘦長條兒學生:“這回總算揭穿了,那幫禍國殃民的家夥不知發了多少國難財!”
麵孔黑黑的學生:“揭穿啥?哼,沒見市長咋說的?‘幾個小毛賊玩的把戲而已’!到頭頂天抓兩個替死鬼平息輿論了事!”
街邊,白須老者忽放悲聲:“作孽呀作孽呀!乾隆爺在天之靈如若有知,亦當痛心而涕泣呀……”
一身穿青色薄綢對襟短衫,顴骨高高,天堂飽滿的青年男子從後麵搖過來,在老者身後站住腳,往老者手上的報紙上探了眼,陪著笑搭話道:“這世道……唉,真是越來越不成樣子了!喂,老爺子,聽說那賊竟然大白天也敢在市府前亮相兒呢,此人真是了得嗬!”
老者推推鼻梁上眼鏡,回頭翻了他一眼,說:“聽口音小哥你是外地來的吧?我看小哥倒象個本份人,奉勸一句,這種事兒你可別跟著人家瞎嚷嚷,像你這樣的精壯男子,又非京城人,千萬別讓偵緝隊當飛賊拿了去嗬!”
青年諾諾連聲哈腰稱謝,卻又嘿嘿道:“老爺子點撥得是,點撥得是,小輩隻是好奇而已。小輩尋思,那鬧禁宮而後又懸寶市府大門者,可不該與一般毛賊一概而論,哪個賊人不愛財?這人卻將珍寶高高掛在市府大門之上,咱背地罵他是賊,不是有失公平嗎?”
老者慢慢挪著步兒,扭頭望著青年微微點頭,嘴上卻道:“小哥,這種話兒可千萬別再信口亂說,大街上人多耳雜嗬!理兒是理兒,事兒是事兒。你不知道,為抓那飛賊,而今京城的局子、保安隊、偵緝隊全都抓紅了眼!小心禍從口出嗬!”
對老者好心的告戒,青年全不當回事兒,挨著老者慢慢走著咧嘴嘿嘿一笑,爽朗地道:“全城的軍警暗探一齊忙乎,竟然抓不住一個毛賊,這賊不就成神了?嗬嗬!我馬家田最佩服這種有本事的俠義之士,若是有緣結識,乃馬某生平幸事,縱是讓軍警暗探錯將李鬼當李逵捉了去又有何憾!晚輩尋思,那義士在市府前飛刀射落珍寶袋兒,亮了像,定有人知道點他的來龍去脈,所謂雁過留聲……”
誰知老者聽他這一說,當即退開兩步,狐疑地將他重又上下打量了番,說聲“恕老夫不陪”,搖搖手中報紙,躬背搖頭轉身管自去了。
馬家田兀立當場,望著老者的背影消失在人群裏後,方歎口氣地朝前方街口走去。
街口,茂源錢莊的黑漆金字招牌在陽光下十分惹眼。馬家田在錢莊門口放慢腳步,左右掃了幾眼,大步而入。
錢莊後院,天開四合,雕窗花欄,中間天井裏小小蓮池、玲瓏假山、幾株花草、一棵梭羅樹,構成小小景致,給滿是銅臭的錢莊帶來絲兒清雅之氣。馬家田穿堂過屋直奔後院,剛踏上天井邊回廊,南廂房內就迎出個五十開外的瘦削男人來,他就是茂源錢莊掌櫃的龔長壽。
龔長壽捋著下巴上胡須笑道:“嗬嗬,大侄子,我沒說錯吧?打聽也是白打聽,要不,咋稱京城人是‘京油子’?嗬嗬!”
青年上前施了一禮,喚了聲龔伯伯。老板娘同了兩個下人也一齊迎出來,青年又施一禮,喚了聲姑母。姑母慌慌地叨咕:“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這年頭兵荒馬亂的,外頭瞎闖啥?也不怕姑母耽心!”
幾個說著話兒,進屋坐了。青年尷尬地笑笑,把方才的事兒說了遍。龔長壽笑笑道:“人家準是把你當暗探了,這年頭誰不怕沾惹是非呀!”
青年眉頭一皺說:“這事兒實在蹊蹺,不弄個明白,家田難以心甘啦!”
龔長壽道:“是嗬,是有點蹊蹺!內有內應,外有外應,那幫黑衣人竟敢同軍警開火,且轉眼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實在是蹊蹺嗬!”說到這兒,傾過身子湊馬家田耳邊輕聲道,“可賢侄你將人家費盡心機盜來的珍寶半道截下,高懸於市府大門外,在人家眼裏不是更蹊蹺嗎?嗬嗬!”
馬家田也將頭湊過去輕聲說:“既讓小侄碰上,不能不管,跟蹤而去,沒想竟進了禁城,結果闖下這樁事兒,給伯伯添亂子了,慚愧!慚愧!”
“啥慚愧不慚愧的?”龔長壽正色道。“這倒令我想起了你爹當年的英雄氣慨!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啦!哈哈!”
姑母不知他二人嘀咕了些啥,瞅老頭子越說越歡喜的樣兒,“就問:“你叔侄倆說啥好話兒?瞧你們一老一小樂得,咋不說出來讓我們也開開心!”
“說啥?還不是大侄子的婚事兒,”龔長壽掩飾道。“方才在大街上他差點沒把人家姑娘當作他的未婚妻關小月,我取笑他急著要進洞房呢,哈哈!”
經龔長壽這麼一說,馬家田臉上真就有些兒燒乎乎的了。姑母也順勢兒打趣了幾句,之後卻幽幽地歎了口氣,說:“唉,也不知小月姑娘到底流落何方了,這些年,天下大亂,你二伯一直在四處打聽,可就是沒半點蹤影……家田啦,聽姑母一句,那市府前飛刀射落珍寶袋的人,你還是別找的好。且不說眼下風聲正緊,這京城裏藏龍臥虎,三教九流哪條道兒上的都有,誰知他是正是邪?莫要惹火上身才好!依姑母意思,還是抓緊打探你小月妹的下落,早早把她找到,早早接回你蓋縣家裏,洞房花燭,了卻你爹懸望是正經!”
馬家田躬身稱是,老爹飽經風霜鬱鬱寡歡的麵影在腦海裏一閃而過。
是嗬,轉眼背井離鄉從東北蓋縣老家來京已是月餘,家裏可好?老爹可好?自從娘過世後爹爹就愈發地鬱鬱寡歡,身子骨似乎也大不如前了。
那天,他正在後花園練功,老爹把他叫去,拿出一柄劍、一封信,讓他來京城找龔、關兩位伯伯。“東北這地方是日本人天下,窩這蓋縣鄉下哪能出息?要謀出身,還是到京城去吧。聽說關內革命黨已成氣候,馮玉祥將溥儀帝都逼出了宮,看來這天下大勢是革命黨昌盛,王道衰微了呢!唉,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嗬……”爹搖頭歎道。“聽說你關伯伯一家似已不在京城,不知是遁世避禍還是遭了啥變故。”爹接著說,神情很是黯然。“你到京後可先去找龔伯伯,有他幫忙,隻要你關伯伯還活著,早晚總能找到他。若你此去能尋到你關伯伯和小月妹,人家也還認這段姻緣,你就同小月先回蓋縣把婚姻大事辦了;若尋不到或是人家嫌三推四,你就跟在你龔伯伯身邊,我已在信中拜托他了,讓他好歹替你在京城尋個事兒,鬧個出身。家田啦,你已不小,終不能隨老父在這鄉野蓬蒿糊裏糊塗了此一生。現雖恰逢亂世,卻正是男兒報效國家,建功立業大好時機。此一去海闊天空,你當好自為之,無須牽掛我這把老骨頭,有朝一日你能衣錦還鄉,作爹的也就含笑九泉了!”說到這裏,爹爹起身抓起古劍,拔劍在手用指頭彈了彈,接著說,“這把寶劍是你爺爺傳下來的,跟隨你爹走南闖北幾十年,從沒負過咱。雖說如今時興洋槍了,但對咱習武之人來說,還是它才是最體己的家夥。況當年離京,你不過七、八歲,轉眼十幾年,你龔伯伯、關伯伯如何認得你?你帶上它,你兩位伯伯都認得我這把寶劍,見劍如見人,可免去許多口舌。”
關伯伯同爹爹早年都是肅王府帶刀護衛,兩個孔武漢子卻偏偏同當時是宮中文職小吏的龔長壽成了莫逆之交,於是三人學那桃園三結義結了八拜之交,爹爹年長為大,龔伯伯次之,關伯伯再次之。後來關伯伯又同爹爹指腹為婚,結下了這兒女親家,而龔伯伯的夫人則同他母親結了金蘭之好,是以他以姑母稱之。
那年,肅親王在日本人慫恿下搞“滿蒙獨立”,從京城逃到旅順口。爹爹不明究裏,一為忠主之事,二來思鄉心切,即隨肅王到了旅順。之後,爹爹又托人將母親和他接到了東北蓋縣老家。因是潛逃,肅王臨行不便多帶人眾,即著令小月父親幫著總管照料在京家產,是故未去東北。
爹爹到了旅順,耳聞目睹,漸漸醒悟,看見王爺整日同日本人勾結,狼狽為奸,禍國殃民,愧悔莫及,於是生發了歸隱家園之心。恰逢蓋縣家裏捎信來說老母病危,爹爹就趁機借口要回鄉探病和祭掃祖墳向王爺告假回到了蓋縣靠山屯。未幾,肅王的“滿蒙獨立”破產,在東北革命黨反“獨立國”浪潮中惶惶不可終日,無暇它顧,爹爹也就趁此稱病歸隱了。
龔長壽見他發怔,以為他是在想念關小月了,嗬嗬笑道:“到底是兒女情長嗬,十幾年沒見了吧?你小月妹早出落成水靈靈的大姑娘了!嗬嗬,別急別急,我包你早晚洞房花燭就是了!眼下我看還是先找個正經事兒做著,要在這京城立住腳沒個正經身份可不成。這也是你爹的意思,年青人好歹總得謀個出身呀。”
馬家田忙起身稱謝:“那就有勞伯伯操心了!”
姑母關切地問可有眉目,龔長壽大大咧咧地笑道:“沒事兒,明兒我去殷太太府上走一遭,十有八九就妥貼了!”
姑母疑惑地:“殷太太?是不是市府那個殷參事的老婆?”
龔長壽點頭:“那可是當今政府裏的紅人,如今革命黨如日中天,家田賢侄要謀出身,也隻有走這條道了。且我看這革命也並不壞,滿清入關,統治我漢人這麼多年,也該革他一革了!”
姑母鼻孔裏冷哼了聲道:“可你難道不知那姓殷的路數可是不正得很,莫非你也想……”
龔長壽麵容一端:“我龔某行得穩站得正,不管咋總不敢忘自己是中國人!”歎了口氣,語氣一軟接著道,“我這就叫利用,賢侄,你可莫多心。亂世求生,既要保蓮藕之清白,又要好好兒活下去,難啦……”
是夜,馬家田久難成寐,對故鄉親人的思念,對下落不明的關小月的擔心掛念,全被勾了起來,加上來京後這一月多所見所聞的各種五花八門的事兒,一齊亂哄哄湧上心來。
不知咋他總記不清關小月的容顏,腦海裏一會兒是童年時穿紅戴綠、哭哭嘰嘰的小月模樣,一會兒又是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含羞帶笑的大姑娘。卻都總模糊,細要辨認,又悠地不見了。哎,小月呀小月,你到底貓哪兒了?讓哥哥找得好苦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