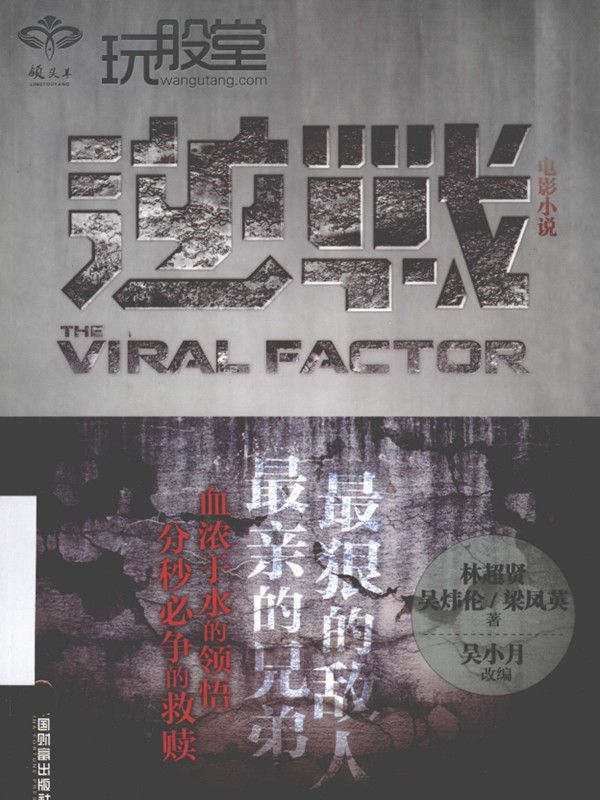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3章
當Jon 推著母親的輪椅時,總是盡量不去看她頭發的顏色,怕看得太仔細了,媽媽的年紀就真的一下子就老了。
他希望她永遠就如同他記憶中的模樣,雖然一個女人帶個孩子過得很辛苦,流著汗的臉上寫盡了疲憊,但始終是黑發烏眸,帶著溫婉包容的笑睇望著他。
趁母親去廚房張羅晚餐時,他把看護王小姐請進客房內,問母親的身體近況如何。
“萬太太這幾個月因為擔心你,使得她的坐骨神經痛症又惡化了。”王看護邊說著,滿臉憂愁的神色,像是真的替他母親擔心。
有她在,或許可以安心一點,但不知道她能替自己照顧母親多久呢……
“王小姐,兩星期後,我會離開一段長時間。”Jon沒有把話說得明白,提起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的事,輕描淡寫得像隻是會出一趟遠門。
隻剩沒多少時間了,不需要令大家都難過。反正,日後也會知道,不如這段時間就快快樂樂地過。
“你剛回來,又要走?”王看護有些不可思議,Jon在她眼裏是很孝順的,每次出差回來,肯定會休息一陣子多陪陪母親,這倒是第一次這麼快又要離開家裏,或許,真的有什麼很重要的事也不一定。
“對,我會多存點錢給你。”Jon淡淡地笑了笑,有一點兒勉強。隻怕,是永遠的走了。“要麻煩你,希望你能夠多多照顧我媽,我不在家的時候,多陪陪她,還有幫我注意她的身體狀況,不要讓她逞強。”Jon 難得囉唆地細細交代,一遍又一遍重複王看護都會背的話。
她笑著點頭,心想著Jon真是個孝順的兒子:“你放心,我會多留下來陪陪她,也會注意她的健康狀況的。”
看著王看護離開房間,Jon 坐在床邊,有些垂頭喪氣。他不知道該怎麼樣才能打起精神來,就算時時刻刻陪在母親的身邊,好像還不夠,似乎還有什麼他能做而沒做的……他不想留下遺憾,他最怕的就是母親無法承受失去他的痛苦,但母親是個非常堅強的女人,相信她應該可以撐過去。
上天啊,請減少她的哀傷,並帶走她的苦痛,讓她能夠自在快樂。Jon 將臉埋進雙手裏,凝神誠心地祈求著。
正打算站起身走出房門,剛剛微彎的身體,導致掛在他脖子上的項鏈滑了出來。他已經習慣了項鏈的溫度,或者說,是他的溫度感染的項鏈,令它有了人的體溫。
他脖子上掛著的,正是當初Jon 和Ice兩人一同挑選的戒指,戒指上還刻著日期和兩人的名字,明知道要忘掉,明知道她早已走遠,甚至不可能再出現,但他仍無法丟棄這個屬於她的專屬約定。
他將它掛在身上,貼近心臟處,好說明她也曾經愛過他,是千真萬確的。
Jon撫著項鏈好一會,發現自己又失神不知道多久,他輕輕拍打自己的臉頰,使自己清醒一點,將項鏈擺進衣服內。冰涼的溫度就像Ice的個性,剛接觸時冰得令人驚心,但沒多久也如同和他體溫融為一體般,溫暖如洋流。
“飛,可以出來吃飯了。”母親在門外呼喊著。Jon即刻揚聲應答,火速起身,不願母親久等。
家鄉菜,母親的家鄉菜,是他在異鄉,最常夢見的味道。“媽今天做得不好吃。”鳳玲有些歉疚地對著兒子說。
“媽媽的味道,永遠都不會變。”Jon 不顧形象地猛扒了幾口飯。記憶中的香味,雖然不是頂一流的廚藝,但就是他心中最美好的味道。
鳳玲沒再多說什麼,隻是一臉欲言又止的憂傷,凝望著她的已經長得好大的兒子。
不知道萬陽,跟著他老爸,是不是也能和萬飛一樣吃得這麼香?
一想起丈夫和大兒子,鳳玲就一陣心痛;那股惆悵的失落感,是用什麼都填補不了的,大兒子在她抱著萬飛離去前那一聲聲的哭喊,近日又開始在夢裏不斷播放,每每都令她哭著醒來。
若是上天能讓她選擇,她實在不願意放棄其中一個。兩個都是她的心頭肉,都是她懷胎十個月生下來的寶,她憑什麼選了萬飛而放棄萬陽?
萬陽肯定是不會原諒她了………
“媽,你還在擔心什麼?我的傷已經好了。”自出院後,萬飛眼裏的笑,起伏都不大,淡淡地還帶點病後的疲憊。他不希望母親為自己擔心,但他也沒辦法找回過去那個正義、熱情的兒子。他的生命一點一滴在流逝。
“最近,我和公司請了長假,每天都可以陪你,吃你做的菜。”又是那麼努力的一笑。
“你這工作狂,也不知道說的是真的還假的。”鳳玲還不了解自己的兒子嗎?她知道兒子心裏肯定有什麼事瞞著她。
罷了,她不也有個秘密,瞞了他將近20年,也該是時候對他說了,不然,怕自己會來不及彌補愧疚,來不及看萬陽一眼,就撒手離世。
鳳玲失神地想著,她沒注意到自己的眼角已微微泛著淚光,Jon 望見了,以為母親仍擔心著自己的病情,不願她多作猜想,心一觸動,放下碗筷就起身走到母親身旁,輕輕地從背後抱著她。
“傻孩子,你這趟出門發生了什麼事嗎?怎麼一回來就不停地抱媽呢?”鳳玲慈愛地又拍了拍他的背,要他安心,要他快樂,不要再憂傷。
“好久沒抱抱你了,很想抱抱你。”Jon 沒多解釋什麼,隻是更擁緊了母親,深怕沒有下一次擁抱的機會。
鳳玲一聽,心更揪得緊了。萬陽根本沒機會可以抱抱她,他是不是很恨媽媽呢?她痛苦地閉上眼,仿佛又看到那個小不點大的小男孩,在門邊哭著要她不要走,不要丟下他……不能不走啊!如果不走,就沒有重生的機會,萬陽,媽媽真對不起你……
從頭到腳徹徹底底將自己洗了一遍,大概這輩子都沒刷洗得這般幹淨。當知道自己生命隻剩下那麼一丁點兒的時候,好像那兩星期的期限是老天爺給的另一種奇異的鏡片,戴著它看世界的每一件事,都有不一樣的視野。
就連洗個熱水澡也是一種令人想哭的珍惜。
他檢視著身上大大小小的傷痕,連同這次在約旦受的皮肉傷,是國家安全局給他繪上的人體藝術彩繪,沒有消去的清潔劑,一生都帶著。
不過他不在意,甚至能因公有傷痕而感到自豪,那是他每一次認真付出的證明,但最嚴重也最無法抹殺的傷,卻從外表看不出來。
有形的,在他腦裏,那顆要命的子彈;無形的,在他心裏,Ice 那一句:“對不起”。
統統好不了,忘不掉,也拋不開。注定一輩子要跟著他。不過,也不用再擔心,因為他的一輩子,也隻剩短短兩個星期的時間。
吹幹頭發後,他躺在床上,拿出項鏈癡癡地望著,出神到隻有Ice還會對他笑著的世界,連母親敲門,自行推著輪椅進他房間都沒發現。
鳳玲見他仍珍寶似地收藏那項鏈,知道自己的兒子重情的個性。想起,被她拋棄的丈夫與兒子,怎麼她這個母親就不像兒子一樣重情?怎麼她就能舍得狠得下心來拋棄那個對著她不斷哭泣的孩子……
孩子啊,萬陽啊……你能、你願意原諒媽媽嗎?媽媽年紀大了,或許也不能再活多久了,你願意來看媽媽一眼嗎?
鳳玲想著想著,又差一點流下淚,她捏捏自己的手臂,暫時用疼痛轉移悲傷。在哭泣之前,她還有很重要的事要和萬飛說。
“飛啊。”她將輪椅移到兒子的床鋪邊,輕聲呼喊他。
“媽?你什麼時候進來的?”萬飛被母親嚇了一大跳,有些驚慌失措,他連忙將項鏈收起,怕母親對自己仍執著於Ice的感情有所擔心。
“思念一個人,是一件很苦的事。”鳳玲沒有回他話,自顧自地,像是在說一件好遙遠好遙遠的事,像童話故事般開頭,但卻注定沒有童話的甜美結局,語氣是那麼淡的悲傷。
“你知道嗎?你受傷的那幾個月,媽媽幾乎每天晚上都做同樣一個夢。”鳳玲的眼神有一點空洞,心仿佛在萬飛房裏,又像是真的要飛到遙遠的海上。“我夢見我們一家人,在海上,一個接著一個消失了,最後,隻剩下我一個人。”
“媽?”萬飛不解母親話中的意思,一開始,他以為母親知道自己的病情了,有些擔憂,但當她接著說下去,又發現她話中的語病,一個一個?
“飛。”鳳玲這才將心神調回來,對著他的眼。萬飛用緊握住母親的手,代替回答。
“媽有一件事要告訴你。”鳳玲有點想鬆開兒子握緊的手,但想了又想,又更加回握住他,像是那樣的動作,給了她萬分的力量。
“當年,我說是你爸爸拋棄我們,是錯的。其實,放棄這個家的人,是我。”
“媽,你在說什麼?”萬飛怎麼也沒料到,自己恨了那麼多年的男人,那個當警察的父親,拋棄他們母子的父親,令他們過得困苦的父親,竟然不是他所認為的那樣?
“我不隻就你這麼一個兒子,你還有一個哥哥。”鳳玲接著說下去,要他不要打斷自己,再不說出口,怕就沒有勇氣、也來不及說了。
“我20歲的時候跟你爸爸結婚,隻想著玩樂,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將來會怎樣,想著愛了就結婚吧,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對你爸也不是十分的了解;直到我生了你們兩兄弟,我才想到你們的將來。”
記憶好像自動會變成黑白色的,像是多份悲傷的力量似的,叫人回想起來更加痛苦不堪,靜靜地在腦子裏不停翻轉。
她又看見了,丈夫不停地拿著錢去賭,她和兩個孩子都要沒飯吃了,賭輸了就回來發脾氣。因賭而失去工作後,不好好反省,反而更變本加厲,那猙獰執意要賭的臉容,還深刻地印在她腦海裏,抹也抹不去。
“但是你爸爸沒有想過將來,他隻知道賭,結果,把自己工作也賠掉了,連警察也當不成,他沒有因此而反省振作,竟然還賭得更厲害,若那個時候,再不走,可能連你們都會被他給賣了。”幽幽地,往事那麼不堪,過程那麼痛苦,卻也隻能在多年後的現在,化成幾句簡單悲傷的話。
“你兩歲的那一年,我想先把你們帶走,再想辦法救他,可是我沒有想到,你哥哥他哭著拉著我的手,不讓我們走。”哭聲還在,像是隨時都會再響起,就在心裏,就在眼前,那小不點大的孩子,哭得眼淚鼻涕都糊在一起,希望她不要走,不要帶弟弟走,不要離開父親。
“那時,我好急,我怕你爸爸回來,我真的沒有辦法了。後來,我隻好抱著你離開,把你哥哥鎖在家裏。”鳳玲說到這裏,已經沒辦法再握住萬飛的手了,她抽開自己的雙手,掩麵哭泣。
“我在樓下,聽到他在上麵一直哭一直叫——媽,你不要走!媽,你不要走!”最後真的失語成泣,她將隱藏了20多年的秘密說出,仿佛掏空身體的力氣般,抽離了所有的空氣,悲傷令她有些暈眩。
“媽,你別難過,都過去了。”萬飛雖然完全不曉得自己還有個哥哥,內心也感到震驚萬分,但仍堅強地安慰著母親,畢竟,他身上背負著更大的秘密——關於自己兩個星期的生命。
所有的不堪、過錯,都在死亡麵前變得微小而不足以為道。
“這份內疚,我帶了20多年。”鳳玲抬起淚眼望著萬飛,眼裏有著深深的企求,"飛,我最近終於有他們的消息,我在想,我該怎麼去麵對他們……雖然我怕萬陽不會再原諒我了,但你最近受了那麼重的傷,令我一度以為會失去你,令我很想再見你爸跟你哥一麵,哪怕他們不原諒我也罷,我想親口對他們說抱歉……”
母親臉頰上的淚雖然可以擦幹,但她心裏的淚卻始終不斷。萬飛不想令母親繼續痛苦下去。
"媽,我去幫你找他們回來?”雖然Jon說的是問話,但答案已然是肯定的。
當母子兩人談完話,他將母親送回臥房後,自己拿了一件外套,便走出家門,到附近的公園裏想事情。
小時候,他好羨慕別人可以一家和樂地在公園裏玩耍,母親坐在一邊笑著,父親和兒子玩在一起,有時候還可以耍耍賴,要父親將自己舉得高高的……
從來都沒有。他沒有一次這樣的經驗,就算羨慕得要命,也隻能將這些收進心裏,他知道母親一個人帶大他很辛苦,而且,因為被父親拋棄,他更有出息,所以他工作時選擇了國家安全局,成為裏麵的探員,他要證明自己比父親出色,令他後悔他曾經拋棄他們母子……但沒想到,這20幾年來的怨、20幾年來的恨,一切都是假的。
縱然父親好賭有錯,但他卻沒有拋棄他們,是母親帶自己走的。
他不會埋怨母親,他知道母親這麼做都是為了他好……隻是,他現在什麼都沒了,生命隻剩下那麼一點,若是不在盡頭前去見父親與哥哥一麵,怕是永遠都沒有見麵的機會了。
耳邊還回蕩著母親說過的一字一句。他透過母親的描述,仿佛也看見幼小的哥哥,在門邊哭喊著要他們不要走的情景。
哥哥,不知道他現在過得好不好?和父親處得還好嗎?兩個人是否都安好地活在這世上?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令他們回來見母親呢?
夜風吹得他頭又開始痛起來。那有些壓抑不了的痛,像是鬧鐘般,定時在警告他:你時日不多了,還有什麼要做的,請加快腳步去做。
是啊,眼下哪還有什麼要做的?當然就是替母親找回父親和大哥,在兩個星期內,他得快點去找回他們,正要起身,那劇烈的疼又令他瞬間軟了腿,不得不跪在地上,甚至忍不住輕喊出聲。
如有強大外力在擠壓他腦神經的痛,幾乎令他要幹嘔出來,他眼睛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就算咳了半天,沒吐出東西也無法阻止那劇烈的疼痛。
雙腳跪在雪地上,已經凍僵了,但這也無法轉移他頭的痛楚;沒有任何可以轉移的方法,隻有自我了斷,才能馬上結束這一切。
Jon自約旦返回家後,就忍受著身體心靈上雙重的痛苦折磨,還要避免被母親看見自己這副痛苦的模樣,就算他受過特殊訓練,鐵打的身體也快要承受不住了,他害怕哪一天,會失去視力,再來失去手腳的行動力,漸漸地,他無法言語不能動彈,是一種消極、你無法阻止、無力阻止它流失能量的死亡過程。
他真的很害怕,有誰能夠救救他?
要快、要快;他已經沒有時間了。爸爸,哥哥,請你們等我,拜托你們等我,不要讓母親失望……
Jon陪了母親兩三天,每夜,他都將母親那晚交給他的一個陳年鐵盒從抽屜裏取出,打開鐵盒緩緩抽起裏頭的一張舊照片。
淚是不經意流下的。他長年受過訓練,早已經把眼淚收在心裏,看著母親的舊照片裏,泛黃的老舊色彩染著他們一家四口當時幸福的笑容,他站在哥哥身旁還噘著嘴,不知道為了什麼有些賭氣,不甘願地對著鏡頭扯了個笑。
幸福太過短暫,短得甚至他連記憶都沒有。
“你爸當年為了避賭債,帶著你哥離開了香港,一直住在馬來西亞。”母親的話一遍又一遍,傳入他耳裏。
他其實想馬上出發,立刻出發到馬來西亞找他們。隻是他的身體……他怕一去就回不來,又舍不得離開母親;反反複複、眷戀躊躇。
母親那晚在他脖子旁滴下的淚,是那麼灼熱,幾乎要燙傷他;他知道,那是母親的殷盼,他不該再猶豫的,因為,時間真的不多了。
“媽,我去找他們回來!”Jon 這麼對著鳳玲承諾。
我去找他們回來,好嗎?Jon 也在心裏,對著自己那麼承諾。他一定要,將父親和大哥帶回來。
濃黑色的深夜,隻有街道上的白雪隱隱泛著光芒,Jon 獨自在窗邊想著母親的話、母親的眼淚,也想著自己,即將快要失去的一切……
隔天,他終於下定決心離開。
收拾好行李,托朋友訂了飛往馬來西亞的機票,他再度踏出那深深眷戀的母親的視線外,尋找他失落已久的另一半親情。
他一向都認為,法院的燈光有些太刺眼了,這麼明亮又令人不自在的地方,他實在非常不喜歡。
他也不喜歡法官自以為是的驕傲態度,案前眾律師的神氣表情,還有坐在後排,一堆堆像看戲般想笑的民眾。
那些人,都不是跟自己一樣的人;那些人,若跟自己過一樣的生活,仍然可以露出一模一樣的表情嗎?有誰天生想當罪犯?
“被告多年來屢次犯案,顯示被告實為一名對社會及公眾均構成極度危險的人,本席現在宣判,被告萬陽於2008年2月5日持械行劫黑珍珠珠寶店,行劫罪名成立,判監10年,另於2010年11月1日被捕時拒捕,襲警等罪名成立,判監3年,兩罪刑罰同期執行。”
在法庭上,一名男子身穿亮橘色的囚服,皮膚曬得有些偏黑,卻不像馬來人般那麼深,仍看得出是其他亞洲國家的人,頭發的長度在男人的短發型來算已經是長到極限了,微卷的劉海剛好蓋到上眼皮,再長一點就會遮到視線,或者,已經有些遮掩,反正他也從來沒有好好地正眼瞧過人。
那人,名叫萬陽。他數不清第幾次聽法庭的宣判了,就連手銬也戴得有些習慣,聽判決時的神情,像極了無奈,又有些不屑,微低的視線裏寫滿了“你們這群蠢蛋廢話說完了沒有,到底懂什麼”之類的譏諷。
或許他們都不明白,他不是為了犯罪而犯罪;他是為了生活才犯罪。
若是可以給他很多的錢,讓他過好生活,又不犯罪的話,他當然也非常樂意,但這個世界上哪來那麼好的事,如果有,那麼監獄裏肯定有大半的犯人都不再是犯人了。
其實遠看,他幾乎就像當地的人了,尤其是那膚色、那發型、那姿態。
滿臉說不出的微憤的悲傷,發梢如其神態略略枯黃而看不出生命力。若要說他放棄、頹靡,又不太對;他可是很頑強地,在他那低下的世界裏,用一種不認真看待,好事壞事都不介意去做的方式對抗世界。
他的自尊,隻存在那一瞥之間,一怒一瞪的背後。其他的什麼,都是多餘的,就是為了生活,什麼都肯幹。
當法官的木槌聲響起,所有罪名塵埃落定,有人眼裏有得意,有人眼裏有恨意,有人眼裏有無所謂的感情;總之,那些人眼裏寫著的,不會是同情。
他也不需要、不屑那些假好人的同情,他隻是選擇一般人較不認同的方式生存,不代表他沒有權利選擇這樣的方式;所有的法律都是自以為正義的一方訂的,到底孰是孰非,都不一定。
時間算得剛剛好,萬陽那放空的眼神,其實隻是想轉移其他人的注意,雖然他知道,根本不會有人在意他這種小罪犯,他在那決定性的一刻,將別人預留給他的手銬鑰匙神不知鬼不覺地取到手,就在眾警押送他離開法院的路上,萬陽伺機暗中解開手銬。
簡直小事一樁。萬陽心中有些不屑的想著。雖然離安全逃避法院還有大半的路要努力,但他幾乎賭定自己可以安然離開。
他在這個世界,可不是摻假的。他對於每一次的行動,都是拿命作賭注的。
白色雕花的走廊,襯著午後的陽光,異常耀眼,萬陽對於這種適合全家出遊的好天氣早已沒有任何感覺,甚至覺得陽光此刻出現顯得有些諷刺,那麼莊嚴美麗的地方,卻讓一個又一個像他這樣的罪犯踏行,令人不得不訕笑。
萬陽沒讓自己的心思偏離太久,他和法警步行到走廊的轉彎處,不動聲色地觀察牆角的監視器角度,當他們一踏至監視器的死角範圍,他隨即一反手,把手銬當成拳套一般,揮拳重擊身後的法警。
根本管不了手上是否還殘留著揮拳揍人後的疼痛感,他隻能盡快地攻擊所有會阻擋他離去的人。
當其他法警還不及按下通信器請求支援,萬陽已快速地衝近,毫不留情地揮拳痛毆,令押送他的法警個個倒在地上痛苦呻吟。
解決完押送他的法警,並不能解決後頭所有的麻煩。才剛要跑起來的萬陽,隨即聽到警鈴大作,他心知不妙,不能再繼續困在這裏,否則肯定逃不出去。
萬陽幾乎像草原動物般,在莊嚴美麗的白長廊狂奔起來,一抹橘色的身影就從每個走廊浮雕的間隙間忽隱忽現,若不說這是一場生存逃亡之戰,簡直可以當成是藝術畫來欣賞。
萬陽在走廊猛衝著,見前麵已有另外幾個警察追來,他還來不及轉頭,那些警察已然衝到他麵前,拿出特殊噴霧朝萬陽的頭噴去,想要製伏他。
萬陽的雙眼瞬感劇烈疼痛,他猛然向警察用力撞過去。
追上來的法警被萬陽這麼突如一撞,跌得有些狼狽不堪。萬陽利用模糊的視線,趁眾人暫時分心時,衝往走廊的一台飲水機,快速用水一抹眼睛,好不容易將視線恢複得七八成,便轉身向樓梯那邊衝過去。
眼看,四麵八方都有法警衝過來,萬陽進無可進,退無可退,好像隻有正麵往下衝才是唯一的路。
但沒辦法,又有幾個警察從樓梯下衝上來阻攔他,萬陽一個狠猛的飛踢,踢倒帶頭的警察,眼見正麵向下的路也不能走,唯有跑到另一邊走廊去看看是否有機會逃出去。
就在萬陽即刻往前衝,不一秒又見另一頭的走廊遠遠又有警察追來,回頭一望,身後也有警察追來,萬陽的視線,隻得盯著下方一望。
兩邊的警察即將要衝到自己的身邊,萬陽心知再不做下決定,就要來不及了。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隻有一條。
跳下去又不是第一次,這次才四樓,上次和老爸為了活命,他們可是從六樓跳下去;最多,就像老爸一樣斷一條腿,沒什麼大不了。
和被監禁比起來,萬陽寧可賭上一把,遂奮不顧身,越過圍欄一躍而下。
從高樓跳下的感覺似曾相識,但這種輕飄飄的致命感,沒有一次是好受的。
亮橘色的囚服在高空中畫出一道美麗的弧線,令人觸目驚心地,雖然最終的落地有些狼狽不堪,但萬陽不要求拿跳姿滿分,他隻求活命。
他順利地穿越兩邊屋簷中的細縫,掉落在一輛車的後車蓋上,雖然撞傷了手臂,大致上仍算安全降落,手臂的痛麻令他有些冒冷汗,他死命咬緊牙關苦撐起身,火速翻身下車,迅速逃離法院。
追上來的法警隻好圍著欄杆,望著到手的罪犯再度脫逃,個個麵露無奈。
碰巧是放學的時候,一群群小學生從校內走出來,每個人邊說邊笑。放學,比上學有朝氣多了。
萬陽將車停在學校附近,已經盯看著校門口好一會兒了。
不知已經出來多少小學生,等在校門口的父母漸漸的少了,好不容易望見一個長發身材纖細的小女孩,臉色有些蒼白地捧著一疊考卷和兩個同學一同走出來。
萬陽臉上不自覺地在嘴角染上一點笑,但隨即又感到難過。見女兒垂頭喪氣,神情寞落的樣子,他難堪地不禁自責。
老爸三不五時就交代他,有時間要多探看女兒,他知道,他也想。
其實他很愛阿勝的,他也想天天看著她;但他的身分卻不允他這麼做,這麼做隻會令老爸還有女兒陷入更大的危險。
這是命,這是他和他女兒被寫好的命;他被母親拋棄了,隻能選擇危險的道路前進,導致他女兒雖然有他在,也形同被拋棄的意味,無法天天看見父親,也無法像正常小孩一般,享受天倫之樂。
他企圖想給女兒更好的生活,所以鋌而走險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沒想到更好的生活一直沒辦法過上,還令女兒抬不起頭來,隻能和爺爺兩人過著相依為命的生活。
是他對不起女兒,但這條路一旦選了,就沒有機會回頭了。
是命啊,阿勝。老爸對不起你。萬陽心痛地將頭靠在車窗邊,邊望著女兒,邊內心自責。
手上的傷還隱隱作痛,但能觸動他的心的,隻有老爸和女兒的感受。
阿勝看起來精神很不好,也不曉得跟著老爸有沒有好好的吃飯,老爸那家夥,成天隻知道賭,雖然阿勝很懂事,但還要照顧爺爺,真的太為難她了。
怎麼他們家的人,年紀越大越不懂事,反而是小小年紀的阿勝,擔起照顧他們父子的責任。
想到這,萬陽不禁浮起一絲苦笑,他欠女兒的,太多太多了。離學校不遠,就是熱鬧的商圈。
街道上,販賣3C產品的商店門口,有幾台大大的液晶電視正同步播放著一則即時插播新聞:“被判持械行劫與襲警的犯人萬陽,於今日下午,在法院審判結束後擊倒多名庭警,從法院四樓跳下後逃去無蹤,警方現已發出通緝令,全國搜捕逃犯萬陽……"
一張張萬陽的通緝照片被放滿整個電視牆,鮮橘色的囚服異常刺眼的映在萬長勝的眼裏。
萬陽也同時看到新聞了,他本來要下車,想上前叫女兒來見個麵,卻止步了。他無法再往前一步,這麼短的距離,若是硬要拉近,肯定會害了他們兩個的。
本來和萬長勝走在一起的兩個同學,正問她要不要買什麼零食,沒想到新聞一播,跟在她們後頭的兩位同學的母親,立刻拉下臉來拉走自己的女兒,一點情麵也沒留。
臉上、嘴上全是嫌棄的高姿態,比新聞上那一張張鮮橘色的照片,更令她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