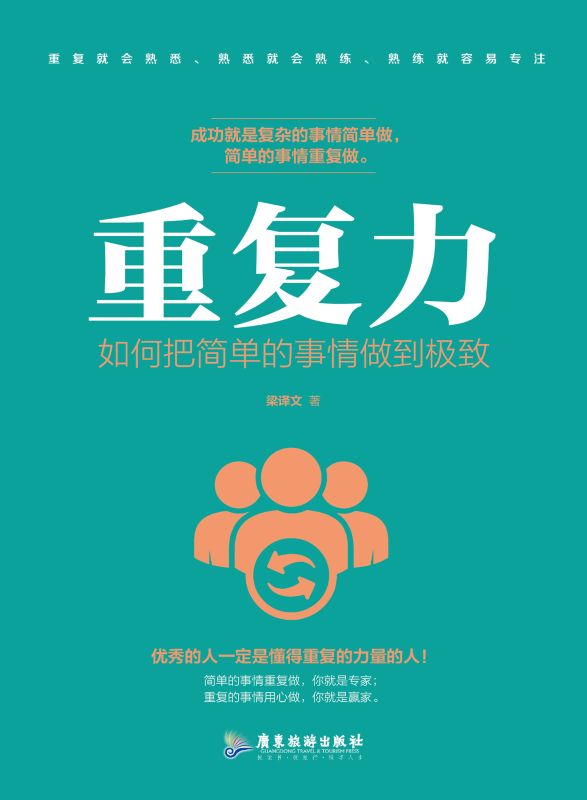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就會不簡單
我們都知道,簡單的事情重複做,就會變得不簡單。這其實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量的積累並無特別之處,這個過程是枯燥乏味的,甚至帶有一種“冒傻氣”的味道。可誰能否認當量的積累達到某一程度,即達到臨界點時,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巨大能量呢?
1955年的美國亞拉巴馬州是美國當時最宜人的洲際之一,這裏富饒的土地孕育出了蒙哥馬利市。獨特的文化不僅僅在於這裏的藝術元素,同時還因為這裏也是當時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沒有人真正地去判斷這裏的規則是否正確,隻是這裏的法律很明確地要求公交巴士上非裔美國人要給白人讓座。
就在12月1日這個下午的6點,有一位名叫羅莎·帕克斯的非裔女裁縫,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了辦公室,接著她登上了一輛公交車。汽車經過了一段行駛之後,已經坐滿了乘客。許多後來上車的乘客也沒有一個座位可坐,這時候公交車的司機詹姆斯·布萊克看見了坐在座位上的女裁縫,由於法律的規定和一直以來的習慣,司機起身要求正在座位上休息的女裁縫站起來,為一名壯年白人乘客讓座。這樣的一幕並不陌生,在這裏,曾經有無數的黑人被司機喝令著,默默起身,遵照當地法律,被迫將座位讓給並非老弱殘孕的白人。
在當時的蒙哥馬利市內,公交巴士的前四排是供白人坐的。而按照所謂的“規矩”,如果沒有白人乘客站著時,黑人有權利坐在前四排以後的位子。但如果前四排坐滿了乘客,那麼這些沒有地位的黑人就必須起來給白人讓位。更為荒唐可笑的是,如果白人多到擠不下,連站著的地方都沒有,那麼這些可憐的黑人們就得下車。
法律尚且不夠健全,社會大環境也沒有對人們有明顯的尊重。幾十年來如一日,黑人們甚至不可以穿過白人座位間的過道而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前排已經坐了白人,黑人必須在前門付費,而後從車外走到後門上車。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很多黑人乘客買票後還未來得及到後門上車,巴士便突然啟動拋下他們。
這一切的規矩,都被一字一句地寫在了城市法規當中,絕大多數黑人隻有默默忍受,仿佛人生而平等隻是一句高高在上的笑談,麵對那些冷漠的規矩,除了仰視和遵守別無他法。
女裁縫羅莎在公交巴士上受到不公的對待,已經不是一兩次了。回顧自己的人生,早在1943年她第一次乘車時便已開始。那是她第一次坐巴士,而駕駛員正是此時喝令她讓出座位的詹姆斯·布萊克。那次她買票後,詹姆斯令她繞到後門上車。更為戲劇化的是,羅莎在離開前門時,不小心將錢包落下了。但是礙於規定,她隻好在後麵坐下,等待前門上車的白人乘客幫助她把錢包拾起。
此種極端“傲慢無禮”的行為,居然令司機詹姆斯憤怒不已,他粗暴地將她攆下車,接著開車離去。當時,外麵正下著雨,羅莎不得不步行8公裏回家。
然而這一次,麵對讓座的要求,受夠了得羅莎紋絲不動地坐著,她拒絕讓出自己的權利。當她說出“不”的時候,也許並不會想到,她數年後會被美國國會授予“現代民權運動之母”的稱號。
如果不是羅莎的堅持,也許現在的美國仍舊實行著那種不公平的法律。也許美國,並沒有足夠的底氣說出“人權”這樣的字眼。也許,那份人類之間應該相互給予的尊重和人類所表現出來的風度和優雅,就並不會出現。
那天傍晚,羅莎被警察以“行為不檢”的罪名逮捕,這項罪名是違反蒙哥馬利城市法規第6章第11條,同時,羅莎還並被罰了一張10美元的罰單與4美元的法庭審判費。盡管遵守了法律章程的羅莎很快便被保釋,但事情並未就此結束。
遭到逮捕的幾天後,羅莎並不能接受這樣一個不了了之的結果。當地民權運動領導人和黑人領袖們討論過後,在阿拉巴馬州立大學一位教授的幫助下,準備行動起來。就這樣。3萬5千份傳單被連夜印刷出來,內容是進行一天的巴士抵製運動。第二天,傳單傳遍了蒙哥馬利的大街小巷,巴士抵製運動從此拉開帷幕。
蒙哥馬利的黑人執著地開始拒絕搭乘巴士,改為步行出行。那些公交巴士上再也見不到黑人的身影,當他們邁著鏗鏘有力的步伐走過蒙哥馬利的每條街道,對巴士視而不見的時候,那份為了維護自我權益的執著使得他們在麵對上流社會的白人們時更顯得優雅從容。公交公司的運營逐漸吃力起來,因為黑人差不多占據當地全部乘客的3/4,如果他們不乘車,對公交公司而言無異於一場災難。
原本,隻打算進行一天的巴士抵製運動轟轟烈烈地重複著,日複一日。黑人們集體抵製巴士的行動使得蒙哥馬利公交公司迅速陷入了虧損狀態。公交巴士抵製運動開展後的一個月,蒙哥馬利公交公司就向蒙哥馬利市長申請緊急財政補助,以維持處於虧損狀態的公交服務。
在這期間,蒙哥馬利的黑人曾遭遇過白人交警和保險公司的刁難,不過,即使麵對被解雇和3K黨的威脅,所有黑人仍重複著最簡單的事——走路,為平等的權利,更為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一名女性抵製者驕傲地說道:“我的雙腳十分疲倦,但我的心靈卻十分安寧。”
這場規模空前的民權運動持續了整整381天。曆史上的這段期間,每一天,每一位蒙哥馬利的非裔美國人,都在不斷重複的步行中度過,官司也從蒙哥馬利地區聯邦法庭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
重複又執著的力量是巨大的,其使得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在1956年11月13日廢止了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政策,並宣布其違反憲法。故事的最後是喜人的,蒙哥馬利巴士抵製運動的參與者於1956年12月20日正式結束了他們的抵製運動,黑人陸續回歸公交車,而處境早已大不相同。黑人們用自己的執著換回了生而為人應該得到的權利,也同樣對白人給予了原諒和寬容。
1956年12月26日的《紐約時報》中寫道:“黑人們從前門上車,坐在前排的空位上,他們不為白人起立。白人們尷尬地坐在他們旁邊。”要知道,在一年之前,他們還需卑微地為白人讓座、被趕到後門上車,甚至因本就不公的法規而被捕。
人們不斷重複著簡單又困難的行為,簡單是因為這行為做起來舉手可行,困難卻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要承受著無比巨大的心理壓力,同時還要麵對著環境的挑戰。這一切都隻為一個簡單的目標——讓一切變得更好。
把小事放大看,世間從無小事,而任何一種成功,也都是透過質與量的交互過程所呈現出的一種優雅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