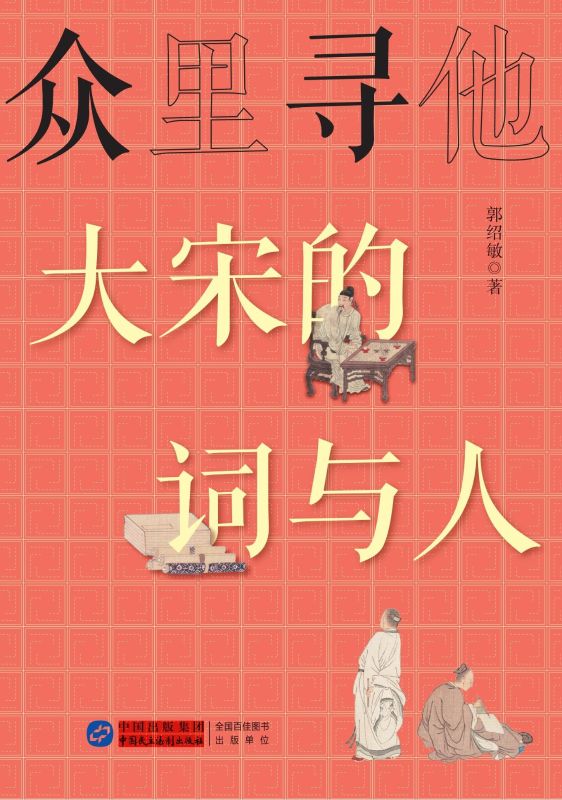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7.永恒之約
李煜詞曰:“蘆花深處泊孤舟。”那蘆花,那孤舟,是遠離塵囂的隱喻吧。汪曾祺的短篇小說《受戒》,輕逸而唯美,講了一個受戒的小和尚和一個名叫小英子的少女的故事,堪謂“傾‘廟’之戀” (9) 。孤舟上,小英子趴在小和尚耳旁小聲地說:“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小和尚眼睛鼓得大大的,小聲說:“要——”兩支槳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葦蕩。驚起一隻水鳥,擦著蘆穗,撲嚕嚕飛遠了。受戒,破戒;有愛,有欲,卻毫無俗氣。李煜就是那個小和尚。
李煜詞曰:“人間沒個安排處。”既然人間不屬於他,沒他的容身之處,那他就隻能屬於天上了,恰如釋迦牟尼,恰如基督,恰如蕭峰。《天龍八部》第五十回,蕭峰自殺前,對眾人說自己無顏立於天地之間。到底誰無顏立於天地之間?真是莫大的諷刺。公元978年,李煜被宋太宗派人鴆殺,終於回歸該去之處。天上不會“車如流水馬如龍”,也沒有“簾幃颯颯秋聲”。
李煜詞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依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夢並非無意義,亦不荒謬,而是欲望的滿足,但夢中人並不知自己身處夢中。那麼,眼下,此刻,客觀存在的、清醒的你我,是否正身處別人(朋友、上帝或外星人)的夢中呢?李煜在夢裏亦知身是客,隻是,這夢是白日夢。詩、詞、誄、賦、曲、小說……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學,都是一場場白日夢而已——不斷接力的大夢。
李煜詞曰“曉妝初了明肌雪”,又曰“春花秋月何時了”。他喜用“了”(liǎo)字。《紅樓夢》中有“好了歌”。跛足道人對甄士隱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但這話不夠徹底,因為好是了,不好亦是了;了是好,亦是不好,並非“了”了,就一定好。其實,世上本無所謂的好與不好,亦無所謂的了與不了,一切都隻是語言遊戲罷了。隻要張口,隻要書寫,必落言筌。這道理既然我懂,李煜自然也懂。但,仍要言,要寫,要鳴,直至肉體“了”了。否則,就真的如一片落葉,被一江春水衝走了,再也找不到一點痕跡。
寫到此處,我耳畔忽然傳來愛爾蘭歌手恩雅的空靈歌聲Amarantine(《永恒之約》)。
李煜和永恒有個約定,和謝了的林花有個約定,和被寂寞鎖住的一江春水有個約定;而我,和李煜的詞有個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