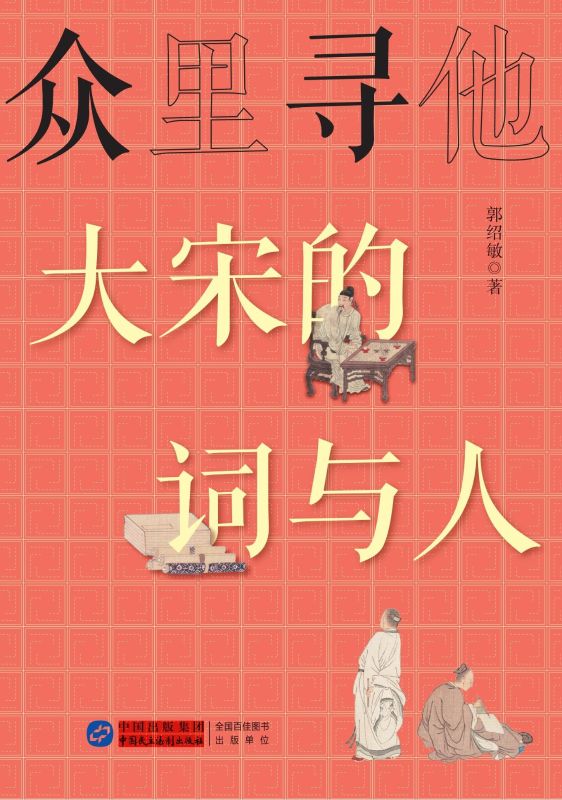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4.士不遇
清代的張惠言以為,溫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是“感士不遇也”,其“篇法仿佛《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陳廷焯的看法類似,他說,“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婦思夫之懷,寓孽子 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複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體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 (3)
屈原不遇,成《離騷》,自沉汨羅江。董仲舒不遇,撰《士不遇賦》,終得漢武帝倚重,獻“天人三策”。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寫《感士不遇賦》,誦給南山下的菊花聽;他抱樸守靜,“擊壤以自歡”“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4) 。那溫庭筠屬於哪一類士、哪一類“不遇”呢?
溫庭筠沒有自沉,不願“謝良價於朝市”,但也不受朝廷重用,隻做過小官。這與其性格或者說性情有關。《舊唐書》中說他“士行塵雜,不修邊幅”,《新唐書》中稱其“薄於行,無檢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羈放縱愛自由,是個十足的浪子。他“思神速,多為人作文”,經常替人寫文章。他在參加科舉考試時曾“救數人”(即做“槍手”,暗中幫助左右考生),攪亂了科場,“執政鄙其為”。溫庭筠寫詞時,情商“開掛”;混官場,卻幼稚得要命,像個三歲小孩。據《北夢瑣言》卷四記:“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雲:‘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令狐相國即令狐綯。代相國捉刀,本是一次大好的奉承機會,溫庭筠做就做了,事後卻大肆渲染,唯恐天下人不知。更何況,他還譏諷相國不讀書,是個大老粗。沒有一個領導會喜歡這樣的下屬,他的不遇是必然的。
如此性情,本不適合當官,偏偏溫庭筠的官癮頗大。唐宣宗對他的評價是:“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一個人應該幹最契合自己性情的事,如蘇格拉底所言:認識你自己。不適合從政,何必從政?不適合經商,幹嗎經商?不適合讀書,亦不必勉強,並非每個人都要考上清華大學(亦不可能)或成為大學者、名作家。人固然可塑,但基本的性情很難改變。正所謂本性難移,性格決定命運。皇帝冷落和放逐溫庭筠其實是對他的保護。詩人隻需把詩寫好即可,不必蹚官場的渾水。歌德說:“誰要是能夠為自己與生俱來的才能而活,那他就由此找到了最美好的人生。”朝廷不缺溫庭筠這樣一個官員,中國卻少不得他這樣一個詩人。
溫庭筠的不遇,是士不遇,更是詩不遇、詩人不遇。
但並非所有詩人都不遇。張九齡、王維、晏殊、歐陽修,官就做得很大。我羨慕魚與熊掌兼得的人,仰望“獨倚望江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