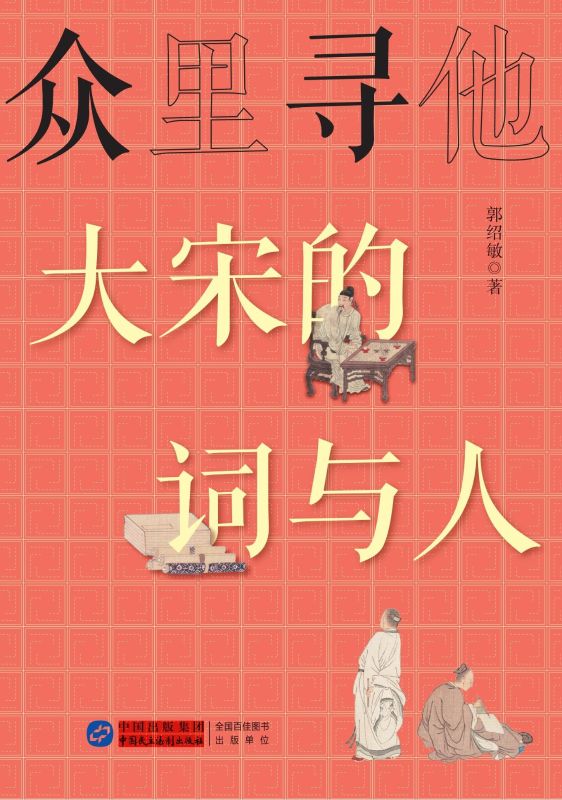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序
此書主講宋詞,是郭師寫作轉型的一次有益嘗試,在汴梁城講宋詞,是有主場力加持的。陳寅恪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誠哉斯言。惜乎文治武功不可兼得矣。剛剛滅了後蜀本不該喪氣的宋太祖都要無奈搖頭,直言“此(大渡河)外非吾有也”,是不敢有而非不想有。當時,後起民族西夏都能成為北宋日後勁敵,蘇軾、曾鞏等人在對外關係和軍事方麵的上書、奏折、策論等,多是討論李元昊和他的西夏,因其近在咫尺,危及存亡。至於南方大理等小國,民風粗蠻彪悍,北宋是無暇顧及的。還有北方更強大的對手,那更是不敢隨意招惹。偏安一隅,無欲無爭,正是創造卓越文化的優質土壤。南宋大儒朱熹曾不無自豪地宣稱,“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而宋代文化中成就最大的當屬文學,尤其是散文和詩詞。
文無第一,喜歡宋詞的人各有各的理由,而不喜歡宋詞的人多是覺得它過於浮豔。沒有辦法,文學從先秦一路走來,進步也好,退化也罷,看好和看衰的讀者都要承認,它變得更加通俗和精確了(也更加煩冗)。先秦和漢代的文學,簡潔高冷,字字鏗鏘,四言成詩,五言成句,一直到漢末,曹操的詩歌仍多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喜歡它的人覺得其氣勢雄壯,不喜歡它的人覺得其過於粗獷。從《詩經》、漢樂府詩發展到宋詞,究竟是文學的進步還是退化?答案見仁見智。就像圍棋,黑白二子,方寸之地,規則也極簡單,而現在3A遊戲中的一棟建築或者人物建模都不知道要耗費多少算力,可究竟哪個更高明呢?答案連輸給AlphaGo(阿爾法圍棋)的柯潔也未必清楚。
其實文學的發展像極了電子產品的更新迭代,表達欲驅動著一代代的文學家們開拓創新。宋代詩詞不但在體例上與秦漢古詩不同,在內容上也和前朝詩歌大迥,年代較近的唐詩仍然專注於表情達意、抒發感慨。也許是因為字數更多了,體例也更豐富了,宋代詩詞竟主動承擔起文章才有的義務,開始試圖說理了。“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這首詩闡述的道理涉及物理學和哲學,對比樂府詩《江南》,應該是高明多了,畢竟“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講的不過是魚在東南西北四處遊戲的事情,根本沒有特殊的意義,也不闡發什麼道理。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在藝術和美學上的價值。文學的價值不在於談意義、講道理,而在於藝術性和美感,過分關注文本的意義,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
宋詞給人以浮華豔麗的觀感,主要是由於它繼承了六朝文的綺靡婉麗。同為大一統餘緒下的偏安政權,東南西北,強敵環伺,異族於宋,正如古羅馬之於古希臘,“以物力則臣仆之,而以文教則君師之”。力有不逮,戰不能勝,終始意難平。隻好無奈地麵對現實,感時傷物,懷戀遼闊的北方,繼而沉湎於物欲的糾縈,以麻醉身心。“武功既致太平,人遂得聞而尚學文,於是壯心勇力為書卷所消磨”,文學的鼎盛,實肇於此。
除了浮豔,生活化、情趣化也是宋詞區別於傳統詩歌的一大特征。這不但體現於文字本身,也體現於選材和內容。比起文章和詩歌,詞曲更接地氣、更貼近生活,也更顯細膩。詞與詩,就像流行曲和古典樂,兩者風格差異明顯,卻都不可或缺。就像孔子刪述《六經》,對《詩》進行剪薙,宋代的士大夫繼承了曆代文人“詩以言誌”的傳統,他們在彙編整理平生詩文時,一般也會把詞曲剔除或者單列。歐陽修在自編《六一居士集》時,就舍棄了他的全部詞作和致仕後閑適縱樂的詩文,蘇軾盛讚此舉有“挽救斯文”之功。正是由於文人著意對詩、詞區分對待,認為兩者不容“勾兌”,才使詞逐漸承擔起詩不便承擔的內容,走上更加偏重情感表達的通俗道路。在此之前,普羅大眾的情感表達唯靠詩歌,而詩歌才不堪任,對通俗隻是偶有照拂而始終無法盡顧。
宋代文風鼎盛,文壇領袖代代不絕,《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這本書重點論述的有三人。一是蘇軾。王安石曾說:“世間好言語,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陳輔之詩話》)不想在當時,就有東坡降世,文章亦張亦弛,亦疾亦徐,亦俗亦雅,亦莊亦諧。蘇軾是天才、仙才、人才、鬼才,還是全才,詩書詞畫皆精通。“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王灼《碧雞漫誌》)蘇軾的詩詞,有很多我們都耳熟能詳,至今傳頌,如“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等。郭師講蘇軾著墨最多、篇幅最長,不隻因其文字,還因其為人的灑脫與曠達。
二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對文采無比自負的歐陽修。他的那首詞《生查子·元夕》膾炙人口,“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寥寥幾字,道盡人世相思。顧隨在《駝庵詩話》中讚美歐陽修對詞曲的“開創”之功,他認為“一種文學到了隻能‘繼往’,不能‘開來’,便到了衰老時期了”。幸而有歐陽修,他不但善於開創,還時刻不忘提攜後進。他很看重文壇晚輩蘇軾,曾這樣評價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三是一個有才的帝王——宋徽宗。在金庸小說中,宋徽宗和宋欽宗一起,成了《倚天屠龍記》故事的源起:“徽欽”被擄,嶽元帥怒發衝冠,繼而是《武穆遺書》的傳聞和多年後倚天劍、屠龍刀重現江湖。《後漢書》中韓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有才似乎成了帝王的原罪。蘇軾在《放鶴亭記》中談道:“《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麵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安享生活之意趣,則不能負擔政治社會之重責。因為勇心已被文雅馴服,鬥誌已遭書卷消磨,且“多言速窮”,才氣愈大、作品愈多則亡國愈速,蕭繹、李煜等以才華傲世者皆不得免。由此看來,帝王將相不得不割舍生活中的百般滋味情趣,不若常人自由灑脫。
一直以為《第九次沉思》將是作者寫作的一大高峰,要好久方可超越,不想這麼快就在燈火闌珊之處,讀到了《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郭師文章,非徒羅致書簡,更兼妙筆巧思。透徹明理處,撥雲見日;用典精妙,如羚羊掛角,不著痕跡。其書《大一統的史詩——三國新解》《第九次沉思》皆是此類代表作,後者因後出而轉精。而《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較之前作又有不同,這本書的一大特點是,作者坦誠敘述了一些情感經曆,雖然篇幅很少,但足夠解釋書名的由來。
王夫之稱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有“仙凡之別”,比起華麗的辭藻和虛浮的表象,他更稱許這種沉鬱感和它背後的真實。記得和郭師探討過所謂的“仙凡之別”,前者有著後者並不具備的文章直覺和藝術天賦。曹丕的言行無不表現出其對無常世事的深刻體認和洞察,在《營壽陵詔》中他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此語很平常,但出自一位帝王之口,就不再尋常。《世說新語》中記載了一則典故:“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想象一下,這是什麼場麵呢?葉嘉瑩稱曹丕的文章以感取勝,所以對人心的滲透力量推進較遲較緩,卻也更耐久。“你不一定需要遭受什麼重大挫折或悲歡離合,僅僅是平時一些很隨便的小事,都能夠給你帶來敏銳的感受,也就是詩意。”
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文風樸素,像嘮家常,與曹植華麗的辭賦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其開篇有一大段浮白,像極了戲劇的幕前鋪墊:“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初讀之下,覺得平淡且質樸,但隻要多讀幾遍,很快就能發現字裏行間流露的沉鬱氣氛,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無比強大的感染力穿越時空,竟讓兩千年後的我們受到極大觸動。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談道:“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郭師的作品,自《第九次沉思》以降,更多摒棄表麵的文采,追求遲緩的深力,用內收外化的沉鬱,寫出打動人心的文字。由此看來,《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不但是郭師寫作手法通俗化的有益嘗試,也是其對文風由激進到保守、由外放向內斂的一種變革。
朱光潛說過:“藝術所用的情感並不是生糙的而是經過反省的。蔡琰在丟開親生子回國時絕寫不出《悲憤詩》,杜甫在‘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時絕對寫不出《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這兩首詩都是‘痛定思痛’的結果。藝術家在寫切身的情感時,都不能同時在這種情感中過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觀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嘗受者退為站在客位的觀賞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經驗放在一種距離以外去看,所以情感盡管深刻,經驗盡管豐富,終不能創造藝術。”
郭師有著對藝術的高度自覺、對文學的高度自信,文藝之於郭師是天作之合。郭師是藝術的寵兒,當然也是其犧牲者。這世上少有人有此資格。我心疼且羨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