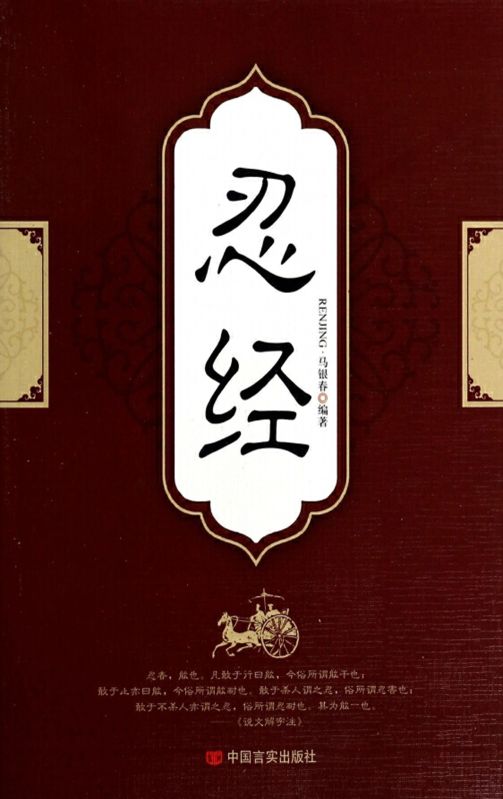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忍辱偷生甘受宮刑
按照漢代的法律,凡被判處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可以用錢贖罪,大約需交50萬錢,約合黃金五斤;或者甘受宮刑。所謂宮刑,也稱腐刑,是閹割生殖器的殘酷肉刑,是對人格最野蠻的侮辱。司馬遷平時的俸祿並不豐厚,家境也很平常,根本沒有能力償付這巨額的贖罪金。自從他因李陵案蒙受不白之冤以來,昔日的親朋好友們生怕引火惹禍,沒有一人敢站出來為他說句公道話,而是遠遠地離他而去。世態炎涼,司馬遷得不到親友的支持。
作為士大夫的司馬遷,理所當然地非常重視做人的尊嚴,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節。於是他想到自殺,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這個世界上隻有一件事使他欲罷不能,這就是正在寫作中的《史記》,這是他們父子幾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勞動,怎能忍心讓它半途而廢呢!
在麵臨著生與死的抉擇關頭,司馬遷不禁徹夜難眠,思緒萬千。他想,自己的先人並沒有立過赫赫的功勳,自己也不過是一個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決不能和曆史上那些“死節”的人相比的,那不過“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對於那些想將自己置於死地的人來說是無所痛惜的;對不明真相的人來說,也許還會產生誤會,以為是“智窮罪極,不能白免”才自尋短見的。人雖不免一死,但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代價有大有小。如果這樣平白無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此時此刻,曆史上那些有過坎坷遭遇的哲人豪傑們的不平常經曆,浮現在他的腦際,更給了司馬遷生的勇氣。他想,西伯(周文王)是一方諸侯之長,卻被紂王拘禁在牖裏;李斯官至秦相,結果身受五種刑罰,腰斬於鹹陽;韓信曾被封為淮陰侯,卻在陳地戴上了刑具,被呂後所殺;彭越、張敖都是麵南背北、稱孤道寡的王,後來下獄受罪;絳侯周勃滅掉諸呂,權勢超過春秋五霸,後卻被囚禁受冤屈;魏其侯是大將軍,卻穿上赭色囚衣,戴上木枷、手銬和腳鐐;季布自受鉗刑給朱家做奴隸;灌夫在居室之中受辱。這些人都曾經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結果都身遭不測,任人處置。連他們都能忍垢厚塵埃之中,在這個世界上,對尊嚴、權勢、榮辱的得失還有什麼想不通的呢?至於曆史上那些身處逆境,在困苦中仍發憤著書,終於功成名就的先賢們更給了司馬遷生的力量。西伯被拘禁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厄而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寫出《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寫出《國語》;孫臏被剜去膝蓋骨而編寫出《孫臏兵法》;呂不韋遷居蜀地,《呂覽》流傳於後世;韓非在秦國被捕下獄,寫出了《說難》、《孤憤》……
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48歲的司馬遷,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選擇,他擯棄自殺和赴死的念頭,決計忍辱偷生,接受那最為慘無人道的宮刑。他“就極刑而無慍色”。
宮刑不僅摧殘了司馬遷的健康,也給他的精神帶來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然而,這都沒有能夠摧毀司馬遷的意誌。正是這人生的悲劇,使他對曆史,對人生,對漢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對封建專製有了新的認識。他很快從極度的悲憤中解脫出來,將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將自己全部的心血,傾注到正在撰寫的《史記》之中。
受刑後的司馬遷仍然被關押在獄中。在這種非人境況中,他沒有一天停止過思考,幾乎天天與《史記》結伴,或在腦中醞釀,或不停地記下一些考慮成熟的片斷。大約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獲釋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