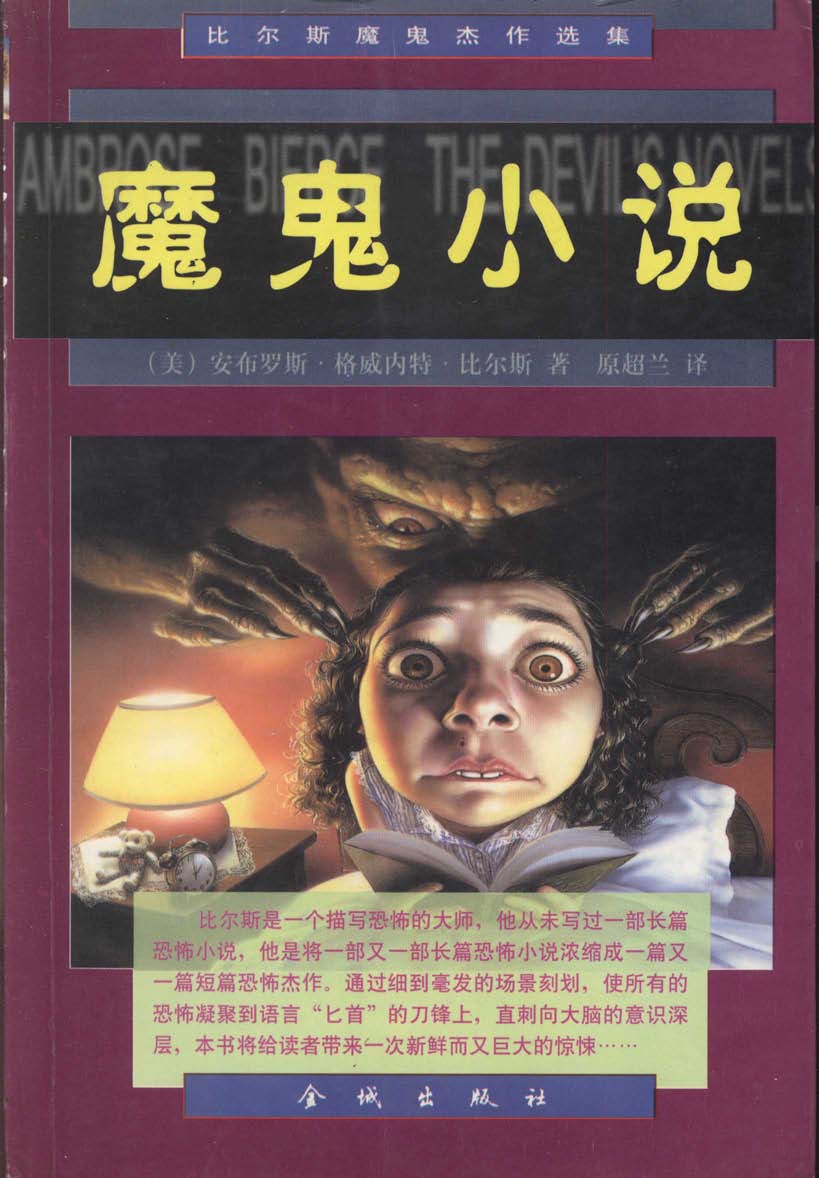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掐死愛子的幽靈母親
一
異乎尋常的死亡製造出比它所顯現的更為偉大的變化。但是,一般來說靈魂時常遊離重現,有時顯現在肉體上(靈魂以它所依附的身體形式出現)使沒有靈魂的活僵屍四處遊蕩。這種偶然的顯現被證明是存在的,這說明一具僵屍如此複活起來,它的身上既沒有自然的感情,也沒有思維記憶,而隻有仇恨。因此。可以確信世間的某些善良、親切的靈魂由於死亡開始完全變得邪惡不善了。
——希爾
仲夏一個漆黑的夜晚,密林中一個男人從沉睡中醒來,抬起頭,凝視了一會黑暗,說道:“凱瑟琳·勞萬。”他沒有再說什麼。不知道為什麼他隻說了這麼一句話。
這男人叫哈爾賓·福雷塞。他原住在聖海倫娜城,但現在他居無定所,因為他已經死了。他獨自一人在林中練習睡功,身下隻有幹樹葉和潮濕的大地;身體的上方隻有掉光了樹葉的樹枝和落盡塵埃的天空,這樣是無法奢望獲得長壽的,而福雷塞已經32歲了。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成千上萬的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把這個年齡視為事業迅速成長的階段,特別是孩子,在他們看來人生之旅的航船,已經駛過相當長的距離,好像就要接近成功的彼岸了。可是不知道哈爾賓·福雷塞是否就這樣走向他的生命的盡頭。
他一直待在拿帕峽穀西邊的丘陵裏,在這季節裏他在尋找斑鳩和這樣一些小小獵物。傍晚,天陰沉沉的,他迷失了方向,盡管他總是隻向下走——這樣當他迷路時也總是安全的,缺乏小徑這妨礙了他,在寂靜的夜晚他走進了樹林。在黑暗中他無法穿過這石南樹的灌木叢和其它樹叢,由於疲憊不堪,他感到深深困惑和沮喪,他靠近一棵櫟樹的樹根旁躺下,進入到無夢的睡眠裏。許多小時以後,夜深時分,上帝的一位神秘天使,帶著難以記數的幽靈從東向西滑翔而來,在睡眠者的耳畔明顯地回響詞語之聲,直接地召喚,他不知道為什麼,說出這個名字,他不知道是誰的。
哈爾賓。福雷塞不是一個哲學家,也不是一個基督徒。事情就是這樣,在夜晚的一個森林之中把他從深深的睡眠下喚醒起來,他大聲地喊出這個名字,但他的腦海裏完全記不起它,這件怪事也引不起他探究的好奇心。他隻是覺得這很怪誕,伴隨著一陣小小的不在意的哆嗦,好像隻是順應一下這夜晚此時的涼意而已,他又躺下,進入睡眠,但他的睡眠不再無夢。
他覺得在夏夜濃重的黑暗裏白花花地亮著一條滿是灰塵的路,他沿著它前進。它引領著自己從哪裏來和到哪裏去,為什麼跟著它走,他不知道,盡管在夢裏這條路的一切看起來簡單和自然,因為在彼岸世界,這種憂慮不值得驚奇,正義正在審視著。不久他來到這條路的分叉處,前麵顯出另一條路,這條路很少有人走,從外觀看得出,真的,這條路遺棄的時間很長了,因為,他覺得,它會將自己引領到邪惡殘酷中去,但沒有任何遲疑。他跨了進去,由於傲慢的衝動,迫使他前進。
在他匆忙行進之時,他變得清醒了,他走的這條路是一條看不見的鬼魂纏擾的路,但他不能肯定。從路兩邊的樹林裏他捕捉到從一條奇怪的舌頭發出來的斷斷續續和支離破碎的耳語聲,盡管這樣他還是聽懂了一部分。他們那聽起來荒誕的碎片般的話語是在密謀反對他的肉體和靈魂。
夜現在顯得更長了,他在無邊無際的森林穿行,到處散布著時隱時現的悶悶不樂的光點,這些神秘的微光之下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投下影子。一個由舊的車轍輾壓出的輪溝形成一個淺淺的消沉的小池塘,它是新近的雨水形成的,微微閃著深紅顏色和他的眼睛相遇。他停下來,把手放進去,池水把他的手指染變了一個顏色,它是血水!血,他馬上認了出來,周圍到處是血。路邊茂盛生長的雜草的大大的、寬寬的葉片上留下潑濺的斑斑血痕。在紅雨過後,車道上到處是凝結幹燥的紅土塊,樹林的樹幹上布滿寬寬的深紅色的流跡,血從樹葉上象露珠一樣滴下來。
所有的這一切在恐懼中他都辨認得出來,這與他天真的預期完全不同。它是對他的一切犯罪的報應,盡管他清楚自己有罪。但他卻記不起來了。意識到周圍環境的威脅和神秘,這更增加了恐怖。他徒然地在回憶中追溯尋找,去再現他犯罪的那一刻:各種場麵和事件混亂地塞滿了他的腦子,一個場麵接一個場麵重疊,或者是一個迷惑和陰暗的混合體,但他隻能看見它們一閃而過。這種失敗更增加了他的恐怖,他感到有個人在黑暗中被謀殺了,既不知道是誰,也不知道為什麼。可怕的是這謀殺地點——神秘的光在這樣的緘默中燃燒,一個讓人畏懼的威脅。有毒的植物,大家都知曉的這些樹都帶著悲傷或憂愁的神態,明顯地泄露著毀滅他的安寧的模樣。在頭上到處令人心驚肉跳地聽到沙沙地密謀的耳語,在腳下的地裏生命的悲傷歎息是這樣的模糊不清——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在寂靜和懈怠中要發揮他的力量。以巨大的毅力去打破這詆毀的符咒,他在肺裏鼓滿了勇氣堅強地大喊一聲!他的聲音衰弱不堪,潺潺地融入那無以記數的陌生的聲音裏,變得含糊不清、結結巴巴,飄到森林的遠處,消逝在寂靜中。但他已開始反抗和振奮起來,他說:
“我將不服從無名之物。這些神靈不是帶著惡意通過這條被詛咒的路。我將寫下記錄並呼籲懇求離開它們,我會講述自己的過錯,我要忍受迫害——我,一個無助的人,一個懺悔的人,一個無罪的詩人!”哈爾賓·福雷塞隻在他懺悔之時才是一個詩人:在他的夢裏。
從他的衣服裏掏出一個小小的紅色皮麵袖珍書,這書有一半頁碼是當作備忘錄用的,他發現沒有鋼筆。他從一株灌木上扯下一根小樹枝,浸進血液的小池塘,飛快地寫著。當寫到書的下端時,他的小樹枝的尖頭幾乎觸不到紙頁,當一陣低沉而瘋狂的笑聲在遙遠的遠方響起的時候,這笑聲越來越響,使人覺得越來越近。沒有靈魂,冷酷無情,沒有歡樂的笑,象一個顛狂的瘋子,孤獨地隱居子夜時分的湖畔,這大笑變成了一種荒謬的吼叫,在這個高潮的高潮過後,它漸漸地,慢慢地消隱了,好像沮喪懊悔它的使用,從它來的彼岸世界的邊緣撤退回去。但這男人感到情況不是這樣——它離得很近,它並沒有離開。
一種奇異的轟響開始緩慢地抓住他的肉體和他的思想。他己說不出這種感受,他感到它作為一種意識——一種壓倒性的存在的神秘的瘋狂的信念——從看不見的世界向他壓過來,是某類超自然的異形,隻有神靈才能控製它。他知道它已使用了駭人的大笑。它現在好像已接近了他,從什麼方向過來他不知道——不能揣測。這以前的恐懼全部消失或混入巨大的恐怖之中,現在它已緊緊地抓住了他。要想從此處脫身,他想隻有一個法子:用寫作去呼籲懇求善良的神靈,才能橫越過這鬼魂纏擾的樹林,如果他拒絕毀滅的企圖,會有一些時間解救他。他驚人地迅捷地書寫著,他手裏的小樹枝的尖頭,血液細細地流淌。但在一句格言的中段他的手已拒絕為他的意誌提供幫助,他的胳膊落在身旁,書掉在地上,無力跑動或喊叫,他發現自己凝視著一張銳利憔悴的臉,那雙空洞無物、死去的眼睛正是他自己母親的,她清晰地、寂靜地立在屍衣的長袍裏麵!
二
在他青年時代,哈爾賓·福雷塞和他的父母親生活在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福雷塞家生活得很好,即使內戰的毀滅打擊,他們家庭在上流社會中仍有一個很不錯的地位。他們的孩子有時間也有地方享受他們交際和培植教養的機會,可以用愉悅的神情和優雅的思想與那些優良的社交圈和教誨進行周旋。哈爾賓是最年輕且顯得不強壯的一個,這也許很容易讓人去“溺愛”。由於他的母親的疏忽和他的父親的嚴厲,他有雙重的性格缺陷。老福雷塞不是一個平凡的北方人——是一個政治家。他的國家,或者確切地說,地區和州的事務,分享了他的時間和精力,他要求家裏的每一隻耳朵都要聽從他政治上的領導和置於他那震耳欲聾的訓斥之下,他自己的耳朵也在此列。
年輕的哈爾賓喜歡幻想、懶散,有一副相當羅曼蒂克的表情,對文學比對法律更為入迷,他對這一行是頗有修養的。他的家裏奉行的是公開地相互信任的現代原則,這一遺傳使他能很好地理解馬龍·拜勒的作品的特點,他母親那一係的偉大莊嚴的祖先,藉著月亮的一閃訪問過哈爾賓——馬龍·拜勒靠著他充分的努力獲得了不隻是一個小小殖民地詩人的榮耀,如果不以專業水準衡量的話,他的作品會相當引人注目。當某位福雷塞並非出於自尊而將祖宗的詩集的印刷品奢侈地收藏(印刷由家族付費,很久以前從冷清的市場收回來),哈爾賓確實很珍視祖宗的作品,偉大的死者,他那神聖的繼承人不合情理地崇敬自己的祖先。哈爾賓家族十分瞧不起那些智力愚鈍的膽小鬼,任何時候都會恥笑那些憂鬱的韻律和節拍。田納西州的福雷塞家是老練實幹的人——對大眾的信仰都不屑一顧,吝於去追求,隻對職業有益的東西表示興趣,對其他不適合職業的品德表示狂暴的輕視。
就公平地評價年輕的哈爾賓而言,他這種漂亮地忠實地再現精神和道義上的力量和才能,是得自家族中那位著名的殖民地吟遊詩人的真傳,這種繼承人的才能遺傳,純粹是神父的猜測。他不僅不知道怎樣招來詩神繆斯,也確實不能夠寫出一行品行端正的詩句從而把自己從傲慢的劊子手中拯救出來,他一直不知道當靈感休眠時如何去喚醒和撥動裏拉豎琴。
在這其間,這年輕人無論如何總還是一個相當自由輕鬆的家夥,在他和他母親之間有一種最完美的同情維係著,因為這位夫人秘密地把自己當作馬龍·拜勒的虔誠的弟子,作為女性,她非常圓通聰慧,非常推崇他的作品(輕視那些強壯鹵莽的誹謗者,堅持認為這些作品的本質頗有靈性),她總是小心對所有的眼睛隱瞞自己的愛好,隻是和他分享作品的歡樂。對這些作品的崇敬是他們倆共同的罪過,這使得他倆靠得更近。如果在哈爾賓青年時代他母親就“溺愛”他,他早已大膽地自我溺愛了。當長到壯年時,他做到了去走連細心的南方人都不敢選擇的路,在他和他美麗的母親之間有一種依戀——他一年年地長大,性格卻越變越溫和。這兩個羅曼蒂克的人明顯地不大注意行跡,在生命的交往中性別的因素占有很大的優勢,它可鞏固、軟化和美化親族的關係。這兩個人親密得不可分離,客人看到他倆的舉止往往錯以為他們是一對情侶。
一天,哈爾賓·福雷塞走進他母親的閨房,親吻了一下她的前額,撚著她暗色頭發上沒有被別針扣住的垂下來的一綹卷發,他帶著明顯經過努力才做出的冷靜,說:
“願你有一個偉大的反對意見,凱蒂①,如果我到加利福尼亞去幾個星期的話?”
這問題幾乎不需要凱蒂去回答,她自己那顫抖的嘴唇和臉頰已馬上回答了。明顯她有一個偉大的反對意見。在聽到確切的證言之時,她睜大棕褐色、大大的眼睛。
“啊,我的兒子,”她說,帶著無限溫情向上看著他的臉,“我知道這事遲早會來的。我常會半夜醒來垂淚,因為,有一半原因是,偉大的祖先拜勒已來到了我的夢裏,他的身影站立——年輕,也漂亮。——你也有同樣的夢嗎?當我仔細看著時我好像不能看清究竟是誰的容貌,我夢到你的臉上罩著一塊色彩鮮明的布,隻有我們死時才會放著這樣一塊布。你的父親對我大笑,但是你和我,親愛的,這樣的事情是不會有的。我看到布的邊緣下麵,在你的喉嚨上有被一雙手掐的痕跡。——寬恕我,但我們常常不願那神秘的世界總出現這樣的事。也許你會有另一種說法,也許它的意思不是你將去加利福尼亞,或許你將帶我一起去?”
這話是坦誠的,夢裏的設計扮演的意味,在新近顯露的跡象的啟示下,經過她的兒子更多的邏輯判斷也不能使他十分信服。他對最初的一瞬預兆的確有著更多的單純直覺,如果缺少悲壯的話,會比暴風雨侵襲太平洋海岸帶來更大災難。這是哈爾賓·福雷塞的猜想,他會被勒殺在滿是石南灌木的荒野裏。
“在加利福尼亞有沒有轉危為安的可能?”在他有時間去真實給她釋夢之前,福雷塞夫人繼續說——“那裏可以讓我從風濕痛和神經痛中恢複過來?看——我的手指感到如此僵硬,在我睡覺時我真是被它們弄得疼痛難忍。”
她把手從他審視的目光中抽了回來。哈爾賓對她的病例診斷有了一個最好隱藏起來的想法,他的臉上帶著史學家無力陳述時的冷笑,為了他自己,他感到還是不去說手指並不僵硬為妙,隻需說明微不足道的疼痛的原因,他很少去聽從醫學的檢查,那種誠實無欺的病人渴求處方的陌生場麵他從未見識。
夢的結果是,兩個奇特的人有一個相同的奇特的順從的看法,一個去到加利福尼亞,這是他的委托人要求的,另一個留在家裏順從地保持一個希望,她的丈夫對此毫不知情。
在舊金山的一個黑夜裏,哈爾賓·福雷塞沿著城邊的海岸散步。一個意料不到的事震驚了他,也讓他困窘不堪,他成了一名隻拿工錢的水手。他事實上被幾個匪徒脅迫到一條華麗又華麗的船上,要航行的南太平洋去。這不是他航行中災禍的結尾,這船被拋棄到南太平洋一個小島的岸上,六年之後劫後餘生的人才被一條鹵莽的從事貿易的縱帆船帶回舊金山。
雖然錢包裏沒錢,經過這些年的磨難,福雷塞比起少不更事的同時代青年,年齡看上去要大很多,但精神上並不缺乏自尊。他不需要陌生人的幫助,他和一個生還的同伴生活在聖海倫娜城附近,等待消息和從家中過來的彙款,他已經開始打獵和做夢。
三
在鬼魂出沒的森林,幽靈麵對著做夢者——像是喜歡,又像不喜歡,他的母親——毛骨悚然!在他心裏激起的既不是愛也不是希望;帶來不是對金色往事的愉快回憶——產生的不是任何情感;所有美好的念頭給恐懼吞噬了。他試著從它麵前轉身和逃掉,但他的腿不聽使喚;他不能從地上拔起腳。他的胳膊無助地垂掛在身上;隻有他的眼睛還轉動自如,這些都讓他不敢從這幽靈灰暗的眼球下移動,他知道沒有軀體也就沒有一個靈魂,但事情在鬼魂纏擾的森林全被攪亂了,變得糟透了——有肉體可以沒有靈魂!在空洞的瞪視裏,既沒有愛,也無憐憫之心,也不存在理解力——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仁慈的東西。“沒有勇氣才會呼籲”,他想,他荒謬地大聲辱罵起來,反而,這使得形勢更為可怕,就好像企圖用雪茄煙的紅火頭照亮墳墓一樣。
一個瞬間,看起來如此漫長,世界在歲月和罪過之中變得古老了。鬼魂的叢林,決心把恐怖推上窮凶極惡的頂點,所有聲音和景色從他身體的意識中消失,幽靈離他不到一步,對他抱著野獸般毫不顧慮的惡毒;伸直它的手,帶著令人震驚的凶暴蹦了過來!這行動激活了他身體的力量卻沒有讓他的意誌激活;他的思想仍被鎮懾住,但他強健的身體和機敏的手足卻自己盲目地、剛強地、良好地抵抗起來。因為一個瞬間他好像看見癱瘓的思維和強健的肌體發生了不自然的衝突——這種觀察的嗜好隻有在夢裏才會有;然後他回到自身,就像一下跳進他的身體裏,激活的意誌開始指揮身體與醜惡的敵人一樣機敏、凶猛地進行搏鬥。
但什麼能與他夢裏的動物進行抵抗?想象中創造的敵人已經贏得了征服,戰鬥的結果是戰鬥的原因。不管他的努力——不管他的力量和敏捷,看起來都是無用的浪費,他感覺冰涼的手指合攏在他的喉嚨上。掙紮著向後倒在地上,他看見在他的上方,他抵抗的手後麵那張死亡的憔悴的臉,然後一切陷入黑暗中。一個聲音仿佛遠方的鼓在敲擊——一種蜜峰的嗡嗡喃喃的聲音,一聲遠方尖利的叫喊,所有歸於沉寂,哈爾賓·福雷塞夢見他死了。
四
一個濕霧彌漫的早晨會跟著溫暖、潔淨的夜接踵而來。前一天的午後,明亮的霧氣輕輕地飄動——它隻是變濃的大氣,雲彩的幽魂——可以看到它們粘附在聖海倫娜山峰的西邊,持續不斷地靠著山峰的近旁向荒涼的高處上升,它是如此的輕薄,如此的清澄,猶如按想像做出來的,一個人會說:“快點看!一下它就過來。”
隻一個瞬間,它明顯變得巨大、濃重,抓住了山體,它膨脹著,膨脹著,前進又前進,進入了低低的坡地的上空。在同一時間它向北向南擴展,帶著聰明的打算一心一意地把山腳邊的小塊霧團連結起來,形成一個完全的整體。它成長、不斷成長,從山穀望過去,頂峰也從景色中消失了,山穀上空,它籠罩了整個天空,顯得曖昧,灰暗。在卡利斯托加,它位於山穀的入口和山峰的山腳,這裏會是一個沒有星星的夜晚和沒有太陽的清晨。這霧下降進入山穀,向南延伸,吞噬了一個又一個牧場,直到它塗刷掉聖海倫娜城,這已離山穀有九英裏之遙。滿是塵土的路趴著,樹林在霧中茫然若失,鳥兒們靜靜地躲在掩蔽處,早晨的光線顯得抑鬱、蒼白,猶如鬼魂,既無色彩又無激情。
在黎明最初的微明中,有兩個人離開了聖海倫娜城,他們沿著路穿過山穀向北邊的卡利斯托加進發。他們肩上掛著槍,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意圖,都會誤認為他們是打鳥或捕獸的獵人。他們一個是拿帕縣的代理警長,另一個是從舊金山來的偵探——分別是霍克爾和葉賴爾森,他們的職責是獵“人”——去捕捉人。
“它有多遠?”當他們大步行進時,霍克爾詢問,在他們的腳下濕乎乎的路麵裏,騰起一陣白色的灰塵。
“白教堂?隻一英裏半還遠一點,”另一個回答。“由這條路過去,”他補充道,“它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教堂,它是一座被廢棄的校舍,隨著歲月和廢棄變成灰黑色了。在它裏麵曾經舉行虔誠的宗教活動一當它還是白色的,有一片墓地會讓詩人興奮。你猜我為什麼帶你到這裏來,告訴你還帶著武器?”
“噢,我從不為事情的類型去打擾你。我發現當時機到了你總是很愛說話。但如果我冒險一猜的話,你是要我幫助你在墓地裏拘捕一具屍體。”
“你還記得布朗斯科姆嗎?”葉賴爾森說,對他同伴的智力帶著一種疏忽的態度。
“那個割斷了他妻子的喉嚨的家夥?我當然沒忘,我為他花了一個星期的功夫,為了我的焦慮,我付出了代價。這裏有一筆五百美元的懸賞金,但是我們的人沒有誰看到他。你的意思是說
“正是。他一直在你的同伴的跟蹤下,他夜晚會來到白教堂的老墳地。”
“這魔鬼!警察們在那裏埋葬了他的妻子。”
“好,你的同伴能斷定他將晚上返回她的墳墓?”
“在那非常靠後的地方任何人都期待他回來。”
“但你們已經搜索了所有其它地方,明白了自己的疏忽之處。我保證他就在這裏。”
“你發現過他?”
“真可惡!他發現了我。這惡棍撲倒我——倒拖著我,讓我旅行了一圈。這是上帝的慈悲,他沒有結果我。噢,主是一個好人,如果你貧困的話,我想將賞金的一半分給你就足夠了。”
霍克爾興致大增,他大笑,解釋說他的債主從不喜歡糾纏不休。
“我僅僅隻是想讓你看看現場,和你一起安排一個方案,”偵探解釋說。“我想我們必須武裝起來,甚至白天也得如此。”
“這人肯定是一個瘋子,”代理警長說,“這懸賞是為逮捕他和判他罪準備的,如果他是瘋子,他將不會判罪。”
霍克爾先生突然意識到審判可能失敗而受到深深震動,他不自覺地停在路中間,減低了熱情,繼續向前走去。
“是的,他明白這事,”葉賴爾森承認說,“我要跳到這個不刮胡子、不剪發、不整潔而且又臟又破、不值一文的可憐蟲身上,我看古代沒有這種規定,我要踐踏這可敬的法令。我為他來了,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溜掉。不管怎樣,榮譽屬於我們。沒有其它任何靈魂知道他是在月光照耀的山峰這邊。”
“好的,”霍克爾說:“我們將去那兒再觀察一下地形,”他補充了一句,這是他喜愛的一個墓碑上的銘文:這裏,你必須馬上躺下。“——我意思是說老布朗斯科姆曾經因你的鹵莽闖入而與你交手。順便說一下,我另一天聽到消息,布朗斯科姆不是他的真名。”
“真名叫什麼?”
“我記不起來了,我已經失去了對這個可憐的家夥的興趣。在我的記憶裏確定不了這個名字——他倆看起來象一對夫妻。當他碰到一個婦女——一名寡婦,他就狂熱地去割斷她的喉嚨。她到加利福尼亞是來尋找一個親戚,你一定知道這些事。”
“當然。”
“但不知道她確切的姓名。通過什麼啟發你發現了確切的墳墓?告訴我那人的名字叫什麼,他是用床頭板割開喉嚨的。”
“我不知道確切的墳墓,”葉賴爾森羞於承認他的逮捕方案有一個重要缺陷,“我已經知道那個墳墓的大致地點,我們今夜的工作就是認明這個墳墓。這兒就是白教堂。”
它離路邊還有很遠一段距離,相鄰的兩邊都是田野,但在它的左邊有一片櫟樹林、石南樹灌木叢和在低窪地段升上來的龐大得驚人的雲杉,在流動的霧中,朦朦朧朧象鬼影。那些樹叢長得極為繁茂,隻是很難穿過去。過了好一會兒,霍克爾沒看到任何建築物,但他們走進樹林,透過濃霧現出白教堂灰暗的輪廓,看上去很大和很遠。走了沒多遠,它完全顯露出來,隻有一個大樹枝那麼高,引入注目,潮濕陰暗,規模很小。它是通常縣城裏的那種——校舍——屬於那種包裝盒似的房屋結構,有一個石製的基座,屋頂生滿青苔,空空的窗洞,玻璃和窗框很久就沒有了。這座建築被破壞了,但還不是廢墟——它在加利福尼亞廣為人知,作為“過去時代的遺跡”收入到旅遊向導手冊裏。粗看上去,這建築毫無趣味可言。葉賴爾森走進滴著水珠的樹叢。
“我將向你指出他抓住我的地方,”他說,“這是一片墳地。”
這裏和那裏的灌木叢到處把墳墓包圍著,墳頭上是肮臟的石頭,墳腳是腐爛的木板,一個個東倒西歪,少數一些還算平展。毀壞的尖木樁撐起的籬笆把墳地圈起來,還有一些墳堆被落葉包圍著。有很多墳墓沒有標出可憐的墓中人的任何身世簡介——隻殘存著朋友們相互悲痛的循環輪回——除開那陰沉的大地,它比悲悼者的精神更為持久。小路,如果曾有任何小路的話,也早已被歲月風雨草木擦拭掉了。一些大樹從墳地裏長出來,它們的根或枝條戳進了圍起的籬笆。作為一個遺忘了的死者的村莊,所有放棄和毀壞的態度是再也適合不過,再也重要不過了。
當這兩個人,葉賴爾森作為前導,通過一片年輕的小樹林向前推進時,冒險者突然停下來,把獵槍舉到胸膛,發出一個低聲的警告,靜靜地站著,他的眼睛牢牢地盯住前麵的某種東西。他的同伴和他做得一樣好,由於灌木叢的阻擋,他的同伴,盡管什麼也沒看到,也仿效他的姿態,警惕地站立,為可能發生的事。作好準備。這一刻過後,葉賴爾森謹慎地向前移動,另一個緊隨其後。
在一棵凶暴龐大的雲杉的枝條下,躺著一個男人死去的軀體。他們靜靜地站在它的上方,第一次被這樣的異常震動了——這臉,這姿勢,這衣著,無論什麼思維最敏捷和清晰的人也回答不了這一個令人同情、好奇的問題。
這屍體背落地躺著,腿大大地叉開,一支胳膊向上戳起,另一支胳膊伸向外,但後者劇烈地彎曲,手僵在喉嚨附近。兩隻手都緊緊地握著。這整個姿勢是一種拚命而無效地去抵抗——什麼?
他倆端著獵槍,身上披著鳥的羽毛的迷彩服,挨近目標。一切顯出奮力掙紮的跡象,他倆看見一些小小的惡毒的萌芽——櫟樹彎曲下來,樹葉和樹皮被撕裂掉,凋零和腐爛的樹葉被不是他們倆的一雙腳推開並堆積成山脊一樣,靠近死者的腿旁,旁邊的滿地的薔薇果明顯地顯出一個人的膝蓋的印跡。
對死者的喉嚨和臉匆匆一瞥,讓掙紮抵抗的證據變得更充分了。雖然胸部和手是慘自的,其它的身體部分卻都是紫的——差不多是黑的。肩部靠在一個低矮的墳堆上,頭扭向背部,怒睜的眼睛轉回來空洞地凝視著腳部的方向。張開的嘴裏填滿了泡沫,舌頭烏黑地、腫脹地從嘴裏伸出來。喉嚨毛骨悚然地青腫,不僅有手指的印跡,而且被兩隻強壯的手搗碎撕裂了,這必須是在放棄情愛之心後才做得出,直到死了很久之後,還一直這樣保持駭人的掐住。胸膛、喉嚨、臉都是潮濕的,衣服濕透了,露珠,從霧中凝凍出來,鑲嵌在頭發和胡須裏。
看著這些,兩人一聲不吭——差不多隻是匆匆一瞥。然後霍克爾說:
“可憐的魔鬼!他被粗暴地施刑。”
葉賴爾森警醒地掃視著森林,他的獵槍用兩手端著,打開了扳機,手指扣在板機上。
“瘋子的傑作。”他說,他的眼睛沒有從掃視樹林的工作中收回來。“它準是布朗斯科姆的同夥幹的。”
有個東西半埋在亂糟糟的樹葉和泥土裏,引起了霍克爾的注意。它是一本紅色皮麵的袖珍書。他撿起來,打開它。它是應急的備忘錄,在第一頁上寫著一個名字“哈爾賓·福雷塞”,後麵幾頁是紅色的筆跡——好像是匆忙寫就的,勉勉強強還看得明白——那些一排排的詩行,霍克爾大聲朗讀,而他的同伴繼續審視著他們狹窄世界的這種朦朧昏暗的氣氛,聽見水珠從每一個重負的枝頭,滴下來的聲音:
這神秘魔咒的奴役,我站在
這受到蠱惑的樹林的幽暗裏,
柏樹聳立著,桃金娘纏繞著她們的絞刑架,
暗示著那些罪惡的兄弟。
搖曳的柳樹與紫鬆密談,
在他們之下,是仇恨的龍葵和芸香,
還有永恒的花朵一直編織奇異
陰森的事情,恐怖的蕁麻在生長。
密謀的幽靈在幽暗中耳語,
僅有一半聽得清,墳墓寂靜的秘密,
血從樹上滴下,葉子
和一朵紅潤的花在迷惑的光中閃耀。
我大聲喊叫!——魔咒,紋絲不動,
讓我的精神和我的意誌入睡。
沒有靈魂,沒有聲音,沒有希望,唯有孤獨,
我努力掙脫這病態的荒誕預兆!
最後看不見——
霍克爾停下來,不能再讀。原稿在這一行中間中斷了。
“這詩的聲音像拜勒,”葉賴爾森說,他的行事方式裏有一些學者的東西。他減少了他的警戒,站著向下注視屍體。
“誰是拜勒?”霍克爾頗不在意的問。
“馬龍·拜勒,一個國家早期曆史上很是有名的家夥——在一個多世紀以前。他的作品憂鬱,令人窒息,我有他的作品選集。這詩不在其中,可能錯誤地遺漏了。”
“這裏天氣真夠寒冷,”霍克爾說,“讓我們離開這裏。我們必須從拿帕叫來驗屍官。”
葉賴爾森什麼也沒有說,但順從地走開。他從死者頭部和肩部躺的那塊略微高一點的地麵經過,他的腳碰到腐爛的樹葉下的一個東西,他費力地踢出來去察看,它是一塊落下來的床頭板,上麵色彩鮮明地寫著幾個幾乎不能解釋的字,“凱瑟琳·勞萬。”
“勞萬,勞萬!”霍克爾突然興奮地驚叫,“噢,那就是布朗斯科姆的真名,他和這婦人並不是夫妻關係。讚美我的靈魂!它是怎樣的福至心靈——謀殺那位婦女的人的名字有了,就是福雷塞!”
“這裏麵存在某些卑鄙的神秘,”葉賴爾森偵探說,“我憎惡這類事。”
他們從迷霧中走出來——看起來離墳地很遠了——一個大笑的聲音響起來,低沉,從容不迫,沒有靈魂的笑,與在不毛之地內夜晚潛行的鬣狗的笑相比,沒有更多的快樂。一個大笑慢慢地增強,上升出來,響亮,更響亮,更清晰,越來越清晰得讓人毛發直豎,直到它們那狹窄的循環的想像之外的頂點,這種大笑如此不近人情,如此沒有人性,如此凶猛冷酷,它降落下來,讓兩個“獵人者”產生了無法形容的敬畏!他們既不能移動武器也不敢想到武器,駭人的聲音的威脅不是用手來接觸到的。它慢慢地消逝下去,現在它漸漸止息了,最後的一聲喊叫消隱在他們的耳朵裏。它最後退到遠方,沒有快樂和機械地持續著,直到忘記這一切,下沉在寂靜中,龐大地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