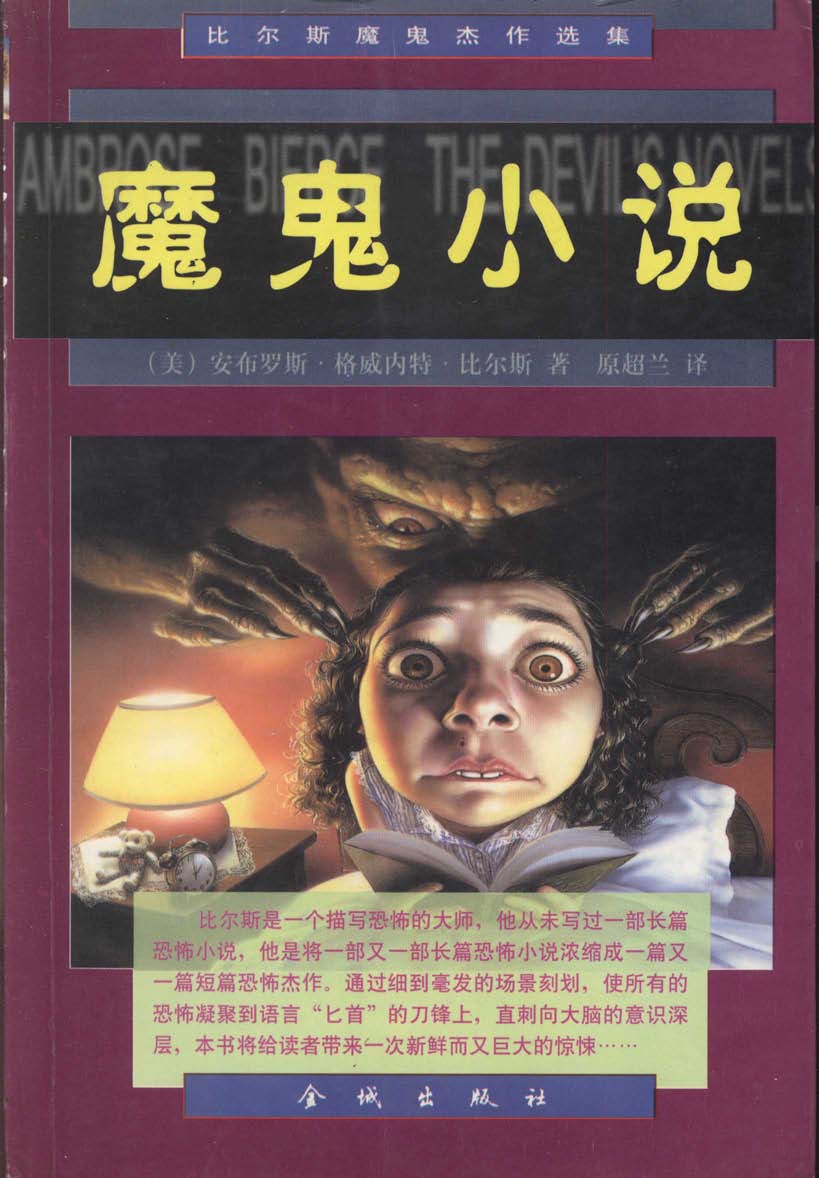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貓頭鷹河橋上的絞殺
一
在亞拉巴馬州北方,一個男人正立在鐵橋邊,俯視著腳下20英尺外的湍急河水。這人的雙手倒捆在後,手腕被繩子綁在一起,一根粗繩不很緊地套在脖子上,他的頭被縛在一個木絞架上,繩子鬆弛的一端垂到他的膝蓋邊,幾塊鬆動的木板正可供這位瞌睡者支撐在鐵軌上,而他的行刑者——兩個聯邦軍的士兵,由一個中士指揮,這個中士不當兵的話很可能是一個不錯的助理法官。臨時站台上一個佩戴軍銜的軍官,全服武裝,來回踱步,他是個上尉。橋的每一端都有一個哨兵,拿著槍站崗,這種哨位通稱為:支柱,就是說,前臂托住槍把經過胸部——一個生硬垂直拘謹的部位,將槍靠在左肩上,使身體保持一個筆直的姿態。
還沒有跡象表明這兩個士兵知道在鐵橋的中間會發生什麼事,他們隻是封鎖這裏不讓人通過,橋兩端的哨兵互望不見,這條鐵路徑直延伸到一百碼開外的一個森林,然後拐個彎,消失在視野外,無疑,遠處有一個堡壘,河對岸是一片開闊地,一個和緩的斜坡上直立的三棵樹幹紮成圍欄,黃銅製大炮口正伸出來俯視著鐵橋,在橋和壁壘之間的斜坡中段是些旁觀者,一隊站成一條線的士兵,正作“操練中的稍息”,槍托著地,槍管稍稍傾斜,靠在右肩,雙手扶在槍把上,一個中尉站在隊列的右端。他的軍刀刀尖著地,左手擱在右手上,除了在橋中間的四個人,再也沒有一個人動彈,這隊士兵麵向著鐵橋,如磐石般注視著。一動不動。哨兵麵對著河,象塑像一樣裝飾著鐵橋,這個上尉交叉著雙手站立,一言不發,看著部下的行動但沒有任何表示。死亡是一位貴族,當他駕臨時,都會受到正式的敬意,甚至對他最熟知的人。在軍規的條例中,沉默和固定是服從的形式。
這個男人被套著,約莫35歲,他是一介草民,單從他的服飾判斷可看出他是種植園主。他的麵相不錯,挺直的鼻梁,堅毅的嘴唇,寬寬的前額,長而又黑的頭發,筆直地梳理直垂在耳際的外衣領口邊。他長著一撮小胡子和尖尖的下頦,但沒有一點絡腮胡子,他的雙眼很大,灰黑色裏有種和善的表情,幾乎不能想像這人的脖子套在絞索裏。顯然這一切都不是粗俗的刺客能幹的,豐富的軍規條例對絞死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具體規定,而紳士是不包括在內的。
各種預備正在完成,兩名聯邦士兵走到一邊,每人將要抽掉正站著的木板。這個中士轉向上尉,行了個軍禮,馬上就站在上尉身後,上尉接著邁開一步,下麵的行動留給了受刑者和中士,他們正站在同一塊木板的兩端,這塊木板架在橋的三根枕木上,這個受刑的人站的位置幾乎差一點點就是三根邊的第四根枕木了,這塊木板剛才一直被上尉的體重恰好平衡住,現在也被中士所平衡著。
一個信號如從上尉那兒發出,中士將會跳向一邊,這塊木板將傾倒,而受刑者將從兩條枕木中間落下而被吊起來。這個男人對這個安排本身已作出了簡單而有效的判斷。他的臉既未蓋住雙眼也未蒙瞎,他盯住他的“馬上不能立足的落腳點”,眼光遊蕩在腳下急流的漩渦上,一片隨波逐流的浮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雙眼和木頭一起起伏,真慢啊這木頭移動著,水流多麼舒緩。
他閉上眼睛為了最後再好好想想他的妻子和孩子,這水被清晨的陽光塗抹得金光亮霞,在河岸遠處是沉沉的朝霧,這些士兵們,這一片浮木,都使他神思恍惚。現在他意識到了一個新的騷擾,他正想著他的親人,不料被一個聲音撞擊著,這聲音他既不能不聽,但也聽不明白,很尖銳的、清晰的、金屬般敲擊聲,與鐵匠的鐵錘同鐵砧的相撞聲,真是異曲同工。他不知道這聲音是什麼,是在很遠的地方還是在近旁——好像都是。這聲音很有規律和喪鐘的鳴響一樣緩慢,他等待每一個敲擊,沒有反抗。也沒有理解,這沉靜的刹那顯得過於漫長,這延續的沉靜使人迷狂隨著這沉靜刹那越來越稀有的聲音,變得更響更尖厲了,這聲響象一把刀刺進他的耳中,他害怕,他要尖叫起來。他所聽到的是他手表的嘀嗒聲。他不能閉上雙眼,他再看看身下的河水,“如果我能使雙手鬆綁,”他想,“我就能扔掉絞索,跳入河中,潛入水中我就能避開子彈,猛力地遊到岸上,跳進樹林裏,然後回家,我的家——謝謝上帝,還在他們的視線之外,我的妻子和孩子離這幫入侵者還遠著呐。”
這些念頭一下閃進了他的腦中,與其等死,不如試它一試,這時上尉衝著中士點了點頭,這個中士馬上跳向一旁。
二
佩頓·法誇爾是一個富有的莊園主,屬於亞拉巴馬一個受人尊敬的世家。作為一個奴隸主,而且也象其他奴隸主、政客一樣,他很自然地是一個天然的分離主義者,並且很熱心參與南方的事務,這些環境產生了他固執的稟性,阻止了他效力於、服務於這些英勇的同沒落的奴隸製進行戰鬥的士兵。他在這默默無聞的克製中十分焦躁,他盼望他的巨大精神壓力得以解脫,更多士兵的生命得到解脫,並有機會獲得榮譽。這個機會,他感到將要來臨,就象戰爭的一切來臨一樣。因此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對他來說因為太卑微了,而不能幫助南方,也沒有去冒風險,因為太危險會承受不起。如果始終如一地具備這樣一個平民化的品質,這個平民應該內心是一個士兵,他非常忠誠,沒有什麼太多的資格同意一個無賴的詭辯,無論是卷入愛情還是戰爭之中。
一天夜晚,當佩頓和他的妻子正坐在一個很土氣的小凳上,就在他莊園的入口處,一個身穿灰布軍裝的士兵騎著馬來到他的門前討一口水喝,佩頓夫人隻記著高興而沒有立即用白淨的手去取水。當她進去取水時,他丈夫湊近這很臟的騎兵,急切地打聽著前線的消息。
“聯邦軍正在修鐵路,”這個騎兵說,“為另一支先頭部隊作準備,他們已經到達了貓頭鷹河橋邊,奉命把守,在河的那邊建起了圍欄,指揮官發布了命令,已經到處張帖,命令說無論那一個公民幹擾了這條鐵路,鐵路橋,掩體或者火車,都要被絞死,我看過這命令。”
“這兒到貓頭鷹河橋有多遠?”佩頓問道。
“大約30英裏。”
“那河的這邊有部隊嗎?”
“隻有一個哨所在半英裏開外的鐵路邊上,有一個哨兵在橋的這一頭。”
“想想一個男人——一個平民和學生會被吊死,隻好要麼避開哨兵或者遇到一個善良的哨兵,”佩頓說著,微微一笑,“你看這成嗎?”
這個士兵馬上作出反應,“我在一個月之前,”他說道,“我注意到去年冬天的洪水給橋的這一端的木材碼頭帶來了大量飄浮的木頭,現在木頭很幹,可以象亞麻屑一樣燃燒。”
這時夫人已經端來了水,這士兵馬上喝完了,非常客氣地道謝,並向他的丈夫鞠躬,然後騎馬而去。一個小時後,在夜幕降臨時,這位騎兵又重新路過莊園,向著北方他來時的方向而去。他是一個聯邦軍的偵察兵。
當佩頓徑直掉下橋時,他已失掉了意識,象個死人樣了,從這種狀態中醒來——後來,似乎對於他來說,由於喉嚨被強勒得非常疼痛,隨即有種被窒息的感覺,鋒利的、刺激的極大痛楚象槍擊一般從他脖子以下滲透到他肢體的每根纖維,這疼痛沿著非常清晰的血脈而扯動,撕扯著不可想象的十分短暫的間歇。它們像跳動的火光灸烤著他達到一個不能忍受的溫度,對於他的頭部,他什麼也不能意識到,除了衝血的感覺,這些感覺是思維所不能伴隨的,他智慧的稟性已經被抹掉,他隻是有力量感覺劇痛,他想動一下,被一片發亮的雲包圍,他現在隻擁有像炸裂的心,通過一個無意識的震蕩的弧光,象一個巨大的鐘擺。隨即可怕的突然,這些弧光伴隨著刺耳的沙沙作響的噪音向他襲來,在他耳際可怖地咆哮,四周冰冷而黑暗。思維能力恢複過來了。他知道這絞繩斷了,而他掉進了河裏,再也不會再來一次絞刑,這脖子上的絞索已經使他呼吸困難,他在黑暗中睜開眼,想看看他頭上的一絲光亮,但是真遠啊,多麼不可能的事,他現正在下沉,因為光亮正變得越來越弱,直至成了僅有的一瞥微光,然後又開始變得亮起來,他知道又在向上浮起來,艱難地意識到他現在感到好受些,“要被絞死和淹死,”他想,“這可不好,但我不願被槍打死,不,我將不會中彈,那不是好事情。”他沒有意識到一個結局,但手腕刺痛提醒了他要讓雙手鬆綁,他集中全力搓動著,象一個懶漢觀看變戲法的技藝,對結局沒有興趣。多麼絕妙的努力,如此壯觀,如此超乎人類的力量,啊,這是多麼了不起的全力以赴!太好了,繩子鬆開了,他的手臂分開了並向上浮起,雙手在漸亮的光線中仍看得有些模糊,他用新的興趣象第一次看著雙手,然後,一隻手猛地扯掉脖子上的絞繩,絞繩扯掉了,用力甩向一邊,它們起伏著象一條水蛇,他想他該對手大喊出這些話:
“手鬆開了,手鬆開了。”
絞繩被成功地解開了,經曆了一陣巨痛後,他的脖子疼得可怕,他的腦髓在燃燒,他的心一直飄動,現在來了一下有力地躍動,試圖從他嘴子跳出來。他整個身體遭受著無助痛苦的無盡磨難!但他雙手一點不聽使喚,它們很快地劃動用力打著河水,他盡力露出水麵,感覺到頭浮出來了,他的雙眼被陽光刺得睜不開,他的胸部抽搐著、膨脹著,隨著肺部急劇的疼痛吸了一大口氣,他尖叫著不停呼氣。
他現在才擁有了肉體的知覺,這些知覺,確實不可思議地渴望和敏感,他的經過可怕幹擾的器官係統,現在可以對一些事情作出有效的接收和精選了。他感到水的波紋蕩漾在臉上,他聽到河水撞擊的聲響,他看著岸邊的森林,看見一棵棵樹,葉子和每片葉子的葉脈,看見上麵的小蟲、蝗蟲,亮亮的身軀飛舞,灰色蜘蛛從一個枝椏至另一個枝椏織著網,他看得眼花繚亂,色彩閃耀在一百萬片草葉上,蚊子嗡嗡在漩渦上飛舞,蜻蜓的翅膀扇擊著。
水蜘蛛的細腿撫摩著,象支槳劃著船,這一切都是動聽的音樂,一條魚在他眼前滑過,他聽見魚從水麵躍起的擊打聲。他浮在水麵,臉朝著河水,一會兒,看得見的景物象個車輪慢慢轉動著,以他自己為軸心,他看見這橋,這堡壘,岸上的士兵、上尉、中士、二個士兵——他的劊子手,普天之下他們都在黑色的輪廓中,其他人沒有武器,他們的動作奇形怪狀而可怕,他們如巨人一般。突然他聽見尖厲的爆炸聲,某樣東西在他頭上擊打著河水,濺在他的臉上。他聽見第二聲爆炸,看見一個哨兵舉著槍,一小片藍色煙霧從槍口裏吐出來,水上的人看見橋上士兵的眼睛正通過槍的瞄準器,對著他,他觀察到這是雙灰色的眼睛,還記得這雙灰眼好敏銳,所有著名射手都是這樣的一雙眼,然後,這人一下又消失了。
一個漩渦卷來,法誇爾轉了半圈,他又警覺地看著岸上堡壘對麵的森林,一個清晰高昂的聲音,單調地在他背後歌唱,聲音傳到水麵,清晰地穿刺進並卷走了所有水域其他的聲音甚至耳邊水波的拍打聲,盡管不是士兵,他有足夠的常識去懂得需要細細想、慢慢說出、渴望吟唱的死亡意義,清晨,中尉在岸上正忙碌著。多麼冰冷和可憐,他平穩、冷靜的音調,迫使這些士兵安靜下來,在精確可測的間隔,降臨這些冷酷的詞語:“全體立正……舉槍……
準備……瞄準……開火……”
法誇爾潛入水中,盡可能深地潛入。水在耳邊咆哮,象尼亞加拉瀑布,他還聽見齊射的雷鳴,又浮上水麵,遇見彈片閃閃發光,特別亮滑,正慢慢地擺動向下沉落,一些金屬片觸到了他的臉和手,然後沉入了水底,一片留在了他的脖子和衣領之間,它有點燙,他抓出扔掉了。
當他浮出水麵大口喘息,他意識到在水裏已呆了很長時間了,他現在察覺到潛得越深,向著安全就更加靠近。這時士兵們已將子彈上栓,彈片立即在陽光下閃光,在空中滑落。這二個哨兵再次開火。
這個被獵捕的人從他肩上看清這一切,他正用盡全力地遊著,他的頭腦現在和他的手臂與大腿一樣有力,他的思維像閃電一樣迅捷。
“這個指揮官,”他推斷,“將不會第二次犯指揮不當的過失。齊射比點射更容易躲閃開,他可能已經下令可隨意開槍,上帝保佑,我再也躲不過了。”
在離他兩碼遠的四周,尖厲的槍聲激起了震驚的水花四處飛濺,槍聲漸漸弱了,仿佛穿過空氣回到了堡壘,一聲爆響攪動到河的最深處,然後死寂!一浪高聳的河水,猛撲向他,使他沉落,使他失明,象在絞死他!大炮在這場遊戲中開始負起作用,在潰退的水麵的騷動中他自如地搖動頭,他聽見射歪的子彈在前邊的空氣中嗡嗡作響,打斷遠處的森林中的枝椏。
“他們再也不會用這種子彈了。”他想,“下次他們將會裝上葡萄彈,我必須死死地盯著槍,槍口一冒煙,我就得躲閃,不然就遲了——這好極了的槍彈。”
突然他感到天旋地轉,轉得象個陀螺,這河水,這岸,這樹木、不遠的橋,堡壘和士兵,都變得模糊起來,物體隻是由色彩顯示,循環的水平麵的彩色條紋,就是他的全部所見,他陷入旋渦中,旋轉著,以令他眼花繚亂的前進速度,一會兒,他就摸到了腳下左岸邊的礫石——南邊的河岸——就在一個射擊點後麵,使他在敵人眼前得以隱身,對突然而來的旋渦,他的一隻被沙石擦破皮的手救了他。他高興得流淚了,他的手指插進沙中,抓起一滿把沙,喃喃為沙灘祝福,河沙看起來像金子,像寶石,紅寶石,綠寶石,他想沒有什麼比這更美麗的。這些河岸上的樹木都是巨大的花園植物,他注意起樹木固定的排列順序,吮吸著花的芳香,一道奇怪的光芒通過樹幹間隙照射進來,風使樹枝發出豎琴般的樂聲,他沒有任何逃離的願望,心滿意足地陶醉其中,在樹枝間葡萄彈的颼颼聲哢嗒哢嗒聲把他從夢幻中喚醒,岸上炮兵已經開炮,他向他們隨便道了聲再見,一躍而起,衝出傾斜的岸邊,一頭紮進樹林。
他一路行進,這森林似乎漫長無邊。
沒有任何地方可發現個出口,甚至找不到伐木工的小道。他不知道他活在這樣一個荒野之地,有些東西變得神神秘秘,到了日落,他感到有些疲勞,饑餓,腳疼,想到他的妻子和兒女正盼他歸來。最終他發現了一條路,這條路導引他走向正確的方向,這條路寬寬的又很筆直,就象城市街道,不象是在旅途,沒有邊緣,沒有人居住,沒有那麼多狗吠叫驚醒居民,大樹黝黑的枝杆在大道兩旁形成了一道筆直的牆壁。
牆壁又終止於平麵上的一個點,象培養洞察力的課堂上的圖解。當他向上看著樹枝間的縫隙,閃爍著金色的星辰,但看起來有點陌生,象聚集在奇怪的星座,他確信它們被某種次序所安排,這種次序具有神秘而誹謗的意義,森林的每一邊都充滿獨特的嘈雜聲,在其中——一次,二次,再次——他清晰地聽見了低語,以不可知的語言。
他的脖子還很疼痛,把手伸向脖子,他發現脖子腫起來,他知道脖子上有圈被絞繩勒出的瘀傷,他的眼睛感到充血,難以閉上。他的舌頭因幹渴而脹腫,他把舌頭伸進冷冷的空氣中以減輕舌頭的燥熱。多麼柔軟啊,這草皮覆蓋著並非旅途的大道,他不再能感覺到腳下的歸路。
毫無疑問,任憑苦痛紛湧,他行走時都昏昏欲睡,現在他又看見了另外一個景象——可能他僅僅是從昏迷中恢複過來,他站在他自己的家門口,一切依舊,在朝陽映照下,一切都是那麼明亮而美麗。他一定跋涉了整夜,當他撲去開門,通過寬亮的人行小道,他看見了令心悸動的女式外衣,他的妻子,氣色新鮮,衣著素淨而笑容甜蜜,從門廊上下來迎他,在門廊的最後一級她站著等待,以一種無法表達的快樂,微笑著一個無比優雅而高貴的姿態,她是那麼美麗,他張開雙臂向前撲去,當他正要抓住她,他感覺到脖子後震耳欲聾,一道旋目的白光罩向他,象大炮的震撼,然後四周一切都黑暗而沉寂。
佩頓·法誇爾死了。他的身體,被扯斷的脖子,吊在貓頭鷹河橋下的木頭上,左右微微來回晃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