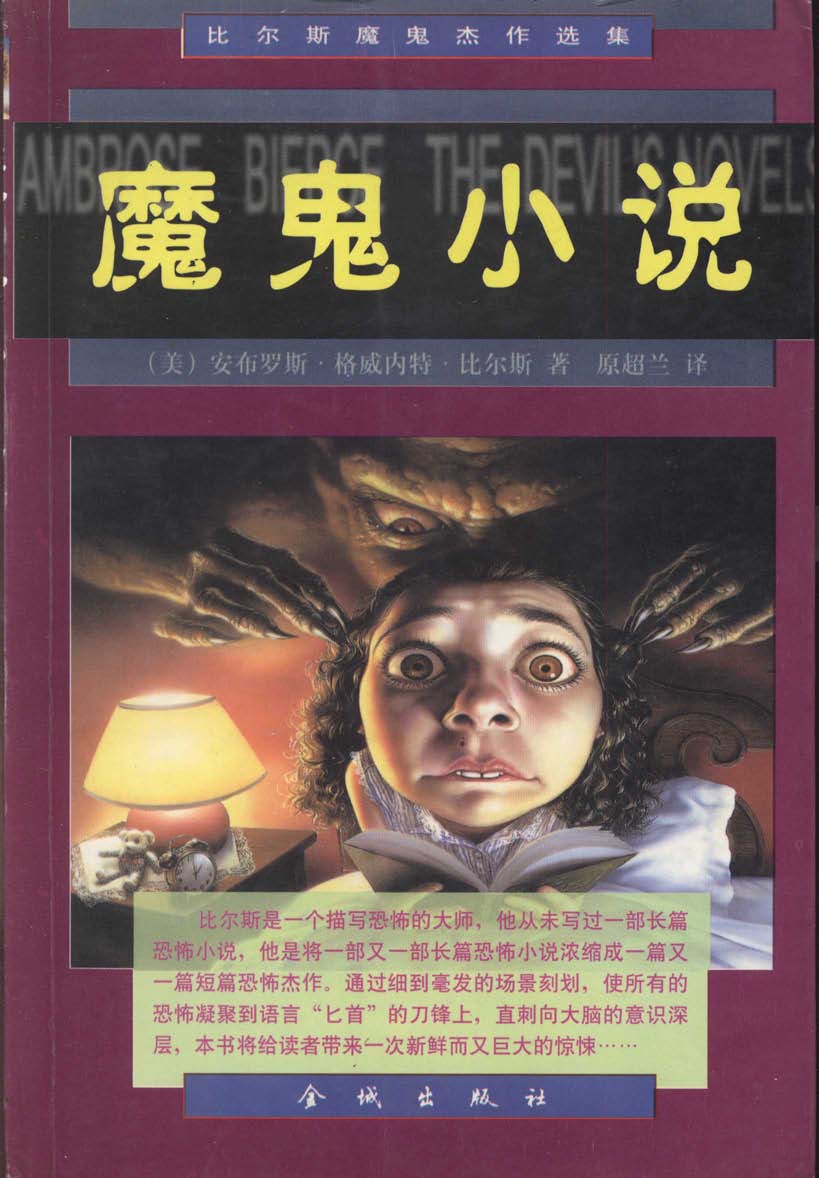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雪夜行劫的死屍
——一個沒有顛倒的故事
它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寒澈刺骨的夜晚,清亮有如鑽石的心。這清亮的夜有一個凶險的詭計。當你觀看時,當你忍受時,在黑暗裏你可以感受到寒冷,卻不知道它在哪裏。這夜機警得簡直可以侵襲人,就像一條大蛇。月亮神秘地沿著南邊山峰頂上的巨人樣的鬆林後麵移動著,凝結的雪驚人地閃著寒光,使得西邊顯得更為黑暗,映襯出海濱山嶺那鬼森森的輪廓,離它較遠的地方是隱匿的廣闊的太平洋。這雪不斷地堆積起來,從急流峽穀的底部升騰起來,起伏地蔓延在長長的山脊上,搖晃地衝向那些小小山群飛濺起浪花,這浪花就是陽光的反射:一次從月亮投射過來,一次從積雪反照過來。
在雪中有許多采礦工遺棄的小木屋被掩埋掉(一個水手可以說它們已經沉沒了),支撐著讓流水運送木材的高架水槽散漫地斷裂得隨處可見,它被稱之為“水滑道”,當然,“水滑道”就是“水路”,這種山峰上水道的優勢和特色也不能剝奪淘金者說拉丁語的特權。對死去的好友你可以說,“他已去了水滑道”,這並不是一句糟糕的話,它實際上意思是,“他的生命已經返回到生命的源頭去了”。
當雪披上它厚厚的盔甲抵擋風的侵襲,就用不著考慮它占有優勢的角落。雪糾纏地進攻著,而風則十足是一支不能抗衡的潰敗的軍隊,在開闊的田野上,雪分配著大規模兵力,使它在那獲得了一個根據地,雪在那裏站住了腳:那裏雪可以掩蓋風的一切所作所為。你可以看到在牆的缺口後麵蹲著整整一堆又一堆雪,在由山邊粗鑿而出的偏僻的老路,也積滿了雪。當風雪出其不意地停止消遣後,一隊接一隊的冰雪騎士為奪路而逃掙紮在這條路上。幾乎難以想像,更多的荒廢和陰鬱的地點竟然怎麼也比不上該死的急流峽穀。但海納姆·賓遜先生就選擇生活在這裏,他是唯一的居民。
從北方群山不斷地向上,可以看到他那鬆木屋腳的小木屋裏唯一的玻璃窗,射出一道薄薄的、長長的亮光,看起來有點像一隻黑甲蟲被一根閃亮而簇新的別針釘在山腰上。在小木屋裏麵住著賓遜先生,在喧鬧的火堆前,他凝視著火焰的心臟好像在他一生中以前從未看到過這樣的玩意。他不是一個漂亮的人,他是灰暗的人;他的服飾顯得襤褸而懶散;他的臉色蒼白、憔悴;他的眼睛卻太清亮了。關於他的年齡,如果有人嘗試猜測的話,會說他已四十七歲了,然後他會自己改口說,是七十四歲。他真實年齡是二十八歲。他是衰弱的,之所以這樣,也許是,他敢於挑戰,喜歡挑釁,因為貧困,他在本特利公寓當殯儀員,在索拉那當驗屍官。貧瘠而熱誠地在上層和下層之間飽受磨難。作為三明治的上層和下層之間的中間層無疑是危險的。
賓遜先生用他襤褸的肘拄在襤褸的膝上坐著,他瘦瘦的嘴巴隱蔽在瘦瘦的手掌裏,沒有顯露出上床睡覺的意圖,他看起來很蔑視任何修改這種意圖的想法。不過在最近的一小時內他打盹不下於三次了。
門上傳來了尖銳的篤篤的叩擊聲。在夜晚的這個時候,在這樣的天氣裏,一陣敲門聲足以令人震驚,在定居了二年的急流峽穀裏,這個人沒有看到一張人類的臉,不應該忘記在這地方是不可能再有別的人,但是賓遜先生沒有從煤火中抬起他的眼睛。甚至當門推開時,他隻是有點親密地對自己聳了聳肩,當一個人做他期待的一些事時,他並不情願被人看見。從小禮拜教堂的停屍間裏,靈樞在女人背後麵的走廊裏被推了出來——你可以在女人那裏看見這個姿勢。
但是當一個裹著羊毛毯大衣的個子高高的老人,他的頭包紮著手帕,幾乎他全部的臉裹在圍巾裏,從裏麵露出一雙綠熒熒的不停轉動的眼珠,而眼珠旁邊看得見的皮膚是亮晶晶的白色,他大步地幽幽地進入屋來,猛力地把戴著手套的手拍在賓遜先生的肩上,這新來者麵對如此忽視他的舉動,給了賓遜先生一個不小的驚訝:任何人他都可以給予這樣一個待遇,他明白任何人都不期待這樣的會麵。不過,這意外來客的方式引導了賓遜先生的下列程序:一種驚訝的感受,一種滿足的意味,一種內心極深處好意的情緒。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抓住自己肩膀上那隻皺紋雜亂交錯的手,熱情而很不負責地上下搖晃,因為這老人的外貌沒有任何引人入勝的地方,足以引起賓遜先生這樣的排斥,驅逐。畢竟,這普通財物的吸引力太一般了,好在厭惡的心情還沒有超過它。在這個世界最有魅力的東西是我們本能地用布蓋住的一張臉,當它變得平靜時有著更多的誘惑力——非常迷人——我們為它準備了七尺之地。①
“先生”,賓遜先生說,放下老人的手,很尖刻地把它放在他的腿的對麵,“這是一個很不爽利的夜晚。請坐下,我非常高興看到你。”
賓遜先生用一種讓絕望的人能很容易地重新產生希望的口氣說起來,這是就賓遜先生所有的為人處事而言。真的,對比他的動作和他的禮貌這足以讓人驚歎,不過這是我們社會裏最常見的情形中的一種。這老人先踏步走向火堆,他那綠色的眼珠既熱情而又幽暗。賓遜先生接著說:
“我是欽佩你的生命!”
賓遜先生的文雅不是太精致,不過通情達理的讓步衝淡了這種感覺。他停頓了片刻,讓他的眼睛從他的客人那包裹的頭部往下掃視,沿著扣住羊毛毯大衣的一排陳腐鈕扣往下,直到綠色的牛皮靴上,在它上麵沾滿粉末狀積雪,它們開始融化並沿著地板上的一條細流流動著,他用眼睛清點一下他的客人的東西,顯露出滿意的樣子。誰不願意擁有這些東西?然後,他繼續說道:
“歡呼我能給你一個建議,遺憾的是,要保持好我的環境。但是我會尊重我自己讚許的利益,如果它讓你也愉快的話,你也可以分享它,這比去住本特利公寓要好。”
賓遜先生說著,帶著一種善於謙遜待客的奇異的文雅腔調,倒好像是他寄居在這樣一個夜裏溫暖的小屋內,簡直可以和在雪中跋涉十四裏之後再把結成硬殼的雪塞進喉嚨的感覺相匹敵,這是一種不能忍受的刁難。作為答複,他的客人解開羊毛毯大衣。主人往火裏放進一些新的燃料,用狼尾巴清掃爐子,補充說道:
“但我想你匆匆離去更好。”
老人在火旁邊找到一個座位,伸出他寬大的腳板去烤熱,卻沒有動他的帽子。我們的習慣則是靴子不脫那麼帽子也很少脫下。賓遜先生沒有再說什麼,他坐在一把由木桶改成的椅子上,這把椅子具有非常古怪的特征,好像是專門為了保留它的屍骨,生怕它自己一高興就散架似的。一個瞬間的寂靜。然後,在鬆林某處傳來一隻狼的嚎叫,同時,這門的框子嘎嘎地響了起來。這二件事沒有什麼聯係,這狼在嫌惡風暴的來臨。風響起來了。在這二者之間看起來深藏著一種莫明其妙的超自然詭計,賓遜先生帶著恐怖的茫然感覺戰栗起來。一下子他清醒了,又向他的客人致詞。
“這裏有奇異的怪事,我將告訴你每一件事,然後,如果你決定去,我將希望在道路上最糟糕的地方伴隨你,直到巴爾迪·皮特遜射死本·海克的地方——我敢這樣說,你知道這地方。”
這老人斷然地點點頭,他這樣做不僅僅是親密的表示,但他確實這樣做了。
“兩年前,”賓遜先生開始說,“我和兩個同伴,占據了這屋子。但後來,我們衝進本特利公寓後留了下來,在那裏歇息住宿,而這十個小時裏急流峽穀沒有一個人。到了夜晚,我終於發現我遺失了一把值錢的槍,‘看它在那裏’,為了它我返回來,獨自穿過黑夜到達這裏,後來我每天夜晚這樣一人回來。我必須解釋在我們離開這裏幾天以前,我們的中國仆人運氣很壞地死了。當時地麵凍上了,以至我們怎麼努力也不能挖出一個墓穴,按慣例把他葬進去。因此,在我們匆忙離開的那一天,我們鋸開這裏的地板,給了他一個我們能夠辦到的葬禮。但是當把他放下去的時候,我心情極壞地割掉了他的辮子,把它釘牢在他的墳墓上方的橫梁上,現在你可以看到它就掛在那裏,或者,更好的是,當溫暖使得你有空閑了,你可以仔細觀看它。
我站立,我腐爛,中國人因為自然原因進入死亡,我這樣想,當然,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沒有什麼製服不了的誘惑讓我回來,或者借助恐怖的魔力蠱惑我回來,但僅僅因為我忘掉了一把槍。那使你明白,還是不明白,先生?”
訪問者莊重地點點頭。他對這個人隨意哼了幾個詞。賓遜先生繼續地說:
“對一個中國人的信仰來說,一個人希望快點上天堂,就像一個風箏,他不能沒有一條辮子升到天堂去。好,縮短這沉悶的故事——畢竟,我的任務是講述。——今天晚上,當我獨自坐在這裏並胡思亂想時,中國人為辮子回來了。
他得不到它。”
這時候賓遜先生又進入空白的寂靜。也許他是對這不尋常的憂愁的敘述感到疲乏,也許他在集中精力回憶。風暴這時奇妙地呐喊起來,鬆林沿著山腳怪誕地哼唱著。敘述者繼續說:“你說你看不到這一切,老實說,我身不由己。但他正在前來!”
又一個長長的寂靜,兩人都手足不動地靠向火爐。然後,賓遜先生打破寂靜,幾乎是氣勢洶洶地把眼睛盯住他的旁聽者那張鎮靜的臉:“把辮子還給他?先生,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任何人的勸告對我不會起什麼作用。你會原諒我,我堅信——這裏中國人會變得很少去勸導別人——但我已冒險把辮子釘牢,按一種想像擔負守衛辮子的艱巨重任。在你體諒的暗示裏這件事幾乎不可能發生。
你和我玩默多克遊戲嗎?”
沒有什麼比這更帶著強烈憤慨的抗議的語氣,突然殘暴地衝向他的客人的耳朵,它好像用一隻鋼製手套打向他客人的頭的一邊。它是一個聲明,也是一個挑戰,他弄錯了,他認為客人是一個懦夫——去玩默多克:這種表達是這樣一個意思,有時它是指一個中國人,就是說你和我為一個中國人玩嗎?這是對那些突然不願傾聽的人的耳朵時常吼叫的一種質問。
賓遜先生的語句打擊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在一個短暫的寂靜之後,風暴在煙囪裏轟響起來,好像屍體扔進棺材的聲音,他繼續說道:
“但當你說,這件事要讓我疲乏不堪,我感覺到這兩年的生活是弄錯了——它自己選擇的錯誤。對這墳墓,你看到多少!不,沒有一個人去挖它。地麵也凍上了。但你非常歡迎。你可以到本特利公寓傳言——但那不重要。它非常難以割斷,他們把絲編進這條辮子裏,呼呼!”
賓遜先生閉上眼睛說著,在屋裏走來走去。他最後一個詞是一個粗重的呼吸,在他打了一個長長的哈欠之後的一個瞬間,他睜開眼,單獨又說了一句話,然後進入深深的睡眠。他說的是什麼,是這樣一句話:
“他們正在揮臂猛擊我的遺骸!”
然後這個到來以後沒有說一句話的年老的陌生人,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從容地放下他的大衣,用和費爾斯通賴茲小姐一樣銳利嚇唬的目光看著,她是一個愛爾蘭少女,六英尺高,五十六磅重,她常常穿著一件腰部寬鬆式樣簡單的女裝,在舊金山的人們麵前招搖而過。他躡手躡腳地溜到一個靠牆的床邊,床上放著一把很容易拿到手的左輪手槍,這是鄉間的習慣。他從床上拿起左輪手槍,它就是賓遜先生提起的兩年前為了它而返回急流峽穀的那把槍。
過了一會兒,賓遜先生醒了,看見他的客人同樣睡著了。但在行動前,他要靠近這異教徒頭發編成的繩子,然後強有力地一勒,這樣可保證他的行動又快又穩當。兩張床——僅僅用那不很幹淨的大衣間隔——大衣麵對房間相對的兩邊,大衣下方正是那進入中國人墳墓的小小四方形蓋板。從蓋板上釘下去兩排釘頭,由釘頭來抵抗超自然的東西,賓遜先生並不蔑視使用工具進行防備。這時,他不由自主地又沉入了夢鄉。
爐火現在暗淡了,火焰憂鬱地燃燒,偶爾暴躁地閃動,射出幻覺的影子在牆麵——這些影子神秘地移動,一下分開,一下又合在一起,那個懸掛著的辮子的影子,仍然憂鬱地單獨呆在屋子另一頭接近屋頂的牆上,看起來象個驚歎號。外麵鬆樹的歌聲上升進入一種凱旋聖歌的威嚴境界。一陣短暫的寂靜,非常可怖。
在這個間隔之中,地板上的那個活動門開始升起。慢慢地,平穩地上升,另一邊,也在慢慢地、平穩地上升著的是在靠牆床鋪上的老人包裹的頭,這陌生的老人正看著這一切,這時隨著一聲使房子地基都搖晃起來的、撕裂的聲音,活動門使它完全翻轉過來,兩排不文雅的釘頭險惡地尖尖地向上指著。賓遜先生弄醒了,沒有坐起來,用手指緊緊捂住他的眼睛,他在戰栗,他的牙齒震顫作響。他的客人斜倚在他自己的一根肘子上,像燈一樣發出鮮豔光芒的眼珠瞪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突然啼哭號叫的風暴猝然撲下衝進煙囪,混亂的灰和煙充斥各個方麵,一刹那每個東西變得無比晦暗。當火光再次照亮房屋時,挨近爐邊的一個凳子邊極小心地坐著一個膚色黝黑的小人,他顯示著潔淨的魅力,服飾給人完美無缺的感覺,帶著迷人的微笑友好地向老人點點頭,“很明顯,從舊金山來的。”賓遜先生想,從他的恐怖中稍微有點回過神來,摸索著分析這深夜事變的來由。
但是又一個角色顯現了。從地板中間那個正方形黑洞裏伸出了死了的中國人的頭,從那瘦骨嶙峋的骷髏的兩個孔洞中,他那玻璃質般呆滯的眼珠向上翻著,用無法形容的渴慕的眼神死死地盯住在上方晃來晃去的發辮。賓遜先生呻吟了,又一次把他的手遮住他的臉。一陣淡淡的鴉片味彌漫在房間裏。這幽靈,覆蓋全身的衣服僅僅是藍色束腰短外衣,顯得華貴而又光滑柔軟,上麵長滿了灰暗黴菌,這是在墓穴裏縫製出來的,他慢慢地上移,好像由一個螺旋形的源泉推進。當它的膝蓋和地板在同一條水平線上,這時極快地向上一衝,就像火焰靜靜地跳躍,它用雙手抓住發辮,把自己的遺骸向上拉,用毛骨悚然的黃牙咬住辮子的末梢,神情暴怒地就這樣抓牢它,獰笑地、可怖地、起伏地、瘋狂地,從一邊蕩向另一邊,它努力從橫梁上解下它的所有物,但絕對沒有聲響,它像一具屍體被猛烈地抽打而不自然地痙攣著。對照著神靈般的敏捷,它寂靜中的所作所為的醜陋並未減輕多少!
賓遜先生蜷在他的床裏,膚色黝黑的小紳士並不阻撓自己的腿。隻是用腳尖焦急連續地輕敲,對著那貴重的金表看了又看。老人豎立起來,冷漠地拿出左輪手槍。
轟隆!
像軀體從絞架上砍下,中國人用他的牙齒咬住他的大辮子落下去,撲通地掉進黑洞下麵,活動門翻過來,吧嗒一聲關上了。從舊金山來的膚色黝黑的小紳士靈巧地從他棲身處躍上去,在他帽子的上方空氣中抓住某些東西,就象一個孩子抓住一隻蝴蝶,好像被他吸住似地上飄消失進煙囪。
從這打開的門外黑暗的某處,一個暗淡的遠遠的叫聲——一聲長長的啜泣嚎哭傳了進來。像一個孩子奇異地死在過錯裏,或者一個遊魂被魔鬼追趕。它應該是一隻狼。
在第二年的早春時節,一夥采金礦工去到新的挖掘地點而路過急流峽穀,偶然進入那荒廢的小木屋,發現了漢納姆·賓遜的屍體,攤在靠牆的床裏,一個彈洞穿過了心臟。子彈很明顯是從房間的另一邊發射過來的,因為在橡木橫梁上擊出了一道淺淺的藍色凹痕,凹痕打了個彎,彎曲向下直指它的受害者的胸膛,原來強有力地吊拉著橫梁的是馬尾毛編成的一條粗繩的尾端,不過現在那個尾端的繩結已被子彈打斷。其餘沒有什麼東西能引起觀察的興趣,除開一堆腐臭的、混雜的衣服,幾件用品後來被證人確認是幾年前被埋葬的某個死人穀的居民的物品。但是它不容易讓人明白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除非,真的!那羊毛毯外套是由死神自己穿著去假扮——這幾乎是難以置信的。
①即所謂為人準備墓地的意思——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