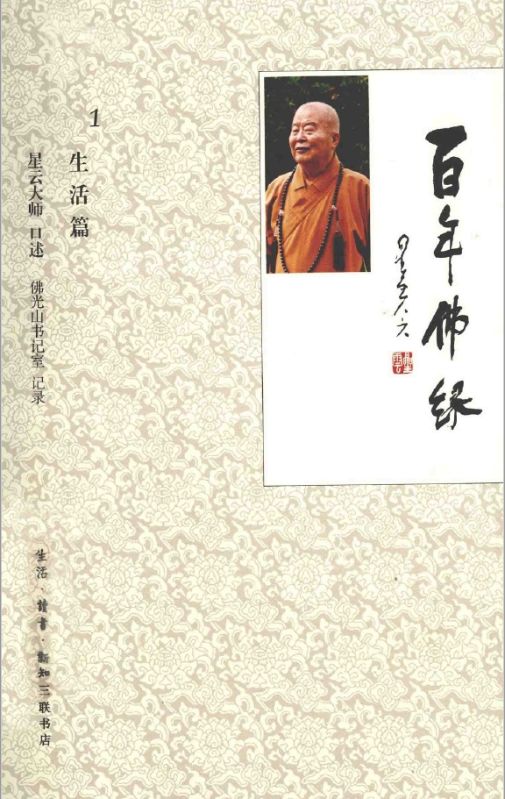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母親迎接我出生,我為母親送行
曆經民國締造,北伐統一,國共戰爭,吾母即為現代史;
走遍大陸河山,遊行美日,終歸淨土,慈親好似活地圖。
這是我在一九九六年,為母親寫下的一副挽聯。
我雖是個和尚,但也是個人子,想要盡孝的心與天下所有的兒女是一樣的。守在靈前,我深深地凝視著母親:皤皤的銀絲,整齊地襯托著她安詳的容顏,使我憶起小時候守在床邊,等待母親起床的情景。
這一次,我的母親,她終於放下了一生的苦難,一生的牽掛,一生的辛勞,和我們告別了,她完成教養兒孫的責任,她要永遠地休息了。
我的母親,剛毅裏有其為人設想的溫柔。就在她往生之前二十分鐘——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淩晨四時,在美國洛杉磯的惠提爾醫院中,她不放心地叮嚀陪伴在身邊的時任西來寺住持慈容法師:“謝謝你們為我念佛,我現在要走了,千萬不要讓二太爺知道,免得他掛心。”(“二太爺”是母親對我的昵稱。)
我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看著飛機窗口的白雲,母親,我來了,您要等等我。從台灣趕到母親的身邊,我看著閉著雙眼的母親,請求母親的諒解,請原諒孩兒的不孝,雖然您苦心吩咐不要讓我掛心,但我也知您的心:您是多麼渴望在一生的最後一刻,讓我握著您的手送您一程。
記得我曾和母親報告,在台北佛誕的法會上,有兩萬多人聽我講話。她露出驕傲的表情,高興地笑說:“兩萬人聽你講話,但是你得聽我一個人講話。”現在,我隻有用“心靈傳真”說給她聽了。
我遵照她的遺願,不讓人知道。四天後,六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我們把她送到西來寺附近的玫瑰崗公墓火葬。
在眾人誦經念佛聲中,我輕輕地按下了綠色的電鈕,一陣火、一陣風、一陣光,永遠地送別了母親。
當初,二十五歲的母親,懷胎十月生下了我的身體。現在,七十年後,不到一分鐘,母親歸於熊熊火光中。
母親好像一艘船,載著我,慢慢地駛向人間;而我卻像太空梭,載著母親,瞬間航向另一個時空世界。
母親,在風火光中,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的聖蓮,請您穩穩地坐好,不要掛念這個世界,不用擔心您的兒孫。跟隨著光明步向蓮邦佛國。
我心中默默地念著:
娑婆極樂,來去不變母子情;
人間天上,永遠都是好慈親。
從玫瑰崗回西來寺,突然覺得少掉了很多什麼,又增加了很多什麼。在心理上,雖然我早有預備,但仍免不了濃濃的懷念。生死是世人解不開的謎,佛陀當初領導著信仰他教法的弟子,要解開生死的秘密。很多徒眾、信徒關心我喪母的悲傷,但我感覺:生者何嘗生?死者又何嘗死?一世的生死不過是永久生命的某個段落而已。那一年,我記得心定法師捧著母親的靈骨,我抱著母親的遺像,回到佛光山,舉行了懷恩法會之後,那個夜晚,母親一生的語笑,慈愛的影像不斷回旋於腦海。為了紀念母親,我想要談談幾件母親的行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