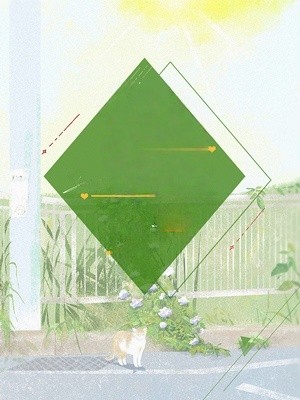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傅西洲,恭喜你,你快要自由了。”
雲思菀對著保險箱裏的離婚協議輕聲說道,指尖撫過紙張邊緣,唇角彎起一抹真心實意的笑。
玄關處傳來開鎖的輕響。
她迅速合上保險箱,轉身下樓,正看見傅西洲走進來。
他穿著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裝,眉眼清冷,正低頭摘下手套,隨後是慣常的流程——消毒液淨手,脫下外套,甚至鞋底也一絲不苟地清潔。
雲思菀沉默地看著,等他完成這一切,才走上前,熟練地接過他遞來的外套。衣領上沾著極淡的消毒水氣味,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女性香水味。
她垂著眼,走向洗衣房。
“下個月兩家要辦家宴,記得把時間空出來。”
傅西洲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冷淡得不帶情緒。
雲思菀打開洗衣機,將外套扔進去:“我去不了。”
“為什麼?”他走近幾步,聲音裏透出不耐,“你一個家庭主婦,還能有什麼事?”
她剛要開口,卻見他眼神驟然冷了下來,像是想到什麼,語氣譏誚:“是不是因為我最近總陪晚棠?簽協議時我就告訴過你,我這輩子隻愛她,我們隻是合約關係。”
雲思菀的指尖在洗衣機按鍵上停頓了一瞬。
五年前的那一天,也是這樣冷的天氣。
在雙方父母的安排下,她懷著隱秘的期待去見他,卻隻得到他遞來的一份協議。
他冷靜地分析兩家聯姻的利益,承諾會給她傅太太應有的名分和體麵,但也明確告知——他不會愛她。
她簽了字,筆尖劃破紙張,也劃破了她心裏那點可笑的幻想。
她答應聯姻,根本不是為了雲家。
那個家,從未給過她溫暖。
就因為她堅持畫畫、拒絕按他們的意願學醫,父親冷眼,母親責打,她像個異類。
那年冬天她發高燒,縮在閣樓裏無人理會,是傅西洲背她去的醫院。她燒得迷迷糊糊,隻記得他脊背的溫度,和耳邊有人不斷重複的名字——“傅西洲”。
病愈後,那個名字就在她心裏紮了根。
所以她滿懷期待去赴約,卻沒想到,他心中早有所屬。
但她還是簽了字,至少能逃離雲家。
原以為日久能生情。
這五年,她按他的口味準備一日三餐,學按摩放鬆他做手術的手,他夜班回來,她永遠亮著燈等。
漸漸地,他似乎也會在她生日時準備禮物,紀念日排場越辦越大,她生病時,他竟也會守在床邊。
她一度以為,這塊冰總算被她焐熱了一點。
直到一個月前,林晚棠回國。
傅西洲當晚就迫不及待去見她,徹夜未歸。
他甚至為陪林晚棠吃飯逛街,破天荒地請了假,連手術都推遲了。
看著林晚棠發來的照片——兩人共用一把勺子,他縱容她吃自己碗裏的食物——雲思菀終於明白,不是他有潔癖,隻是他的潔癖唯獨不對林晚棠生效。
他允準她的靠近,他的原則為她一再破例。
真正讓她心死的,是發現她們容貌有七分相似的那一刻。
原來他叫她“菀菀”時,心裏想的,一直是“晚晚”。
她不僅是商業聯姻的工具,還是感情上的替身。
好在五年的婚約即將到期。
她每一天都在倒計時。
“怎麼不說話?”
傅西洲的聲音打斷她的回憶。他看著她,眼神裏帶著慣常的不耐與審視。
雲思菀忽然有些疑惑:他是不是忘了協議到期的事?
以前是他反複提醒她看清關係,現在反倒不在意了。
她剛想開口,傅西洲的手機響了——是林晚棠的專屬鈴聲。
他幾乎是立刻接起,不知那邊說了什麼,他神色瞬間慌亂,抓起車鑰匙就衝出門。
“別怕,我馬上到。”
是他從未給過她的溫柔。
雲思菀怔在原地,想說的話哽在喉間。
原來他能緊張的,從來隻有與林晚棠有關的事。
白月光回國後,傅西洲永遠把她放在第一位,絲毫不在意她這個合約妻子的感受。
不過沒關係,她很快就能離開。
到時候她去追她的夢,他圓他的舊夢。
就當這五年,大夢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