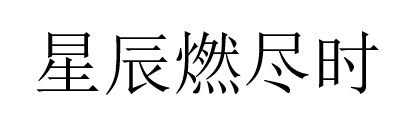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3章
枯井寒院,一鎖三日。
每日隻有一個年邁的婆子,從門下的小洞裏,遞進一些冷掉的飯菜。溫言手掌的傷口發了炎,又紅又腫,她卻仿佛不知疼痛,隻是每日抱著安安,給她講自己小時候在鄉下的故事。
講那裏的天有多藍,水有多清,講她在河裏摸魚,在山上摘野果的趣事。
「阿娘,那裏有花蝴蝶一樣的姨姨嗎?」安安似懂非懂地問。
溫言笑了笑,那笑容裏帶著一絲向往和釋然,她搖搖頭:「沒有,那裏隻有阿娘和安安,好不好?」
「好!」安安用力點頭,有阿娘的地方,去哪裏她都願意。
第四天清晨,厚重的門鎖終於被打開。
張嬤嬤帶著兩個丫鬟站在門口,陽光照不進她陰鷙的眼。
她居高臨下地看著衣衫單薄的母女,像在看兩隻討飯的野狗。
「溫夫人,將軍讓您準備一下,今晚宮中設宴,慶賀將軍大捷,所有家眷都要出席。」
她頓了頓,眼神裏的鄙夷幾乎要溢出來,「將軍特意吩咐,讓您穿得「體麵」些,別丟了將軍府的臉。」
溫言站起身,拍了拍衣裙上的塵土,麵無表情地說:「知道了。」
那日傍晚,是安安第一次看到阿娘為自己梳妝。
她沒有穿那些被送來又被原封不動放在角落的華麗綢緞,隻從自己小小的包袱裏,選了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素色棉布裙。
那裙子樣式簡單,卻被她熨燙得沒有一絲褶皺。
她將一頭及腰的青絲挽成一個簡單的婦人發髻,沒有插任何金釵珠翠,隻在發間,插了一根色澤溫潤的木簪。
那根簪子,是她最後的堅守。
是對那個曾經真心待她的少年傅望之的祭奠,也是對如今這個被權勢迷惑了心竅的鎮國大將軍無聲的抗議。
阿娘一直視若珍寶。
當溫言收拾妥當,從昏暗的房間裏走出來時,安安覺得,阿-娘比那個穿著綾羅綢緞的公主姨姨,好看一百倍。
她就像一株空穀幽蘭,於寂靜處,散發著遺世獨立的清冷與芬芳。
宮門口,傅望之和明月公主的馬車早已等候在那裏。
明月公主今日穿了一件火紅的織金宮裝,裙擺上繡著展翅欲飛的金鳳,頭上戴著全套的紅寶石頭麵,一走動便環佩叮當,將皇家的富貴與氣派彰顯到了極致。
她看到溫言的打扮,先是誇張地捂住了嘴,隨即轉向傅望之,一臉天真地驚呼:「將軍,姐姐這是......怎麼穿成這樣就來了?是不是府裏的下人怠慢了她,沒有把那些新料子送過去?」
傅望之的臉,瞬間黑如鍋底。
他壓抑著怒火,走到溫言麵前,低聲質問:「溫言,我不是讓張嬤嬤提醒你了嗎?你這是存心要讓我在同僚麵前難堪?」
他的聲音裏,帶著被忤逆的惱怒。他似乎已經忘了,當年他最愛的,就是她這身素淨。
他曾說,她穿什麼都好看,就像山間的清泉,幹淨透徹。
溫言淡淡地抬眸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平靜無波,像在看一個陌生人。
「我沒有別的衣服。」
「胡說!」傅望之怒道,「我讓人給你送去的那些上等貢緞呢!」
「我不喜歡。」溫言的回答幹脆利落,沒有一絲轉圜的餘地。
「你......」傅望之氣得胸膛起伏,最終狠狠一甩袖,大步走在了前麵。
明月公主得意地瞥了溫言一眼,嬌笑著挽上傅望之的胳膊,親昵地跟了上去,儼然一副將軍府女主人的姿態。
金碧輝煌的宮殿內,衣香鬢影,觥籌交錯。
傅望之無疑是今晚最耀眼的星,無數王公大臣前來向他敬酒,他意氣風發,談笑風生,身邊的明月公主也與有榮焉,應酬得體。
而溫言和安安,則被安排在了最角落的一張桌子,無人問津,仿佛是被遺忘的影子。
溫言看著主位上那個談笑風生的男人,恍惚間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個除夕夜。
他打了小勝仗回家,兩人隻有一壺濁酒,一碟花生米,卻對著窗外的煙火,說了整整一夜的話。那時的他,眼裏隻有她。
安安餓了,小聲對阿娘說:「阿娘,我想吃那個桂花糕。」
溫言點點頭,起身想去給她取一些。
可她剛站起來,一個尖細的女聲就響了起來:「喲,這不是我們大夏的戰神,鎮國大將軍的......原配夫人嗎?」
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貴婦人圍了過來,她們是依附於明月公主一派的,此刻正用審視貨品般的目光,毫不掩飾地打量著溫言。
「聽說溫夫人是鄉下出身,沒見過什麼世麵,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啊。」
「可不是嘛,你瞧她穿的,我們府裏燒火的婆子都比她體麵。」
「真不知將軍怎麼想的,這樣的女人,怎配得上我們大英雄?」
她們的聲音不大不小,卻足以讓周圍幾桌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竊笑聲和鄙夷的目光,像無數根細密的針,紮向溫言。
溫言的背依舊挺得筆直,臉上沒什麼表情,但她放在桌下的手,卻緊緊攥成了拳,指甲深陷入掌心的傷口。
正在這時,傅望之與明月公主攜手走了過來。
明月公主端著一杯猩紅的葡萄酒,笑意盈盈地走到溫言麵前,姿態放得極低:
「姐姐,今日是將軍榮光之日,妹妹敬你一杯。多謝你這些年,在鄉下將將軍照顧得這麼好,才有他的今日。」
她話說得客氣,手腕卻在遞出酒杯的瞬間,故作不穩地「一歪」——滿滿一杯殷紅的酒液,不偏不倚,全都潑在了溫言那身洗得發白的素色棉布裙上。
深色的汙漬迅速在淺色的布料上蔓延開來,像一朵醜陋而刺眼的花。
「哎呀!」明月公主誇張地驚呼,「姐姐,對不住,對不住,我真不是故意的!」
方才那幾個貴婦人立刻上前打圓場:「明月公主,您就是太心善了。有些人,給臉不要臉,您何必敬她這杯酒。」
明月公主嬌羞地看了傅望之一眼,然後故作為難地對那幾個貴婦人說:「幾位姐姐可別這麼說,溫姐姐......她隻是性子淳樸了些,不懂京中的規矩罷了。」
這番話,聽似解圍,實則坐實了溫言「鄉下人」、「沒見識」的名聲,將她釘在了恥辱柱上。
傅望之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
他沒有斥責那些出言不遜的貴婦,也沒有安慰假意自責的公主。
他的目光,像兩把淬了毒的利劍,死死地盯著溫言,仿佛她是什麼讓他蒙羞的汙點。
他一步一步走到溫言麵前,從牙縫裏擠出幾個字:「溫言,你滿意了?」
溫言緩緩抬起頭,迎上他燃燒著怒火的眸子,清澈的眼睛裏沒有一絲畏懼。
「我做什麼了?」她平靜地問。
「還不夠丟人現眼嗎!」傅望之壓低了聲音,怒氣卻像即將噴發的火山,「公主好心敬你酒,你為何不接?為何要擺出那副冷冰冰的樣子?非要鬧得如此難堪!立刻,馬上,給公主道歉!」
周圍的人都在竊竊私語,看好戲的眼神毫不遮掩。
安安看到,明月公主姨姨的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覺的、勝利的微笑。
溫言笑了。
那笑聲很輕,很輕,卻像一根針,狠狠紮進了安安的心裏。
「傅望之,」她說,第一次連名帶姓地叫他,「在你眼裏,我做什麼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帶我來,自取其辱呢?」
「你......」傅望之被她話語裏的決絕和疏離刺痛,氣急攻心,竟猛地揚起了手。
「啊!」周圍響起一片倒吸涼氣的聲音。
所有人都以為這一巴掌會結結實實地落下。
溫言沒有躲,她就那麼靜靜地站著,仰頭看著他,看著那隻曾經為她削木簪、為她遮風雨的手。
她的眼神裏,沒有恐懼,沒有哀求,沒有憤怒,隻有一片死寂的、廣袤無垠的荒原。
傅望之的手,在半空中生生停住了。
最終,他還是沒有打下去。但他說出的話,卻比一千個、一萬個巴掌還要傷人。
他緩緩放下手,轉身,對身邊的親兵下達了冰冷的命令:「把她給我送回去!即刻!我傅望之的夫人,不該是這副模樣。」
然後,他頓了頓,補上了那句讓溫言徹底心死的話。
他看著滿身狼狽的她,一字一句,清晰地說道:
「她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