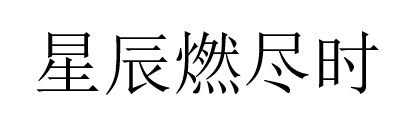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2章
大將軍府還是那座府邸,卻又不再是她們的家。
府中最大、最向陽的院落被命名為「聽月軒」,理所當然地成了明月公主的居所。
亭台樓閣,暖爐熏香,下人往來不絕,熱鬧非凡。
而溫言和安安,則被傅望之的一個親兵,麵無表情地「請」到了府中最偏僻的角落。
那是一座荒廢已久的小院,院中隻有一口枯井,和一棵在寒風中抖落所有葉片的枯槐,傅瑟得像一幅失了色的水墨畫。
「將軍說,公主殿下身子嬌貴,自幼在宮中長大,聞慣了禦賜熏香,對......鄉野的泥土氣有些過敏。」
親兵低著頭,公事公辦地傳達著命令。
泥土氣。
溫言牽著安安,看著女兒腳上那雙沾著些許泥星的舊鞋,那是她們從鄉下老家一路走來時穿的。
她沒有言語,隻是默默地走進那間散發著黴味的屋子。
夜裏,寒氣從四麵八方的縫隙裏鑽進來。溫言咳了幾聲,用帕子捂住嘴,看到上麵又見了紅。
她平靜地將帕子收起,借著昏暗的油燈,為安安縫補著一雙新鞋。
掌心的傷口還在隱作痛,但遠不及心口的萬分之一。每一次落針,都像是縫合著自己那顆千瘡百孔的心。
安安睡得不安穩,在夢裏小聲喊著「阿爹」。
溫言停下手中的活計,輕輕撫摸著女兒的臉頰,眼中的星光,黯淡得隻剩下一點微光。
很快,明月公主的人便來了。為首的是她宮裏帶來的張嬤嬤,一臉皮笑肉不笑,身後跟著幾個小丫鬟,捧著幾匹光彩奪目的錦緞和幾件花裏胡哨的衣裙。
「溫夫人,」張嬤嬤捏著嗓子,居高臨下地說,「公主殿下心善,見大小姐衣著簡樸,特意送來些新衣。將軍府的大小姐,總不能穿得如此寒酸,丟了將軍的臉麵。」
安安躲在溫言身後,探出個小腦袋,看著那些滑溜溜像蛇皮一樣的料子,搖了搖頭:「我不穿,我喜歡阿娘做的衣服,軟和。」
「大小姐,這可由不得你。」張嬤嬤的臉色沉了下來。
溫言將安安護得更緊,她抬起頭,迎上張嬤嬤鄙夷的目光,清冷堅定:
「我的女兒,穿什麼由我這個當娘的做主。公主殿下的心意我們領了,東西請帶回去吧。」
「你!」張嬤嬤沒想到這個看似柔弱的鄉下女人竟敢當麵駁了她的麵子,正要發作,一個冷硬的聲音從院外傳來。
「吵什麼?」
傅望之一身玄色常服,大步流星地走了進來。
他剛從兵部回來,眉宇間帶著一絲處理公務的疲憊和不耐。
明月公主立刻像一隻受了驚的小鳥,嫋嫋婷婷的跟他在身後,眼眶一紅,淚珠便滾了下來:
「將軍,你可算回來了。我......我隻是好心給安安送些新衣,想著姐姐初來京城,或許不熟悉這裏的規矩......可姐姐她,不但不領情,還說我多管閑事......」
傅望之的目光掃過那些華麗的衣料,又落在安安懷裏緊緊抱著的、一個針腳細密的布老虎上,眉頭皺得更深了。
「安安,過來。」他的聲音冷得像冰。
安安害怕地抓緊了溫言的衣服,把頭埋得更深了。
傅望之見她不動,耐心告罄,大步上前,一把將安安從溫言身後拽了出來。
力道之大,讓安安驚呼一聲,胳膊被抓得生疼。
「一個布老虎,臟兮兮的,像什麼樣子!」
他奪過安安視若珍寶的布老虎,看都沒看,隨手就扔在了滿是塵土的地上。
那隻布老虎,是溫言用自己做嫁衣剩下的最後一點紅布,一針一線為安安縫的。
隻因傅望之在某封家信中曾畫過一隻威風凜凜的大老虎,對安安說:「等阿爹回來,做你的大老虎,保護你和阿娘。」
老虎的眼睛,用的是她嫁妝裏僅有的兩顆黑玉珠子,在光下溫潤明亮。
「哇——」安安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掙脫開傅望之的手,就要去撿她的小老虎。
可一隻鑲著金線的精致繡花鞋,比她更快一步,狠狠地踩在了布老虎上。
是明月公主。她依偎在傅望之懷裏,柔柔弱弱地說:
「將軍,小孩子不懂事,您別跟她生氣。隻是......這等粗鄙之物,確實不該留在府裏,沾染了晦氣。我們將來還會有孩子,可不能被這些鄉野的東西影響了。」
「將來還會有孩子......」這句話像一根毒刺,紮得溫言渾身一顫。
傅望之聽了公主的話,竟點了點頭。他冰冷的目光射向溫言,語氣裏滿是責備:
「溫言,你就是這麼教女兒的?不知好歹,刁蠻任性!還不快給公主道歉!」
溫言的臉白得像一張紙。她死死地盯著地上被踩得扁平肮臟的布老虎,身體控製不住地發抖。
她沒有理會傅望之的怒吼,而是徑直走過去,彎下腰,想要撿起那個布老虎。
明月公主卻故意不挪開腳,甚至用鞋尖碾了碾,笑道:「姐姐這是做什麼?一個破爛玩意兒,回頭我賠安安十個、一百個就是了。」
「不必了。」溫言的聲音冷得能結冰,她猛地抬頭,直視著明月公主,「請你,把腳拿開。」
那眼神,像一匹被逼到絕境的母狼,充滿了原始的、決絕的野性。
明月公主被這眼神嚇得心頭一跳,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撞在傅望之懷裏,哭得愈發梨花帶雨。
傅望之徹底被激怒了。
「夠了!溫言!」他大吼一聲,那聲音如同在戰場上號令千軍,「你看看你現在像什麼樣子!潑婦!妒婦!簡直不可理喻!」
他被怒火衝昏了頭,想也不想地伸出手,一把將溫言推開。
那隻手,曾無數次在她崴了腳時,小心翼翼地將她背起;曾無數次在她受了涼時,為她搓熱冰冷的手腳。
而現在,這隻手卻帶著千鈞之力,狠狠地推向了她。
溫言本就體弱,被他這麼一推,沒能站穩,踉蹌著摔倒在地。手掌擦過粗糙的砂石地麵,瞬間蹭破了皮,鮮血淋漓。
「阿娘!」安安哭喊著跑過去扶她,「阿娘你沒事吧?」
溫言卻像是感覺不到疼,她隻是怔怔地看著傅望之,看著他那隻推開她的手。眼睛裏,最後那一點微光,也徹底熄滅了。
傅望之似乎也愣住了,他看著自己懸在半空的手,大概沒想過自己會動手。眼神裏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但稍縱即逝。
因為懷裏的公主已經開始抽泣:「將軍,我是不是做錯了?我是不是不該來......都怪我......」
他的心立刻又硬了起來。他心疼地摟住明月公主,再也沒看地上的母女一眼,冷硬地丟下一句:「溫言,你就在這院子裏好好反省!什麼時候想通了,什麼時候再出門!」
說罷,他擁著嚶嚶哭泣的公主,轉身離去,仿佛身後是他丟棄的一件無用舊物。
「哐當」一聲,院門被從外麵鎖上了。
安安哭著問:「阿娘,阿爹為什麼不理我們?他是不是不喜歡安安了?」
溫言將女兒緊緊抱在懷裏,伸手,撿起那個被踩得又臟又扁的布老虎,用自己的袖子,一點一點,固執地擦拭著上麵的汙泥。
她沒有哭。
隻是抱著女兒,一遍又一遍地輕輕拍著她的背。
很久很久,久到安安的哭聲都變成了抽噎,她才用一種近乎耳語的聲音說:「安安不怕,有阿娘在。他不配我們喜歡,是他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