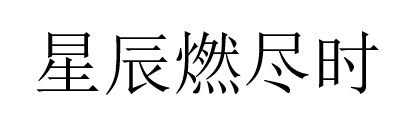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章
建安十六年,冬。
北風卷著碎雪,給巍峨的京城披上了一層素白。
鎮國大將軍府門前,車馬喧囂,全京城的目光都聚焦於此。
戰無不勝的鎮國大將軍傅望之,今日凱旋。
五歲的安安被乳母抱著,擠在人群的最前方,小臉凍得通紅,一雙黑葡萄似的眼睛卻閃閃發光,滿是孺慕與期盼。
她已經有整整一年沒有見過阿爹了。
「阿娘,阿爹是不是馬上就到了?」她扭頭,望向身側的女子。
溫言為她緊了緊頭上的虎頭帽,柔聲應道:「是,就快了。」
她的聲音溫潤如江南的春水,可眉宇間卻藏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倦意。為了迎接丈夫,她已連續幾夜不眠不休,親手為他縫製了新的寢衣,又將府中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條。
此刻,她穿著一身半舊的藕荷色棉裙,外罩一件素色披風,未施粉黛的臉上帶著一絲病態的蒼白。
那雙望向長街盡頭的眼眸,亮得驚人,仿佛盛著一整片星河,隻為等待她的月亮歸來。
終於,長街盡頭,馬蹄聲如雷,一麵繡著「傅」字的黑龍大旗破雪而來。
玄甲鐵騎簇擁下,為首那人身形挺拔如鬆,銀甲在雪光下熠熠生輝,正是傅望之。
「阿爹!」安安興奮地揮舞著小手。
傅望之聽見了,他勒住韁繩,翻身下馬。
那張曾無數次出現在她夢中的臉龐,如今被歲月與戰火雕刻得更加剛毅,也......更加陌生。
他不再是那個會在家信中畫著小人,抱怨軍糧難吃的少年郎了。
他的目光越過歡呼的人群,落在溫言身上。
那眼神裏沒有她徹夜期盼的久別重逢的溫情,反而帶著一絲審視與不易察明的煩躁,仿佛在審視一件不合時宜的舊物。
「阿言,」他開口,聲音沉穩卻疏離,「在門口像什麼樣子,進去吧。」
溫言心頭微微一沉。
她壓下心頭異樣,牽著安安的手,柔順地應了聲「好」。
可他們還沒來得及轉身,傅望之身後,一輛極盡奢華的鎏金馬車裏,下來一位身著火紅狐裘的嬌豔女子。她珠翠環繞,容色傾城,一下車便引來無數抽氣聲。
「明月公主?」人群中有人低呼。
女子嫋嫋婷婷地走到傅望之身邊,親昵地挽住他的手臂,一雙美目帶著嬌嗔,掃過溫言母女時,眼底飛快地掠過一絲輕蔑。
「將軍,這便是姐姐和安安吧?姐姐真是......樸素得緊呢。」
這聲「姐姐」叫得婉轉動人,卻像一根針,紮進溫言的心裏。
傅望之沒有抽開被挽住的手臂,反而將公主往身後護了護,皺眉看向溫言,語氣帶著不容置喙的命令:
「這是陛下親賜的平妻,明月公主。阿言,你如今的身份,配不上我鎮國大將軍正妻之位。公主屈尊為平妻,你......當好自為之。」
「轟」的一聲,溫言感覺整個世界的聲響都消失了。
她為他親手縫製寢衣而伸出的手僵在半空,袖中還藏著為他納的千層底布鞋,鞋底的針腳細密結實,因為她曾發誓,要讓他走的每一步路,都安穩踏實。
一根納鞋的針,不知何時滑出,狠狠紮進了她的掌心。
血珠瞬間沁出,染紅了細膩的皮肉,她卻感覺不到絲毫疼痛。
所有的感官,都凝固在了「平妻」這兩個字上。
她隻是怔怔地看著眼前的男人。那個出征前還抱著她,說「等我回來,再不讓你和安安吃苦」的男人。
那個她曾夜夜跪在星空下,用自己的健康與氣運祈求他平安順遂的男人。
原來,他回來了,帶著赫赫戰功,也帶著對她最殘忍的背叛。
安安不懂什麼叫平妻,但她能感覺到阿娘在發抖。
她仰頭,清晰地看見,阿娘眼中的光,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