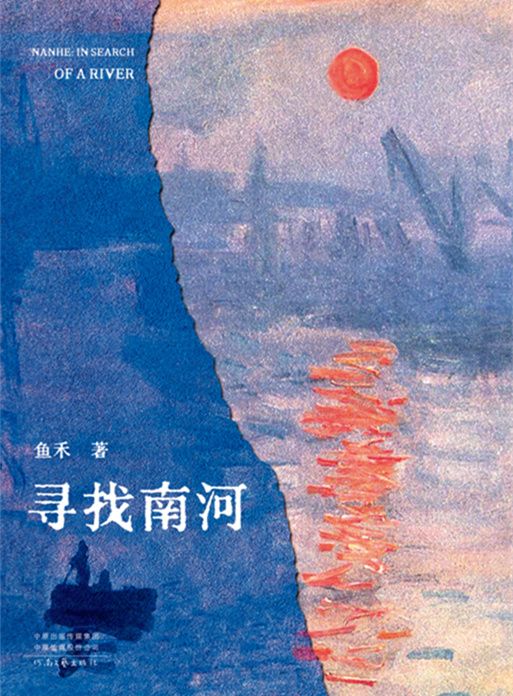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3
梁奚的最後一個電話,被我漫不經心地掛斷了。那個號碼打過來的鈴聲跟別的不一樣,我用的是一支不知道名字的黑管獨奏樂曲,我自己名之為《虛構》。《虛構》最後一次在我的手機上響起,那是什麼時候的事了,我已經記不分明。後來,我在一場酒後無意間觸碰到《虛構》的開關,我在那種讓人軟弱的樂聲裏再次撥打那個號碼,它已經變成了空號。
梁奚是那種挺能慪人的主兒,隻有危險臨頭才知道節製自己。但在太多的反複無常之後,我斷定這種節製隻是曇花一現。危險過去,他會立刻回到那種匪夷所思的狀態——忽東忽西,非黑即白,極端到令人發指,卻什麼也沒有堅持。類似毒癮發作的極端,我在一些人那裏不時見到。那種萬事不容商量的姿態,不是為了辯明什麼,也不是要衛護某種立場,隻是表明自己持有立場。隻要仔細打量,就會發現那種堅持是空心的,沒有實質,甚至沒有主題,那隻是對於爭執的嗜好。總覺得這是個不定哪天就會闖禍的家夥,卻從來沒想過這個人會去最高的雪峰冒險。
說出告別的時候,窗外的鳥鳴此起彼伏。氣溫還不夠高,但是春天畢竟來了,這些比我更靈敏的生物都按捺不住了。我想,是時候了,我將從一種程序錯亂的醞釀中,從逼真的虛構裏醒轉,恢複常態。鳥鳴聲讓我意識到我的心輕快至極。時間是輕的、跳躍的,正如那些從居所清除掉許多贅物的時刻,或那些動用強力殺毒軟件清洗電腦的時刻——那些果斷而極不厚道的時刻,我仿佛從“全班”認定的積習裏掙脫開來,化為某個姓氏不大好聽的小孩;從“人”的積習裏躲開,化為箭鏃般俯衝的遊隼;化為冬天沉眠、春天蘇醒的萬物中的一分子,從泥土裏拱出頭來。我在案上鋪開宣紙,抄那首《小雅·大東》: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時間過了很久,我覺得我已經把他忘掉了。可是冥冥中仿佛有一種未曾消滅的勢力負責阻止我的淡忘,仿佛故意為著要提醒我——有一天零點,手機的短信提示音響了。
夜半發來的短信隻有四個字:生日快樂。
但是,他用慣了五筆,竟然把“快”字打成了“怏”字。
我看著“生日怏樂”四個字,心中感到可笑,又有些不明所以的哀傷。這哀傷與愛無關,與發來短信的人也無關。我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齡。盡管我始終都不覺得我離開青春有多遠,但事實不容懷疑,我早已離開了青春,離開了那個任性、揮霍、無所顧忌的生命段落。現在,似乎隻有這個“怏”字是跟我匹配的——有點蔫巴,又有點不甘心,有點“慍怒”,又有點無所謂,多少曾經的無可無不可已經全然不可,我再也沒有興致在諸如此類的事情上費神了。
那個萬事敷衍的人啊,活得像個采集時代的原始人。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飲食偏生,衣著單薄。身材矯健,動作敏捷。極其好動,精力充沛。對動植物種類、地形、方位和道路、天氣變化等有精準的判斷力。能夠徒手逮住一條正在淺水裏遊動的魚。知道漫山遍野的野草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哪些能止血哪些能驅蟲。盯著人看的時候眼神直白專注毫不掩飾。溫存起來像海豚,發起脾氣來像怒獅。知識廣博,不求甚解。沉默,更喜歡用態勢語言交流。這些特征每逢走在路上的時候便可以大展身手。
我自幼四體不勤,對自己不具備的身體特征——發達的肌肉,高大的體格,強悍的體力,充沛的精力——有一種靈肉與共的迷戀。我在副駕駛位置上看著他,看他棱角分明的側臉上那塊誘人的咬肌,看他正在控製方向盤的胳膊和手,看那雙奔馬一般矯健的長腿,渾身奔騰的昏熱讓我不斷地提醒自己,似乎沒有理由不愛這個男人。盡管這種片刻之間達到巔峰的迷戀常常很快便會冷卻,我依然確信,這是我所經曆的理由最為充分的動情。他這樣的人似乎還沒有進化到精細的程度,不太可能有常人所謂的深情。我的迷戀也如植物的萌生、成長和衰亡,自然,美妙,平順,單調,有注定的期限。我確信我的冷漠隻是身體造成的,是體力不濟的人慣有的心灰意懶。對於這種無形無跡的生滅,我根本沒辦法掌握。
遇到鄭重的社交場合,梁奚常常會暴露潛在的虛弱。他對窸窸窣窣的禮儀不勝其煩。他強忍著不說話,正如因某個微不足道的差異而被孤立的小可憐兒祁連,他這樣的人,在人群裏也總是很快被作為異類辨認出來。他容易被人們正在進行中的談話激怒,這個線條堅硬的男人常常被怒氣弄得紅頭漲臉。本來他是好看的,但是在一屋子大腹便便的人裏,這個言行風格都透著“不一樣”的人總難免顯得滑稽。
真可憐,我忍不住這麼想,這不怪他,似乎更不能怪別人,但是,這真是可憐。我也忍不住警告自己,這根本不是你會愛上的人,你的情意隻是自我瞞哄,是對歡樂和虛榮的貪慕。
曇花明滅,倏忽來去。我選中那條短信,點擊“刪除”,然後清空回收站。
最後一條聯係他的線索就這麼斷了。這個號碼,雖然我很久都不撥打也不接聽了,但是它一直在某個角落待著,一直“在那兒”,就像一條溫順的老黑狗,什麼時候我招招手,它都會搖搖尾巴跑過來。但我不想這樣,似乎也毫無必要。直到幾個月以後,在一個醉酒的深夜,我被《虛構》的樂聲催眠,像許久之前一樣抓起手機要給他打個電話,才發現那個老黑狗一樣一直“在那兒”的號碼不在了,它早已被我毫不在意地刪除了。那時我才發覺,我竟然從來沒有記住過那個號碼,連它的尾號都沒有記住。
醉酒的人有著神經病一樣的執意。我忽然特別想找到它。我搜尋短信回收站,在數百條短信裏麵一條一條搜索。搜索無果。是的,我想起來我操作過清空。“生日怏樂”猶如散失在宇宙空間裏的飛船碎片,雖然我知道它存在,但是事到如今,我也明白,它永遠也不會在我眼前出現了。我曾經以為自己愛上了的那個人,還有那個一直“在那兒”的號碼——那條總是應聲而來的溫順的老黑狗,他們轉眼之間化為烏有,仿佛他們的出現隻是我的一場想象,是我十指翻飛在鍵盤上演繹的一場虛構。
或許這也是天命之中的一條。它慫恿了我對於身體的仰慕,也慫恿了我的厭倦與訣別。在醉酒的深夜,我想著那個仿佛丟失於外太空的人,想著他的俊美、強悍、憤怒和局促。在醉酒的深夜,在執意平複之後,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覺得我在“等待”。我從來沒有耐心等待過什麼,現在它來了,這種執意過後的平靜,不著急,也不鬆懈。凡命中應許的,都會在某個地方、某個時候出現,它們需要等待,需要漫長的耐心和沉默。我要等過許久才會知道,命運已經在我與他之間,用一座雪山布下了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