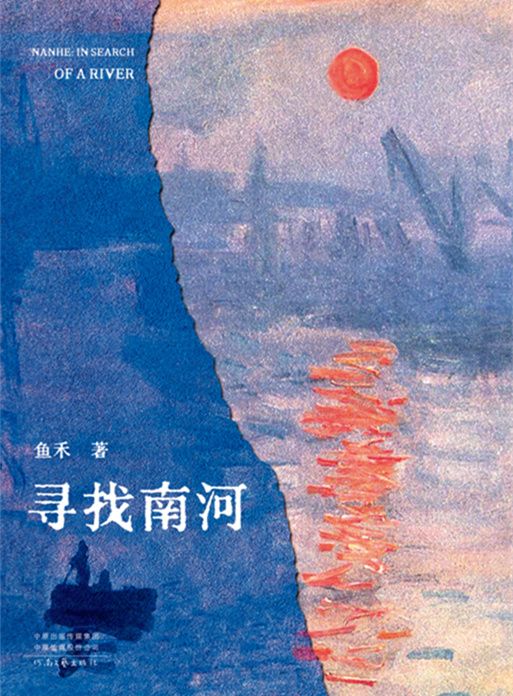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界限
1
1989年初夏,生物研究者在以色列沿海發現了一隻奇特的灰鯨。研究者追蹤灰鯨的來曆,發現它來自太平洋。
灰鯨這一程漫長遷徙的起點是北美大陸西南部的海域。它從那片溫暖的海域出發,向北穿過白令海峽,再折向東,經由加拿大與格陵蘭島之間的結冰海域(即著名的大西洋西北通道)遊到大西洋,又橫貫大西洋,穿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地中海,最後,它遊到地中海東岸,在那裏滯留下來,猶如一場指向新月沃地的朝聖。
在無邊無際的海洋裏,鯨魚群是靠聲音頻率保持聯係的。但這隻灰鯨的聲音有點特殊,它的同類聽不到。鯨魚的聲音頻率一般隻有15到25赫茲,它們的聽覺也大致隻能對這個範圍的聲音有反應。而這隻灰鯨的音頻高達52赫茲。它所發出的聲音信號,遠在它的同類能夠接收的音頻之外。正如浩蕩的地震波令許多動物驚恐逃竄,卻被人類全然“無知”一樣,灰鯨的聲音不幸處於被同類“無知”的範圍。沒有同類能夠接收到它的消息。相應地,它也隻能聽到自己這個音頻範圍內的聲音,而接收不到15到25赫茲的音頻信號。
52赫茲的音頻,成為一道阻隔在它與同類之間的無形的。它的世界裏隻有自己。
但這絕對的孤單,是否也隱藏了造物者的特殊意圖?固然,造物者的粗枝大葉、敷衍潦草無所不在,有些作品的製作簡直可謂用心殘忍。但這隻獨自完成了比人類最初的遠航更艱苦卓絕的旅程、獨自到達神聖傳說中的應許之地的灰鯨,顯然並不是造物者手下的殘品。
這更像是一次隔絕實驗。
這實驗會不會擴展到鯨類以外的物種,比如人類?
有確鑿的測驗數據表明,人被單獨關在一個房間裏十五分鐘,幾乎所有被測試者都會選擇隨便“做點什麼”,而不是待在那裏“不動”。“做點什麼”當然在大多時候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意義,能做的事甚至無可選擇。盡管如此,被單獨關在一個房間的人總會選擇“做點什麼”——哪怕所做的事情令人不悅,哪怕是自己厭惡的事,哪怕是破壞。
實驗者給出的解釋是,在直覺中,“不動”意味著一個人正在“獨自”思考(說胡思亂想也可以),而“做點什麼”則暗示著在自己與環境之間建立某種關聯,加入某種潛在的合作,比獨自思考更合群。參與實驗者不約而同地選擇“做點什麼”,再一次印證了人類作為生物的群居屬性。
這似乎表明,人類對於“獨自待著”有某種本能的不喜歡。
幾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簇擁團結的,隻有極少數例外。成群結隊,仿佛是生物借以保持種屬生存力的自然稟性。但是偶爾,因為造化的陰差陽錯,孤獨也會成為某些特殊生命個體的先天屬性。在人類的少數個體內部,是否也布設著一種52赫茲的先天性?那種對於獨處的迫切,也許並不是刻意要把自己與人群隔開,而隻是對於天賦的順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