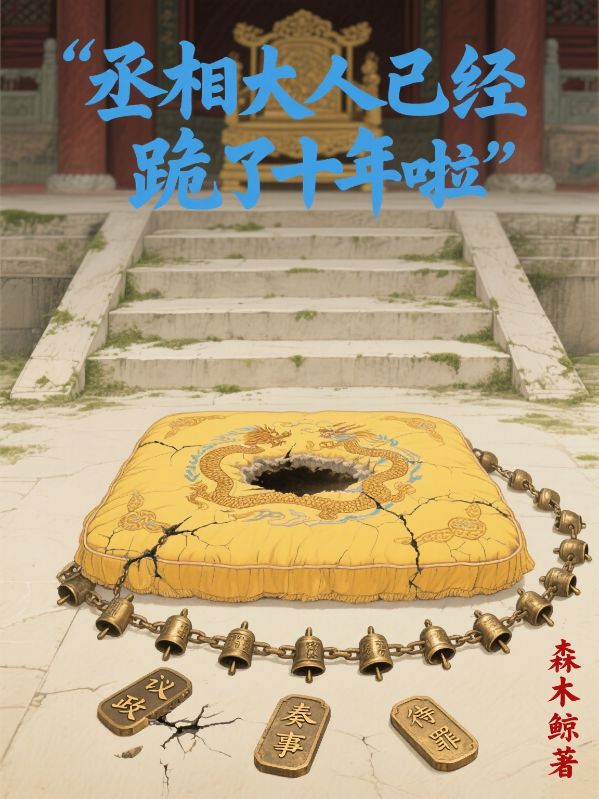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2章
銀針冰涼的觸感刺得我回神。
潞王的目光帶著期許。
我垂下眼,將銀針穩穩收好,聲音平靜。
“王爺抬愛。隻是此行倉促,師命隻囑為王爺診治,時限緊迫,恐難兼顧。”
“況且,京城名醫如雲,丞相大人自有良醫隨侍,不差我這鄉野醫女。”
潞王花白的胡子動了動,最終化作一聲歎息。
“罷了,強求不得。小神醫辛苦,先去歇息吧。”
潞王府的客房舒適,但我躺不住。
有雙亮晶晶、充滿期待的眼睛總在眼前晃。
“我就想看看他長什麼樣子!”
畫像,還得弄到一幅他的畫像。
接下來的兩日,除了給潞王治病,我就在京城各大畫坊間碰壁。
“丞相畫像”四個字,說出來就帶著忌諱。
畫師們要麼諱莫如深地搖頭,要麼漫天要價。
第三天,聽說城南“墨韻軒”辦文會,或許有畫技精湛的清貧畫家願意接這“私活”。
我換了身素淨衣裙,混了進去。
文會熱鬧,絲竹管弦,墨香浮動。
我尋了個角落,剛鼓起勇氣向一位畫師開口。
一個尖利刻薄的聲音,猛地響起。
“喲!瞧瞧這是打哪兒鑽出來的山野村婦?”
聲音帶著毫不掩飾的鄙夷。
說話的是個身著鵝黃錦緞、滿頭珠翠的年輕女子,被侍女簇擁著,下巴抬得老高。
眾人的目光聚焦我們。
我聽到有人小聲驚呼一聲,“安平縣主……”
原是癡戀丞相、出了名跋扈的安平縣主啊。
她搖著團扇。
“一個村姑,也敢肖想求丞相大人的畫像?也不照照鏡子!你算個什麼東西,配得上瞻仰丞相大人的天人之姿?”
“這墨韻軒,也是你這等下賤人能踏足的地方?”
四周的目光充滿了探究、鄙夷和看戲的興味。
我攥緊了袖中的手指,臉上極力維持著平靜。
“縣主誤會了。”我聲音不高,卻清晰,“民女奉師命進京行醫,求畫像隻為……”
“為攀高枝兒唄!”安平縣主尖聲打斷,團扇直指我的鼻子,滿臉鄙夷。
“少在這裝模作樣!一個下賤醫女,求當朝丞相的畫像,打的什麼齷齪主意,當本縣主看不出來?來人!給我把這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
她刻薄的話音未落,廳堂入口處,那扇雕花的楠木大門,被人猛地推開。
所有人都看了過去。
門口站著個人,玄色衣袍,沾著露水塵土。
是沈聿。
他的目光,帶著一種穿透十年時光的沉鬱和疲憊,越過滿堂驚愕的人群,直直地、死死地釘在了我的臉上。
我心頭一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