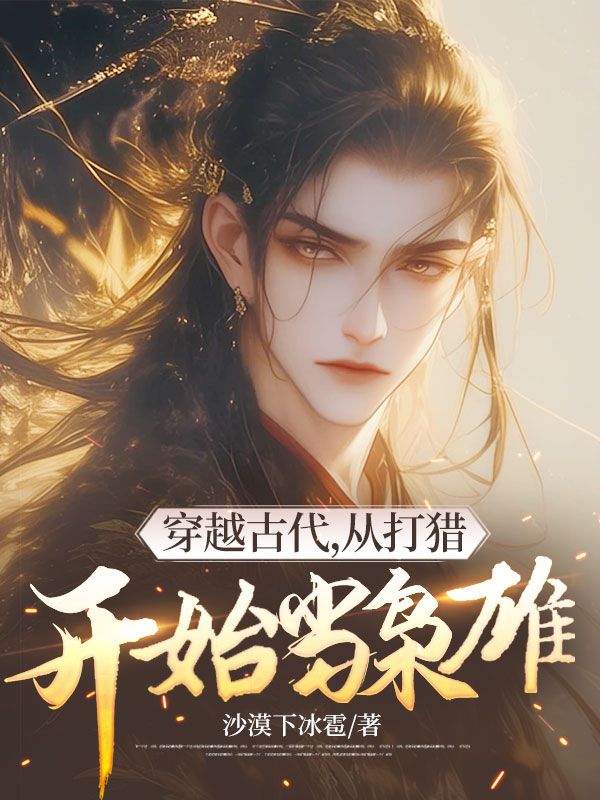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0章
這價錢,比張鴻預想的低了不少。
要是沒處理過的生皮,這個價還湊合,可這都是他費了功夫硝製的熟皮。
“掌櫃的,這可是三張囫圇個兒的成年狼皮,都是一箭斃命,身上沒多餘的窟窿。”張鴻語氣平靜,“而且,是硝製過的熟皮,您拿回去就能直接用,省了多少工夫?六兩銀子,太少了。”
“那小兄弟想賣多少?”掌櫃的眯了眯眼。
“一張,至少三錢銀子,三張,九錢。”張鴻報了個價。
“謔!”掌櫃的像是被噎了一下,“小兄弟,你這價錢,可比金貴的狐皮都高了!”
“不高。”張鴻搖頭,“這狼,是我親手打的,就在前幾天,一共四頭。打它們費了多大勁,掌櫃的應該清楚。這皮子,值這個價。”
他特意強調了“四頭”,又隱晦地點出是“親手打的”,話裏的意思,掌櫃的自然聽得懂。
這年輕人,看著不起眼,卻是個能從大黑山裏活著拖回四張狼皮的狠角色。
山羊胡掌櫃沉吟了一下,心裏快速盤算著。
這皮子確實好,轉手賣給那些需要做裘衣或者軍用的大戶,利潤不小。
而且,能一次拿出三張好皮子的人,說不定以後還有貨源。
“行,小兄弟也是個爽快人。”掌櫃的臉上終於露出點笑意,“這樣,八兩銀子,三張皮子我全要了!交個朋友,以後有好貨,還請優先送到我聚寶行來。”
八兩銀子,比張鴻的底價高了一點,也算公道。
“好。”張鴻點頭。
掌櫃的當場點了八塊碎銀子,足額。
銀子入手,沉甸甸的。
張鴻把錢貼身收好,心裏踏實了大半。
有了這筆錢,日子就能緩過來了。
他沒急著走,反而在聚寶行裏轉了轉。
用賣皮子的錢,他扯了足夠做兩身厚實冬衣的棉布,這次挑的是更耐磨的青色土布。
又買了十斤白麵,二十斤糙米,一大包鹽,還買了一把新的柴刀,一個鐵鍋,家裏的陶鍋早就裂了。
零零碎碎置辦下來,也花了不少。
剩下的錢,他仔細揣好,徑直朝著縣城西邊那片烏煙瘴氣的地方走去。
鴻運賭坊。
還是那個破爛門臉,門口還是那幾個無所事事的閑漢。
看到張鴻,他們的表情明顯不一樣了,帶著幾分忌憚。
張鴻掀開簾子走進去。
賭坊裏比上次更吵鬧,人也更多了些。
但他還是一眼就看到了角落裏的康麻子。
康麻子臉上的淤青還沒全消,正跟幾個潑皮吹牛。
看見張鴻進來,他猛地站起來,手下意識地摸向腰間。
周圍的賭客和打手也都看了過來,氣氛瞬間有點凝滯。
張鴻沒理會那些目光,走到康麻子麵前,從懷裏掏出最近攢下來的銀子放在桌上。
“這是剩下的七兩本金,外加這幾天的利錢,你點點。”
康麻子看著桌上的銀錢,又看看張鴻,臉上陰晴不定。
他沒想到這張鴻居然真能在這麼短時間湊齊這麼多錢。
“哼,算你小子識相!”康麻子色厲內荏地哼了一聲,伸手把錢扒拉過來,也沒細數。
“錢貨兩清,以前的賬,一筆勾銷。”張鴻看著他,一字一句道。
“但是,雲娘,”他話鋒一轉,冷了下來,“以後誰再敢去七河村找麻煩,或者打她的主意......”
他沒再說下去,隻是手按在了腰間那把匕首的柄上。
周圍的潑皮打手們看著他這副樣子,想起他上次徒手幹翻三個人的狠勁,都下意識地縮了縮脖子。
康麻子張了張嘴,想放幾句狠話,但最終還是沒敢說出口。
他知道,眼前這個張鴻,已經不是他能隨便拿捏的了。
“知道了知道了!”康麻子不耐煩地揮揮手,“錢還清了就行!以後井水不犯河水!”
“最好如此。”張鴻最後掃了他一眼,轉身就走。
出了賭坊,張鴻長長舒了口氣。
壓在心頭最大的那塊石頭,總算是搬開了。
雖然那個刀疤陳還是個隱患,但至少眼前的麻煩解決了。
他拉起裝滿物資的拖橇,腳步輕快地往城門走去。
天色還早,夕陽正好。
他得趕緊回家,雲娘還在等著他呢。
天擦黑,張鴻才拖著那簡易拖橇進了院子,上頭堆得冒尖。
灶房裏,昏黃的油燈光暈從門縫裏擠出來,隱約還有點吃食的香氣。
雲娘聽見院裏的拖拉聲,先是縮了下,隨即從門後小心探出個腦袋,見是張鴻,緊繃的小臉才鬆快了些。
“相公......”她幾步跑出來,伸手想搭把手拽那拖橇。
“死沉,不用你。”張鴻沒鬆手,自個兒把拖橇拉到屋簷底下。
他先解開那捆青布,抖落開,布料厚實,帶著股子新染料衝鼻子的味道,直接塞到雲娘懷裏。
“給你的,天冷了,扯了做身厚實的。”
雲娘的手指頭碰到那布,跟觸了電似的縮了回去,又忍不住,伸出指尖輕輕在布麵上劃拉。
這料子,她以前想都不敢想。
她低著頭,半天沒吭聲,隻是肩膀輕輕抖了一下。
張鴻又把那包紅糖、幹棗,還有新買的鐵鍋、柴刀拎下來。
“這些,收好。糖跟棗子,沒事泡水喝,瞧你那身子骨。”
他一股腦兒塞過去,又指指拖橇上鼓囊囊的糧袋,“糧食也搬進去,找地兒放嚴實了。”
雲娘抱著東西,幾乎要把臉埋進那堆布料裏,悶悶地“嗯”了一聲,轉身進了黑黢黢的屋子。
張鴻看著她抱著東西的背影,瘦伶伶的,像根隨時會折的草。
接下來的幾天,他沒再急著進山,開始拾掇這個破窩棚。
屋頂漏雨的地方,他弄了黃泥和著碎草,爬上去仔仔細細地糊了幾遍。
院門爛得快散架了,他用新柴刀砍了幾根粗木頭,橫豎加固,門閂也換了根結結實實的。
院牆矮得不像話,張鴻繞著院子轉悠,心裏有了計較。
他沒學村裏人那樣糊弄著壘土,而是找了堅韌的藤條和不少削尖的木樁,沿著牆根開始打樁,樁子斜著往土裏砸,交叉著用藤條死死綁住,弄得又密又高,尖頭朝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