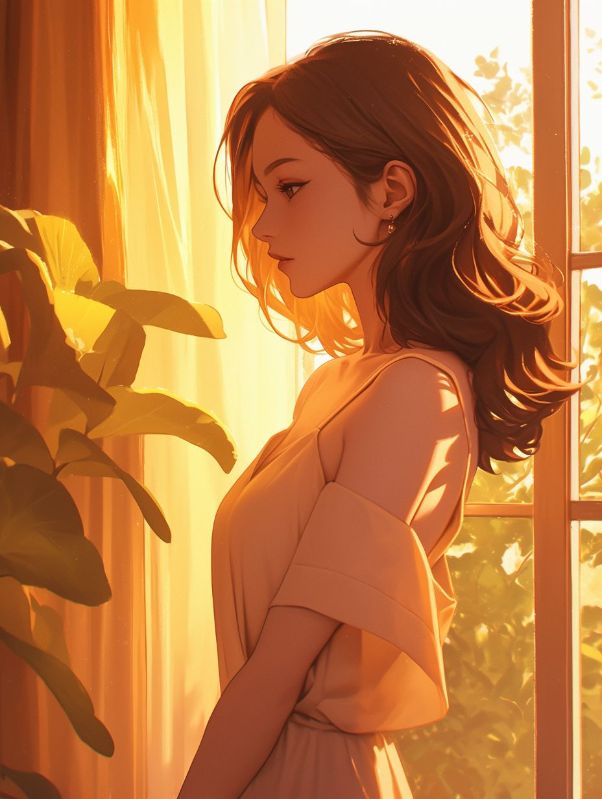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3
王珊珊徹底慌了,隻能死死抱著副主任的胳膊大哭。
她反複說著同一句話: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會這樣......我隻是想要她的東西......”
她那幾個死忠跟班還在不遠處大喊:
“不就是拿了一對破耳環嗎!她一個山裏來的窮鬼,能有什麼好東西!”
“肯定是她搞的鬼!主任,你們別被她騙了!”
我連一個眼神都懶得給,轉身回宿舍,重重關上了門。
當晚,學校以“涉及封建迷信活動,造成不良影響”為由,
暫停了我進出圖書館和實驗室的權限。
宿管也以“避免宿舍恐慌”為名,強製將我調換到一間滿是灰塵的廢棄雜物間暫住。
我在班級群裏,看到了輔導員發出的通知。
她嘴上說著“不要信謠傳謠”,但字裏行間,
卻都是對我這種“特殊家庭背景”學生的暗示性排擠。
王珊珊的團隊發動了第三波公關。
他們買通情感博主,長篇大論地分析我“因自卑而產生的報複心理”,把我塑造成一個陰暗扭曲的校園妖道。
輿論再次被點燃。
網絡上的熱搜話題變成了#女大學生現實版咒怨#。
我的照片被打上了恐怖濾鏡,在網上傳得到處都是。
評論區裏,無數人咒罵我“應該被燒死”。
甚至有人扒出了我老家的地址,揚言要去“淨化”我這個“不祥之人”。
學校的舉報電話,徹底被打爆了。
我看到學生處副主任在工作群裏的表態截圖:
“必須嚴肅處理,給王珊珊同學和全校師生一個交代。”
眾多老師紛紛附和。
我的處境,岌岌可危。
在被徹底隔離,手機即將被沒收前,我撥通了最後一個電話。
電話那頭,是我那位身為國內最頂尖民俗學專家的導師。
我隻說了一句:
“林教授,黃家世代鎮壓的怨靈,被人激怒了。”
半小時後,來的不是警察。
而是一輛掛著特殊牌照的黑色紅旗轎車,悄無聲息地停在了行政樓下。
我透過窗子,看到車上下來幾位氣質沉穩、不怒自威的中年人,徑直走向了校長辦公室。
他們沒有找我,而是直接找到了那位上躥下跳的學生處副主任。
為首的一人做了自我介紹,說自己來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副主任一愣,還想開口投訴我搞封建迷信。
對方卻直接從公文包裏抽出一份蓋章文件,拍在了他桌上。
“我們接到舉報,說你正在阻撓我們對‘特殊民俗文化傳承人’的保護性觀察項目。”
為首那人盯著他,一字一頓地質問:
“請你解釋一下,為什麼?”
副主任當場腿軟。
躲在人群後麵,正準備看我好戲的王珊珊,
在看到那份文件上鮮紅的印章時,臉色瞬間慘白如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