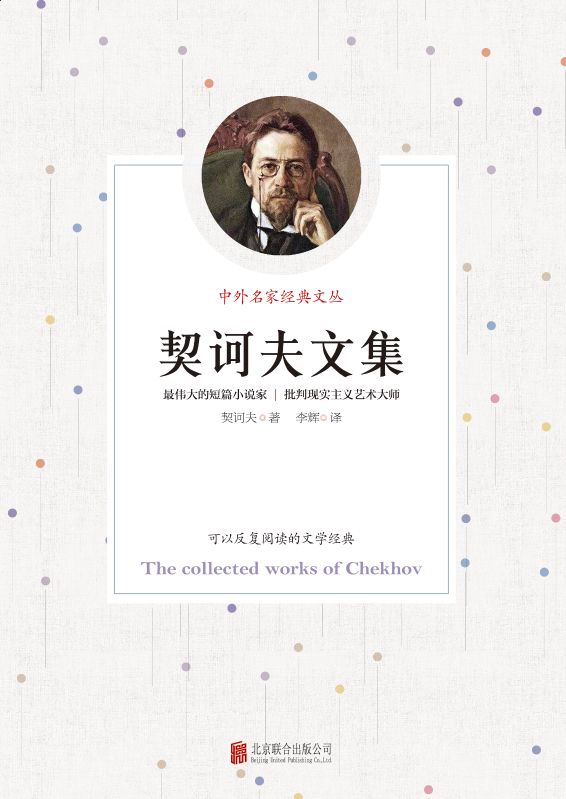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小人物
“我那尊貴的先生,父親,恩人!”文官涅維拉濟莫夫正在起草一封複活節的賀信,“希望您在健康和平安中度過這個神聖的日子以及此後的許多歲月,希望您闔家安康……”
燈裏的煤油快燒幹了,冒著黑煙,發出一股焦臭的氣味。桌子上,就在涅維拉濟莫夫寫字的那隻手旁邊,有一隻迷途的蟑螂正在驚慌失措地奔跑。跟這值班室相隔兩個房間,看門人巴拉蒙已經是在第三遍擦他那雙節日才穿的皮靴。擦得那麼起勁,所有的房間裏都能聽到他吐唾沫的聲音和上過鞋油的刷子聲。
“此外,對於那個混蛋我應該寫些什麼呢?”涅維拉濟莫夫思索著,抬起眼睛瞧著熏黑的天花板。
他看到在天花板上一個發黑的圓圈:燈罩的影子。下麵是落滿灰塵的牆簷,再下麵是牆壁——以前是刷成深褐色的。他覺得這間值班室像沙漠一樣荒涼,他禁不住可憐起自己來,同時也可憐起那隻蟑螂了……
“我下了班就可以離開這裏,可這蟑螂卻要一生一世守在這兒,”他伸著懶腰想道,“真是苦悶啊!要不我也把我的皮靴擦一擦?”
涅維拉濟莫夫又伸了一個懶腰,這才懶洋洋地朝看門人房子走去。巴拉蒙已經停止擦皮靴了……他一手拿著鞋刷子,一手在胸前畫著十字,站在通風小窗前仔細聽著……
“敲鐘了,先生!”他小聲對涅維拉濟莫夫說,睜大他那雙呆滯的眼睛望著他,“已經敲鐘了。”
涅維拉濟莫夫把耳朵湊到通風窗前麵去聽。複活節的鐘聲隨同春天的氣息,一齊從窗口飄進室內。各處的教堂鐘聲齊鳴,大街上馬車轆轆作響,在這亂糟糟的一片響聲中,隻有最近的教堂那活躍而高昂的鐘聲清晰可聞,不知誰還發出了一陣又響又尖的笑聲。
“人真多啊!”涅維拉濟莫夫望了望下麵的街道,歎口氣說。在那些亮著的街燈下麵時不時閃過一個個人影。“大家都跑去做晨禱了……我們東正教的複活節一般在俄曆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五日之間。恐怕人們現在喝足了酒,正在城裏閑逛哩。有多少歡聲笑語!隻有我一個人倒楣,在這種日子還得坐在這裏。而且我每年都是這樣!”
“那是因為您拿了人家的錢呢?要知道今天本不該是您值班的日子,是紮斯杜波夫雇您當替身的。別人玩得高興,您卻在這裏替人值班……您這是貪財啊!”
“見鬼,這怎麼能叫貪財呢?根本沒有什麼財可貪喲。錢一共隻有兩個盧布,外加一條領帶……這是窮,而不是貪財!可是現在,你知道,要是能跟大夥兒一道去做禮拜,然後去開齋,那該多好啊……喝點兒酒,吃點冷葷菜,然後躺下睡他一覺……或者你在桌旁一坐,桌上擺著受過聖禮的庫利契,茶炊在‘噝噝’作響,身邊還有那麼一個迷人的小妖精……你喝上一小杯,再摸摸她的下巴,那東西還真能撩人心魄……這時你會感到自己是個人……唉……我這一輩子算是白活了!你瞧,有個騙子坐著四輪馬車過去了,可你卻隻能待在這裏,惟一可做的事就是想想心事。”
“人各有天命,伊凡·達尼雷奇。上帝保佑,您日後也會升官晉級,坐上四輪馬車的。”
“我?嘿,得了吧,夥計,你別開玩笑。哪怕是拚了命的幹,我這九品文官也上不去了……我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我們的將軍也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可是……”
“嘿,將軍啊,他在還沒有做將軍之前,就偷盜了十萬公款。他那副派頭,夥計,我可比不上……看我這副模樣也不會有什麼出息了!連姓也招人惡心:涅維拉濟莫夫!一句話,夥計,我的這種處境是沒什麼指望的。你願意,就活下去;你不願意——幹脆上吊……”
涅維拉濟莫夫從通風小窗邊走開,懶散地在各個房間裏轉來轉去。鐘聲就越來越響……用不著站在窗口就能聽清楚了。可是,鐘聲越是清晰,馬車聲越是熱鬧,這深褐色的四壁和煙熏的牆簷就越發顯得陰暗,煤油燈的黑煙顯得越濃。
“要不要丟下值班的差事,一走了之?”涅維拉濟莫夫這樣想道。
不過,這種不負責任的一走了之結局是很糟的……即便離開了公署,在城裏逛蕩一陣,涅維拉濟莫夫還是得回到自己的住所,他那個住所比值班室更陰暗、更糟糕……就算複活節這一天他過得很好,很舒服,可是往後又怎麼樣呢?依舊是陰暗的四壁,依舊是要替人值班,依舊是寫這種賀信……
最後涅維拉濟莫夫在值班室中央站著一動不動,沉思著。
美好的新生活是他內心一直非常渴望的,這種渴望弄得他滿心痛苦,痛得他受不了。他熱切地盼望著自己能突然出現在大街上,卷進活躍中的人群,參加節日的慶典——為此鐘聲齊鳴,馬車轟響。他渴望著小時候所熟悉的種種現象:全家團聚,親人們喜氣洋洋的臉,白色桌布,室內亮堂而溫暖……他想起了剛才一位貴婦人乘坐的四輪馬車,想起了庶務官穿在身上的十分漂亮的大衣,想起了秘書佩在胸前的金表鏈……他想起了溫暖的床鋪,斯坦尼斯拉夫勳章,新靴子,袖子沒有窟窿的文官製服……要知道他之所以想起這些,是因為所有這些東西他一樣也沒有……
“難道隻有去偷?”他又想道,“其實偷東西並不難,可是要藏好可就不容易了……據說,很多人帶著贓物都逃往美洲,不過鬼才知道這個美洲在什麼地方!看來要想能偷會盜,還得受教育才成啊。”
這時鐘聲停了。此刻惟一能聽到的隻有遠處的馬車聲和巴拉蒙的咳嗽聲了。可是涅維拉濟莫夫的滿腔愁緒和憤恨,卻變得越來越強烈,簡直受不住了。值日室裏的掛鐘敲過十二點半。
“也許寫封告密信也不錯?普羅什金很快高升就是因為幹過這種事,很快就高升了……”
坐在自己的書桌前,涅維拉濟莫夫沉思著。燈裏的煤油已經燒幹,正冒著濃煙,眼看就要滅了。迷途的那隻蟑螂還在桌上爬來爬去,找不著窩……
“告密倒也確實行,可是這告密信到底該怎麼寫呢?要寫得摸棱兩可,還得耍點花招,像普羅什金那樣……我哪能辦得到!這種東西一旦寫了,日後準把我牽連進去,我這個笨蛋隻會見鬼去!”
涅維拉濟莫夫左思右想,一邊琢磨著擺脫困境的種種辦法,一邊呆呆地看著他起草的那封賀信。這信是寫給一個他十分憎恨又很懼怕的人的,近十年來,他一直在向這個人請求把他從十六盧布的職位提到十八盧布的職位上……
“啊……看你住哪兒跑,鬼東西!”他惡恨恨的一巴掌拍在那隻不幸被他看到的蟑螂身上,“可惡的東西!”
蟑螂仰麵朝天,絕望地蹬著細腿……涅維拉濟莫夫捏住它的一條腿,把它丟在燈罩裏,燈罩裏突然燃燒起來,發出劈劈啪啪的響聲……
涅維拉濟莫夫這才覺得好過了一點。
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