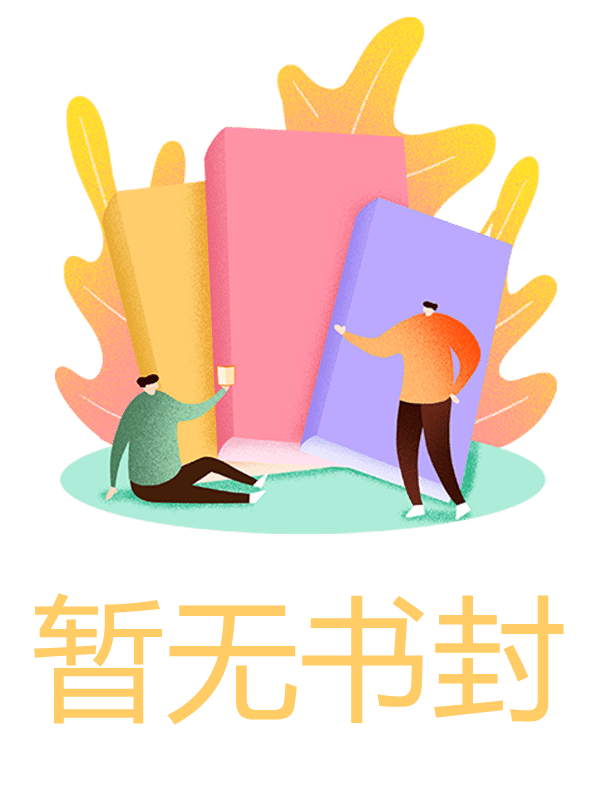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章
法官妻子在病房抱著白月光喜極而泣的時候,隔壁病房裏,我已經變成了一具屍體。
她不知道這一切是用我命換來的,反而發來短信:
“算你運氣好,阿銘要是出事了,我就和你離婚。”
“現在過來和阿銘道個歉,隻要態度好,我可以考慮收回離婚協議書。”
我沒有回信。
反而是負責我急救的醫生,給她打去通知電話:
“請問是陳晨的妻子嗎?您的丈夫搶救無效去世了。”
妻子冷笑回應:
“他就這麼見不得阿銘好嗎?他都病愈了,還要演這種無聊的手段?”
“讓他三分鐘內滾過來和阿銘道歉,不然我再也不可能撤回離婚申請書!”
她不必撤回了。
她為救尿毒症的白月光,擅自將我一顆腎臟判給他白月光後。
我再沒有回複她消息的可能了。
當宋溪然陪在何洛銘病房外的時候,我正躺在冰冷的手術台上,絕望的等死。
管子插滿我的全身,儀器的聲音像是死神奪命一般,提醒著我該走了。
直到我的心電圖變成了一條直線,何洛銘那邊卻傳來了手術成功的消息,手術室的緊急燈暗掉,我的眼睛也永久的閉上了。
大概是我生前怨氣很重,靈魂竟然來到了宋溪然的身邊。
看著宋溪然抱著死裏逃生的何洛銘,激動到眼眶發紅,我的心也跌入了穀底。
我想問問宋溪然,我們兩個同時被推入手術室的時候,她是否有那麼一瞬間擔憂我的生死呢?
答案是否定的,畢竟宋溪然為了何洛銘的病,將我告上了法庭,宋溪然找了業內最著名的律師,在她的宣判下,我到底還是敗了。
摘除我腎臟的時候,我在手術室裏疼得汗水浸濕了後背,我給她打電話,語氣帶著乞求。
“老婆,我錯了好不好,不要摘我的腎臟,我真的好疼,我要死了。”
從未在宋溪然麵前服過軟的我,以為隻要我認輸,將所有莫須有的罪名都攬下,宋溪然是否會看在五年的感情裏饒我一命?
可宋溪然在電話裏冷笑。
“認錯是你該做的事,能救洛銘一命是你的造化,你別想著蒙混過關,別以為你把腎臟給了洛銘就不用道歉了,這麼多年裏,你傷害洛銘做得一樁樁一件件,等洛銘好了我再跟你算賬。
“你想死是嗎?那也得跟洛銘道完歉再死!”
我試圖張張開裂的嘴,想否認那些子虛有的事不是我做的,可實在沒有力氣了。
宋溪然像是沒解氣,惡狠狠對我說道。
“你這個樣子真讓我惡心!”
隨著電話被掛斷,我的心沉到了穀底,連帶著對宋溪然五年的喜歡,也隨之煙消雲散。
宋溪然說我惡心,可當初她嫁給我的時候,深情款款的對我說,她會愛我
一輩子,我是她的首選,是她的例外和偏愛。
隻是有了何洛銘,便忘了我這個丈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