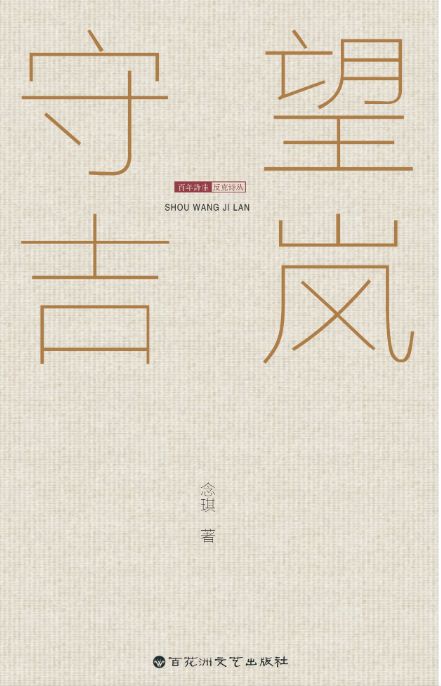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一個詩人的精神返鄉之旅
——念琪詩集《守望吉嵐》閱讀印象
譚五昌
一個仍然活在世間的真正意義上的詩人,他必然是懷鄉病患者。這個詩人在大地上行走,苦苦尋找自己的歸宿:一方麵是其肉身安居之處,另一方麵是其精神棲息之所。二者合一,則為靈魂意義上的故鄉。一個詩人若要重返故鄉,須對擺放在自己麵前的物質世界予以疏離。否則,人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重返故鄉。在一個眾人汲汲於追名逐利、貪娛求樂泛濫的世界上,城市欲望和物質膨脹將人引離故土,人們的生活被形形色色的市場原則所主宰,詩心漂泊到自由、激情和想象力之外的邊緣土壤上。然而,人類的精神之燈卻從未熄滅,在那古老恒久的美的中心,有詩人個體活生生的性情與呼吸。詩人念琪用濃鬱而充沛的南方氣息,以抒情達成對流逝時間的抵抗,以抵抗完成自我人生的詩性回歸。通過閱讀念琪的詩集《守望吉嵐》,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詩人是如何在傳統書寫與抒情姿態的結合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詩人對南方鄉土的追戀,同時也見證了詩人精神返鄉的動人旅程。
麵對人生蒼茫,念琪寧靜如初,然而月光和熱愛構成美好的回憶。“月光中鼓浪嶼飄出鋼琴的味道/鄭成功披星戴月護劍守望”(《有關廈門的一場熱愛》)。月光映襯詩人心,皎潔照耀每一個荒涼之夜,詩人已經通體透明。此刻抒情依序展開,以古典傳統的浪漫意緒觸及生命中不可預期的風暴,而這風暴象征曾經的摸爬滾打和對生活的不屈不撓,詩人亦會暫時或局部被不可預知被卷入深深的海底。“南洋紅磚刻畫一張張如花一樣地盛開”,詩人似“魚兒在這裏奮力遊弋/尋找出海的方向”。故此寧靜,如江心之石默守千年。詩人將我們帶入一個隱秘世界,不拒絕浪從哪裏來,隻要水,水。水是構成詩人生命哲學的重要實體,水聲、水光、水色均印上了詩人固有的生命底色:“你盡可以放心,頭枕著波濤/沉睡在鮮花盛開的日月穀”,此時詩人生命的神妙幻想使人回歸自然,成為自然之子。麵朝自然,心懷廈門之戀,詩人在隱喻中抒情彰顯出鄉思的強度。
詩人對故鄉的眷戀情感極為深沉,類似於河流對於大地的情感, 他的目光在故鄉的土地上到處流轉,其視線返回到事物本質的內裏,語言所到之處,皆是實體顯露原形。在《吉嵐山歌》中,詩人雙手合十,“用一首詩的熱情,結廬/在寒冷的北風中放養油菜花”,其實就是“在風上寫詩”。詩人這樣坦白:“我總懷疑有一群人埋伏在羊欄後麵/伺機報複春天。阻止時間繼續向前/靜心諦聽鐘表的嘀噠嘀噠蛩音/我把它當成禾苗的拔節痛哭”。其鄉村情感令人無限動容。在《故鄉的田疇》中,詩人暢言“最是牽引我目光的是莊稼/種出來的圖畫/瞭望,可以治療許多病/層次分明/自然在人們手中無須整容/引吭高歌”。禾苗、莊稼等意象疊加,使詩人變成“一個姓名寫在田上的人” ,這便是念琪的精神皈依方式。詩人將“在田上”意象實在化又虛擬化,也因此而更加物性化和想象化。這是有關詩歌的隱秘詞語在洞穿自然之境。詩人的目光進入事物的本體,也是返回事物的過程,糅合其形狀、色彩和運動,故而外部世界和詩人的內心世界一道,以音樂般的序列和諧展開,詩人寫作的本土特質與鄉村經驗融為一體,勾勒出詩人精神返鄉極為動人的心靈軌跡。
與此相關,詩人對於詞與物的關係也產生相當的迷戀態度。詞與物的對稱與彼此融彙讓詩人對精神歸宿的追求進入更高的層次。念琪嫻熟出入於物我兩忘的境界。在詩集第二輯《如歌散板》中,詞語覆蓋在表麵的程式化觀念被解構,字義的演變幻化出一幅一幅美妙絕倫的畫麵。比如“蒲公英”、“雨季歌者”、“預謀一場花祭”、“南方的熱情”,還有“清明”、“盛開”等為題的詩,承載著各自的命運,暗喻出實物的構架。詩人走向“傳統”的做法反而造成了某種“陌生化”的效果,從而達到了對詞義的再創造。詩人的“所指”撒向多個方向:隱喻隨之蔓延,在內心的南方與實際的南方之間存在的事物或跌宕起伏,或縱橫交錯。事物各自為陣,構成念想與存在的對應網絡。事物們最終都指向“我”,這就使詩人、世界和詩三者之間組成三維立體圖景。由此,詞物交融、天人合一的關係得以生成。而那個“古老的敵意”(裏爾克語)也終於得以消彌。在精神有所皈依的基礎上,詩人進行著本色的生命抒情。這樣的抒情在詩集中幾乎隨處可見。例如,“你的無奈終於被黑夜解救/這一年,人們紛紛離開村莊/沿著新月的光芒/舉起了火把” (《臘月》)。此種抒情態度可追溯至傳統古典詩學的命脈中。這一境界不僅是對於現世萬象的逐一實錄,而且在僵硬、龜裂的世界裏拉抻出一片彈性時空,將人情置於其間,在寒冷、虛無的風中深情地創造出點滴暖意,在疏離、傾軋的人間重新肯定人的主體地位。詩人從語言的內部尋找出路,在情緒複雜時覓得語言的生存方式。“一場花祭,讓我的心事盛開/鮮花朵朵,究竟在哪裏卜卦無知的未來/拱手作揖,心裏的許願/腳下深埋” (《花祭》)。夢一切可夢的,詩人窺伺著現世裏太多隱而不彰的幽暗和神秘,成了一個靈怪,在一種離奇的、失重的、暗影般的世界裏享受著極致的癲狂,更成了一個偶像破壞者,恣意嘲諷虛無的思想與情感。但詩人對愛情骨子裏存在信任乃至信仰態度。在詩人看來,愛情在“今天銀河有雨/牛郎背著孩子尋找織女”(《花之盛開》)時才出發,這是詩人的高明,也是無可奈何。詩人以東方話語闡述西方哲思,最終通向真實的存在之境:“上古演繹了一場悲劇/恒久述說相思的美麗/回家吧,月亮”(《中秋》),念琪的抒情放大到天穹和曆史想象中,回家的強烈訴求,有力的彰顯了詩人寫作隱秘而強大的精神動機。
詩人還運用理性的敘述手法來表達自己對於生命意義的感悟。例如:“昨晚的茶裏肯定被人下毒/一陣陣的飽嗝湧上茶多酚的多情”(《失眠》)。念琪在此詩中有了反抒情的自覺,不著意鋪排風景或抒發情感,這就意味著詩人將從心所欲不逾矩、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寫作追求轉向對於生命與事物本身的敏感。“黑暗中有人牽著好多羊從眼皮前走過/千姿百態的羊都扭過頭來看我”,在這裏,詩人在時間與空間的想象中把握生命的意義,並且將其個性的一麵融入其中。詩人此處的敘述在綿延不絕的瞬間完成,打破界限,通向各種無界限的可能性中去:詩人已麵朝遙遠的未來而沉思。這時,“何必轟轟烈烈?周而複始地熱情/台風跟身體一樣,一嘯而過”(《台風一嘯而過》)。詩人此刻思維澄明,寫下“思考是一串煎熬——/石頭不要生長/流水不怕阻斷/火車機械奔跑”(《思考》),此種思考狀態也體現為詩人誠實內心的語言脈絡。
簡單說來,詩人念琪的詩歌意境並不隻是一種靜止的陳述。他在地域性書寫、鄉土性書寫中完成傳統詩學的現代應用,這恰好體現出他的浪漫情懷與詩歌追求,構成本土化經驗呈現的純度與寬度。念琪在寫作手法上展示出對傳統意象的繼承和發揚,同時在營造自我抒情的藝術景觀,這種景象有利於詩人建立自己的風格特征、情感世界與寫作個性。詩人往往在直抒胸臆時表達自我的真實情感。一個真實的詩人,行走在大地上,抬頭仰望星空,往往心念故鄉。我們可以看到念琪是在通過寫詩這一行為實現精神還鄉的可能性:《守望吉嵐》即是詩人通過語言與意象完成精神返鄉的一個象征事件。
這本詩集的出版,對念琪而言應該是一個別具意味的事件,那不僅是現實意義上的回鄉,更是詩人向著精神之鄉、語言之鄉的歸返。對於任何試圖還鄉的詩人而言,此途亦即險途:地方知識、本土經驗與科學進步思想之間的緊張關係。或許,詩歌的諸多秘密起源中包含著上述緊張關係,就此而言,詩也是對世界之緊張關係的語言化解與情感撫慰。念琪守望吉嵐,實際上他在精神故鄉的守望中給自己準備了另外一個出發地:因為回鄉也意味著另一種向別處的出發。在這個意義上,詩人是一直走在精神返鄉的路上,一直幸福地走在精神返鄉的路上。
拉雜地寫了上麵的文字,在此真誠地祝賀念琪詩集《守望吉嵐》的問世。
2017年5月16日夜至17日淩晨4點
寫於北京京師園
(該文發表於2019年第2期《星星·詩歌理論》。譚五昌:男,江西永新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漢語詩歌協會秘書長。兼任貴州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已出版詩歌類編著及詩學專著二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