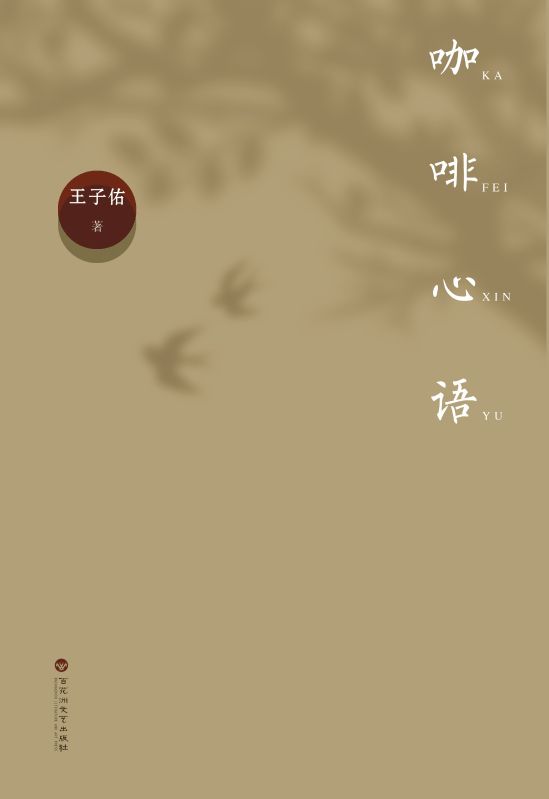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狼山散記
我這是第三次去狼山了。倒不是我對狼山情有獨鐘,而是前兩次是單位組織,那導遊把時間卡得死死的,把旅遊搞得像個登山比賽一樣,既緊張又乏味。此番一家四口自由來去,毋庸受以往跟團的種種約束,隻求乘興而去,盡興而歸。
狼山位於南通市南郊,是著名的自然風景區,由狼山、馬鞍山、黃泥山、劍山和軍山組成,西臨長江,山水相依,通稱“五山”。狼山居中,山不高,海拔僅106.94米,但挺拔俊秀,文物古跡眾多,其他四山如眾星拱月,把狼山襯托成眾山之首。相傳狼山曾有白狼居其上,又傳因山形似狼而得名。北宋時,州牧楊鈞覺狼山之名不雅,便改稱為琅山,又因山岩多呈紫色,故又稱為紫琅山,因此南通市也得“紫琅”之雅致別稱。狼山原在長江之中,北宋時狼山才與陸地連接。
此次登山,我們改從北門進入景區。狼山北麓較為幽靜,遊人稀少。此處以山為屏而構園,園內崖下為溪水,樹木蒼鬱,野花遍地,花徑旁點綴著稀疏亭榭,勝似田園風光。不由使人想起作家二月河在《散說名利場》中說過的:“有點像達官貴人發愁沒時間寫詩,吃慣了魚肉想吃一口老鹹菜,賓館裏住膩了向往雞鳴犬吠的鄉間農舍。”信步走去,猶見臨水巨石兀立,上刻近代書畫大家吳昌碩“大磊落磯”幾個大字,令人振奮激越。
沿山腳蜿蜒的山路緩步前行,來到狼山正門,即可見到法乳堂,其原為廣教寺大雄寶殿,又稱釋迦殿。紅漆大門上的對聯印證著彌勒佛的心聲:世上許多難耐事自作自受盡堪大肚包容,人間善男信女人相親相愛怎不滿腔喜歡。出大殿西側,拾級而上,是一座七級四麵的實心磚塔,是為紀念北宋住持智幻和尚而建的,稱幻公塔。塔北麵建有一碑亭,內立撫台平倭碑,記載了明代抗擊倭寇的史實。再往上行,則可見白雅雨烈士墓。白雅雨出生於南通,1905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時領導灤州起義,1912年壯烈犧牲,其絕命詩中曾抒寫錚錚鐵骨和豪情:“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革命當流血,成功總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隨日月旋。耿耿此心誌,仰望白雲間。”該詩為那個時代的人們指明了革命方向,不惜犧牲一切也絕不放棄對真理和信仰的追求。憶昔撫今,試看今天有多少人早已忘卻了初心,揮霍著前人用生命換來的勝利成果,從思想到精神都安於現狀甚至墮落,整天碌碌無為,沉湎於花天酒地醉生夢死之中,還鼓吹平庸可貴!
登上狼山之巔,即見廣教寺主體建築群,站在寺門前大觀台上,視野開闊,山水田野盡收眼底。寺前兩側廊柱對聯曰: 長嘯一聲山鳴穀應,舉頭四顧海闊天空。門旁書有“潮平兩岸闊,江束四圍圓”十個金燦燦的大字。進門是萃景樓,穿過大堂進入室內,迎麵是圓通寶殿,殿內青煙嫋嫋,香霧氤氳。我不知道在這種場合,人們會擦出怎樣的思想火花。
沿級而下,輾轉至狼山東南坡萬鬆嶺,樹叢中建有望江亭。亭旁兀立著幾塊巨石,登上巨石,視野變得開闊起來,俯瞰浩蕩長江東去,江南小山若隱若現。望江亭亭柱上書有對聯:千年古塔久曆風霜屹立於斯尚堅實,萬裏長江不舍晝夜奔流至此且從容。不由讓人感慨: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人生須臾,當自信奮鬥力爭朝夕。
下山後向東漫步,可遇到“初唐四傑”之一的著名詩人駱賓王之墓。其隨徐敬業起兵反對武則天所寫的一篇《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至今讓人記憶猶新。與該墓並列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僚屬金應將軍之墓和清代《南通州五山誌》編纂者劉南廬之墓。墓前豎立的石碑上書:碑掘黃泥五山片壤棲,筆傳青史一檄千秋著。從中隱喻三人的奮鬥史實和成果。
天色漸晚,步出東門旁職工通道,遊興未盡,不知何時能再登狼山一覽海闊天空呢?有人將閱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旅遊何嘗不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其當然可以是一種求索之旅,築夢之旅,思想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