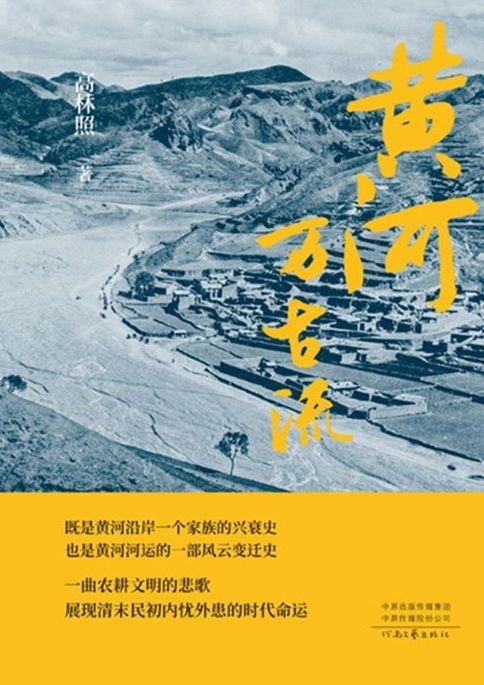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三章 魁記貨棧
1
鄭英魁深知這門差使來之不易,所以他一直記著離家前爺爺交代他的那些話,勤儉謙和又小心,《二程全書》不離手,《杜工部集》也不時地翻看,幹起公差來也格外用心。這些天,他天天帶著差役在碼頭上、大街上轉悠,一家一家地檢查,他要弄清整個東昌府有多少商戶,每家商戶的交易情況,是否有違禁私鹽的行為,是否足額交了稅賦。
這天,鄭英魁又帶著差役在碼頭上查驗,一艘三桅貨船開過來了,幾個水工使勁搖著船櫓,等這艘貨船靠在了碼頭,鄭英魁對隨行的差役說:“走,上船看看。”
剛到船邊,一個身材魁偉、嘴巴卻露出兩個大黃門牙的大漢攔住了去路:“幹啥咧?幹啥咧?”一說話,就噴出一片唾沫星。
鄭英魁隨行的一個差役衝上前大聲喊道:“幹啥咧?這是我們東昌府鹽運大使鄭大人,奉命上船查禁私鹽。”
那大漢“呸”的一聲,向地上使勁吐了口痰,不屑地說:“鄭大人?東昌府地界啥時候冒出來個鄭大人?”
“你小子,妨礙公務,辱罵朝廷命官,走,跟我們到衙門裏去。”說完,鄭英魁帶的幾個差役就要上前捉拿那個大漢。
“且慢。”鄭英魁攔住了幾個差役,鄭英魁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人與人的關係錯綜複雜,不定誰跟誰有牽連呢。眼前的這個大漢,見官不怕官,見官還罵官,看來他也大有來頭。想畢,鄭英魁走上前,雙手抱拳,“敢問好漢尊姓大名,家住哪裏,做何生意,請一一道來。”
“俺叫黃大牙,俺這船是王四海王掌櫃的,你們鄭大人還要查嗎?”
鄭英魁一聽是王四海的,腦子裏立馬浮現出金道正金大人的身影,鄭英魁渾身打了個激靈。王四海的貨船,查還是不查呢?鄭英魁作了大難。如果查,金道正金大人會怎麼想,誰知道金大人和王四海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交易,而且,鄭英魁還收了人家王四海兩千兩銀子,短處在人家手裏呢,把柄被人家握著呢。可是,不查呢,這幫差役跟著,一聽說是王四海的貨船就不查,那其他人的貨船還查不查?再者說,一提王四海就不查了,那豈不太長王四海的威風、滅自家的誌氣了?這鹽運使的官威以後還怎麼撐得起來?還有,如果這船隻是一般的貨船,而沒有私鹽,王四海得理不讓人,可咋辦?
這時,隨行的差役在一旁催問:“鄭大人,咋辦?”
不容鄭英魁多想了,鄭英魁心一橫,說:“我們是秉公辦事,別管誰的船,咱照查不誤,先查了再說。”鄭英魁說完,帶頭跳上船。
有了鄭英魁這句話,隨行的幾個差役跟著跳上了船。這時,隻見貨船船艙內跳出幾個壯漢,都掂刀拿棍,鄭英魁隨行的差役也抽出刀劍,一時劍拔弩張,雙方對峙起來。
鄭英魁見此情景,哈哈大笑,對為首的黃大牙說:“黃老弟,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們是奉公查禁私鹽的,如果船上沒有私鹽,你們怕什麼?我們也是例行公事,轉一圈兒就走,你們犯得著這樣嗎?”
黃大牙噴著一口唾沫星子說:“想查,可以,順著船沿兒走一圈兒就行,船艙裏的貨都是打包好的珍貴瓷器,你們就不必進船艙裏看了,打碎了一件,你們吃不了兜著走。”
“好好好,我們就順著船沿兒走一圈兒。”鄭英魁說完,領著幾個差役順船邊慢騰騰地走,順勢低頭瞅了瞅船艙,隻見裏邊大包大包、鼓鼓囊囊地堆著貨物,船艙地板上還有一些散碎的白花花的鹽粒兒,這分明是販賣私鹽的一條貨船,鄭英魁心裏有了數。
黃大牙一直跟在鄭英魁身後,警惕地看著鄭英魁,鄭英魁繞船轉了一圈,對黃大牙說:“黃老弟,你說這貨船是王四海王掌櫃的,可有憑證?”
“憑證?要啥憑證?我說是王掌櫃的就是王掌櫃的,我的話就是憑證。”黃大牙拍拍胸脯說。
“那不行,你要是不能證明這船是王四海王掌櫃的,這船我們要認真搜查。”
“你敢?”
“我有啥不敢?王四海王掌櫃做的是正經生意,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你卻冒充王四海王掌櫃販賣私鹽,辱沒王四海王掌櫃的名聲,來呀,把這黃大牙先行拿下,再把貨船扣留,替王四海王掌櫃正正英名。”鄭英魁義正詞嚴地說。
“嘿!你這個鹽運使,有意思,以前的鹽運使,隻要聽說我們王掌櫃的大名,早跑得無影無蹤,你倒好,還敢到俺王掌櫃的船上溜一圈兒,這已經給你天大的麵子了,你還不依不饒的,你還說這不是王掌櫃的貨船,大睜倆眼說瞎話,你真是吃飽了撐的,不想幹了吧?別看你是個鹽運大使,俺王掌櫃一句話,你明天就得卷鋪蓋滾蛋。”
鄭英魁一聽這話,怒火中燒:“黃大牙,話不可說絕了,我這鹽運大使也不是白撿的。我要是沒有金剛鑽,就攬不了這瓷器活兒,你既然把話說到這份兒上了,我今天就非查不可,今天非把你送到衙門裏不中,我不管他什麼天王老子,我還真就較上勁兒了。”
鄭英魁說完,對隨行的幾個差役說:“你們還愣著幹什麼?把這黃大牙給我綁了。”
差役正要動手,隻聽岸邊碼頭上有人喊道:“鄭老弟!鄭老弟!”
鄭英魁抬頭一望,卻見王四海在岸上向他招手,鄭英魁心想,這家夥消息恁靈通啊,這才多大一會兒啊,他可來到了現場。鄭英魁不敢怠慢,趕忙下得船來,向王四海走去。
王四海說:“鄭老弟,大熱的天,不在衙署戶房裏納涼,到這運河上幹啥咧?走,跟老弟我去茶館,咱吃茶去。”
鄭英魁一本正經地說:“王掌櫃,我奉命來查私鹽,正好查到你的船上,等我查驗完畢再說。”
“查啥呀查?在東昌府誰不知道我王四海是個正經生意人,我走的是正道,掙的是良心錢,你剛來東昌,不了解情況,你身後幾個兄弟能不知道嗎?我的船從來可都是免檢的,連知府大人金道正都不查我的船。”
“是嗎?那我這次真要查一查了。”鄭英魁說。
“查啥查呀?我的船已經開走了。”王四海指了指運河方向。鄭英魁扭頭一看,可不呢,他跟王四海說話的當口,王四海的貨船駛離了碼頭。
鄭英魁如釋重負,他心裏一塊兒石頭落了地,這貨船終於開走了,要不開走,他鄭英魁還真沒法兒處理呢,唉,走了好,一了百了。不過,鄭英魁表麵上還裝著很生氣的樣子指指遠去的貨船說:“王掌櫃,你這是唱的哪出戲啊?你怎麼讓你的貨船開走了呢?”
“笑話,我在這兒站著沒動,我怎麼讓貨船開走了呢?這貨船來來往往,不是很正常的事嗎?算了,啥也別說了,走,跟老弟我喝茶去。”
“喝茶就免了,我回去還有些事,不奉陪了。”說完,鄭英魁帶著幾個差役離開了運河碼頭。
“不送了,走好啊!”王四海滿麵笑容地說。
2
到了晚上,天氣異常悶熱,熱得人頭昏腦漲,鄭英魁卻趁著燭光捧著《二程全書》在驛站內潛心攻讀。他一手拿書,一手拿把大蒲扇,穿了身白色絲綢單衣,渾身早已濕透。他肩上搭了一條濕毛巾,不時地擦一擦流到眼角滾到鼻尖滴到下巴的汗珠,兩隻腳則放在一桶涼水裏,用以緩解暑氣。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鄭英魁正搖頭晃腦地讀著《二程全書》,這時,從河洛老家一路跟來的鄭英奇來到鄭英魁房間,見此情景,對鄭英魁說:“英魁哥,這麼熱的天,你還穿戴恁整齊,別讀書了,去外邊涼快涼快吧。”
“沒事,這算什麼?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佛經又雲:不受魔不成佛,不吃苦不開悟。我也正好借此機會鍛煉鍛煉意誌,磨煉磨煉心性,存天理,去人欲。嚴格要求自己,就要從這些日常小事做起。”
“唉,哥,你忙了一天,這麼累,天又這麼熱,你還在讀書、鍛煉意誌啊?別太辛苦了,對自己恁狠幹啥?你要注意自個兒的身子啊。”
“英奇,古語雲:待有餘而濟人,終無濟人之日;待有閑而讀書,終無讀書之時。我沒事兒,年紀輕輕,不吃點兒苦,啥時候吃苦?你沒聽人說嗎,年輕時多流汗,年老了才會少流淚。年輕時吃苦不算苦,老了吃苦才真苦。要想老了不吃苦,就得年輕時多吃苦。對自己狠,是為了別人不對自己狠,現在不對自己狠,將來才會對自己更狠,別人也會對自己更狠。”
“哥,你說得有道理,不過,一般人可是做不出來,像我都不中,我就吃不了這個苦,所以說我也當不了你這官兒,幹不成啥大事。”
“管不住自己,咋能管住別人?要想管住別人,必先管住自己,我越讀《二程全書》,越覺得理學的厲害,治國興家靠理學,正理啊。”說到這裏,鄭英魁又說,“英奇,你別光站這兒了,去給我倒碗涼開水。”
鄭英奇端來一大碗涼開水遞給鄭英魁,鄭英魁接過後“咕咚咕咚”喝了個精光,“得勁,真得勁。啥是快樂?這就是快樂,瞌睡了遞來個枕頭,渴了喝碗涼白開,比啥都得勁。”說完這句話,鄭英魁突然想起什麼,問道,“英奇,你不睡覺,來我這兒是不是有啥事兒?”
“嗯,我想問你個事兒。哥,你今兒個是不是去查王四海的船了?”
鄭英魁一愣:“你咋知道?”
“哥啊,你是不知道,我跟你來這兒之後,沒事就跟人噴空兒,就是想了解些東昌府的事情,我怕你不明底細辦差吃虧,我聽說王四海可不是一般人哪,所以,你今天辦這事兒,很快就傳開了,不隻是我知道,東昌府很多人都知道。”
“是嗎?”鄭英魁心裏七上八下,這東昌府的水真深哪。
“哥,不過,聽說你沒有查成,咱今天不查王四海的船就對了。在東昌府,誰敢惹王四海王掌櫃呀!”
“此話怎講?王四海不就是一個商人嗎?有啥了不起?”鄭英魁故作不知。
“哥,你的前任是咋走的,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咱來的時候,前任鹽運大使就走了,咱跟他沒照上麵兒,沒說成話,不知道他為啥高升,也沒顧上打聽。”
“還高升呢?削官為民了。要說你前任那位大使跟你差不多,也是有點兒直,不信邪,非要跟王四海王掌櫃過不去,結果,沒整治住人家王掌櫃,倒把自己的飯碗搞砸了。”
“王四海不是本地人,他是徽商,咋恁厲害?”
鄭英奇壓低聲音說:“哥,你不知道,王四海跟東昌府知府金道正金大人關係好著呢。這事兒全東昌府的人都知道,恐怕就咱倆不知道。聽說,王四海的生意有金大人的份兒,王四海在明處,金大人在暗處,倆人合穿一條褲子。”
“噢——”鄭英魁若有所思,心裏波濤洶湧、感慨萬千,原來金大人跟王四海還有這種關係,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啊。
“哥,你不知道,這王四海還有更厲害的關係呢。”
“誰?”鄭英魁知道王四海跟金道正關係鐵,可是,王四海還有什麼關係,鄭英魁倒不知道,不過,鄭英魁也能預感到王四海不隻有金道正這一個關係,像他們做大生意的,走南闖北,上下都打點得到,說不定京城裏也有後台,至於是誰,鄭英魁倒不知道。
“王四海還有個關係,叫王強,他跟王強是一個村的,是本家兄弟。”
“王強是誰?”鄭英魁不解地問。
“你不知道,其實我原來也不知道,咱中原地區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可這海邊的人,沒有不知道王強的。”
“是嗎?那他是幹啥的?”
“幹啥的?王強他可是大弄家,是大海盜,是朝廷通緝的重犯要犯。”
鄭英魁聞聽此言,更加吃驚,蒲扇也不搖了,也顧不上擦臉上的汗了,急忙問道:“照你這麼說,那王四海也該是通緝的要犯嘍?那王四海咋還恁厲害呢?那金道正金大人咋還跟他王四海打得火熱呢?”
鄭英魁越聽越覺得這個王四海可怕,看來,王四海是個禍根,還是敬而遠之、離他越遠越好。“兄弟,照你這麼說,王四海是個通匪的商人了?”
鄭英奇說:“哥,是咧,想做海上生意,沒有海盜的保護,沒有官府的照顧,能做成嗎?王四海能做那麼大的生意,就是跟王強有關係才這樣的。你想想,王四海掙的銀子會都裝到自家腰包裏嗎?他落三分之一,再給王強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都打點各位官家了?”
“這些官員就不怕將來萬一有一天皇上翻臉了,開始收拾王強了,那不就倒黴了嗎?”
“哥,人都是管頭不管屁股,都是隻顧眼前,誰想恁遠的事兒?車到山前必有路,到時候再說。”
“嗯,兄弟,沒有白帶你來,你還真幫我大忙了。以後你沒啥事兒,就找那閑雜人等多聊聊,多了解些情況,咱在東昌府就會少走很多彎路。”
“放心吧,哥,你把我帶到東昌府來,東昌府人不少,可就咱倆親,我不跟你一條心,誰會跟你一條心?”
“嗯,多長點兒心眼。你也看到了,咱到這兒,人生地不熟的,這地方又是繁盛之地,更是龍潭虎穴,不好混。混不好,就像你說的,也許跟我那前任一樣,就被人趕跑了。趕跑是小,說不定啊,還招大禍呢!”
這時,鄭英魁想起王四海到驛站給自己送銀兩的事,有點兒後怕,下意識地說:“這王四海的銀兩可不敢沾啊。”
鄭英奇聞聽此言,詫異地問:“哥,你說啥?”
鄭英魁自知說漏了嘴,急忙打圓場說:“啊,沒啥,沒啥,我是說老家生意上的事兒呢。”
鄭英奇歎了口氣說:“哥,咱一轉眼離開老家倆多月了,也不知老家咋樣了,山高路遠,也沒個消息,我有點兒想家了。”
“英奇啊,當個人,忠君報國,處處是家,公私不能兼顧,忠孝不能兩全,既然走了當官這條道,就要做好舍家的準備。人人都說當官好,世人誰知吃飯難?你想家了,其實我也想家了,這樣吧,你替我回老家一趟,看看家裏有啥事沒有。”
鄭英奇點點頭說中。
3
第二天,鄭英魁從驛站挑了匹快馬交給鄭英奇,又在街上買了些東昌府的土特產,還送給鄭英奇一些盤纏,鄭英奇簡單收拾了行裝,回河洛縣鄭家村探親了。
半個月後,鄭英奇回來了,鄭英魁急忙問鄭英奇老家咋樣,家人的身體咋樣,鄭英奇說:“好,都好,就是家裏生意有點兒緊張,錢上周轉有些困難,俺雲祥大伯的身體不太好。”
鄭英奇說得輕描淡寫,鄭英魁聞聽此言卻坐立不安,他拉著鄭英奇的手說:“兄弟,跟哥說實話,我爹身體到底咋樣?”
“哥,沒啥事,人年紀大了,都會有這病那病的,沒啥事。”
“你跟我說實話,你要是不說實話,你就不要再跟我了。”
鄭英奇歎了口氣,說:“哥,俺振昌爺一再交代我,不要跟你提家裏的難處,光說好的,可我的嘴不把風,有些話還是說漏了。”
鄭英魁一聽,更坐不住了,著急地問,“兄弟,到底咋了?家裏到底出啥事了?”
鄭英奇囁嚅著說:“也沒啥,就是俺大伯走山路不小心摔倒,腳崴住了,躺床上不會動了。”
鄭英魁著急了,說:“兄弟啊,這是小事嗎?這麼大的事你咋不跟我說呢?人年紀大了最怕崴住腳摔著腿躺床上不會動了,人往床上一躺,整天不動,啥病都出來了,這可不是小事,不行,我得趕快回去一趟。”
事不宜遲,鄭英魁向金道正金大人請了假,簡單收拾下行裝,在鄭英奇的陪同下,騎快馬日夜兼程回到了河洛縣鄭家村。
臨回老家的時候,鄭英魁看著王四海送的那兩千兩銀票,猶豫不決,帶回老家還是不帶回老家呢?他鄭英魁上任時間不長,也沒有多少俸祿,如果說回家不帶些錢也說不過去,可是,如果帶走這兩千兩銀票,就等於上了王四海的套,等於被王四海係上了一根繩,從此,王四海讓他鄭英魁往東他不能往西,叫往南他不敢往北。
猶豫了半天,鄭英魁還是決定把這兩千兩銀票拿回家,眼下,老家生意不好,父親又有病,不拿回去些錢,咋辦?至於將來咋樣,將來再說吧。
鄭英魁把這兩千兩銀票裝進包裹,沒有跟鄭英奇說這事,回家後才發現,父親的病情真的不輕。
父親鄭雲祥跟鄭英魁不一樣,他活這大半輩子,對做生意不感興趣,卻喜好讀書,讀書時間長了,也想考取個功名,好光宗耀祖。怎奈他命運不濟,屢考屢敗,總是名落孫山。萬般無奈,通過納粟捐了個監生的虛職,但他總覺得不滿足,總是咽不下這口氣,因為監生這個職位,在當時已經江河日下,流品以雜,那些潔身自好的飽學之士對監生一職早已嗤之以鼻,打心眼兒裏看不起。因此,鄭雲祥並不以此監生為榮,反以監生為恥,他一直想通過正途取得功名,在讀書人麵前抬起頭來。
在鄭英魁納捐到洧川縣任職又提拔到山東東昌府之後,鄭雲祥對做官仍念念不忘,他無心做生意,生意上的事兒由年邁的父親鄭振昌打理,他則鉚足了勁兒到開封府參加鄉試。
這天,他在仆人的陪同下,走在開封的大街上,但見石子鋪道的大街兩旁,攤販林立,人聲嘈雜,讓人眼花繚亂。鄭雲祥雖是富家子弟,但畢竟長在山溝溝裏,沒見過大世麵,今日到了開封府,真是大開眼界。
鄭雲祥邊走邊四處張望,見路邊圍了一群人,鄭雲祥和仆人互相對望了一眼,兩人好奇地湊了上去,踮起腳往人群中間瞅,人群裏,原來是一個剃頭的。鄭雲祥正要離開,仆人說:“老爺,別慌,你看那剃頭的可是不一樣。”隻見那剃頭的師傅拿了兩把剃頭刀,左手一把刀在一個半躺著的老先生的頭上剛刮了一刀,揚一揚手中的這把剃頭刀,刀子甩到了半空,接著,右手另一把刀在老先生的頭上又刮了一下,刮了之後又扔到半空中,等第一把刀快落下來時,這剃頭的師傅接過後又在老先生的頭上刮了一下,就這樣,一上一下,輪番在老先生的頭上刮來刮去。老先生半閉著眼,一副很享受的樣子,而老先生的頭上邊,刀光閃閃,兩把刀像銀燕飛舞,周圍的人看得心驚膽戰、眼花繚亂,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鄭雲祥和仆人眼都看直了,正在發愣發呆的時候,隻見剃頭的師傅倏然收起兩把刀,裝進剃頭架上的藍布袋裏,又從藍布袋裏拿出另一把更小點的刀給老先生刮臉、修眉毛。一切停當,老先生睜開眼,伸伸懶腰,滿意地說:“真得勁!”圍觀的人群響起“啪啪”的掌聲。
鄭雲祥感歎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看來不能死讀書,要多出去走走才能長見識。”
仆人說:“是啊,老爺,您不能天天關在屋裏讀書,您就是出去太少了,咱中國地方大著咧,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好多好地方您都不去,太虧了。”
鄭雲祥說:“嗯,咱小山溝溝裏的人,就是眼界小,到了大地方,才算開眼界,你說得對,我以後有機會要多出去走走轉轉,見見世麵。”
鄭雲祥帶著仆人繼續往前溜達,見有一家店鋪前圍了很多人,鄭雲祥和仆人也湊了上去。隻見這家店鋪在售賣一種洋玩意兒,旁邊有個招牌寫著“洋火”倆字。店掌櫃手拿著這個長約一寸的洋火,一擦就起火,人人見了都很驚奇。有膽大的人問價,竟然十兩一盒。很多人都是隻看隻問,搖搖頭伸伸舌頭嫌貴就走了。鄭雲祥是個孝子,他給父親鄭振昌買了一盒。看到這家店鋪裏還有賣小圓鏡的,又給妻子鄭趙氏買了一個小圓鏡。想想也該給兒子鄭英魁買個禮物,向前溜達了一圈,隻見一家賣小孩兒玩具的,店鋪裏有麵具鬼臉、木刀木槍、空竹、小泥人頭、小鳥籠,鄭雲祥想給在東昌府做官的兒子鄭英魁捎個什麼玩意兒,再一想,鄭英魁已經十八歲了,是個小大人了,不是小孩子了,還怎麼當他是小孩子呢?想到了這裏,他自嘲地搖頭笑了笑,罷了這個念想。再走走瞅瞅,見到一些流動書販,背著小布包,向路人兜售《百家姓》《三字經》《千家詩》等書,大都是木版的,也有麻紙的、竹紙的,也兼賣些小羊毫、烏龍水毛筆,還有太華秋、龍門等墨錠。鄭雲祥想給鄭英魁帶些書和筆墨紙硯,可這些小攤販沿路兜售的是劣質品,鄭雲祥看不上眼。鄭雲祥來到一家較大的書鋪裏,買了些寄售的古籍珍本,如《東京夢華錄》《洛陽伽藍記》,他讓仆人收好帶回去,等有機會鄭英魁回家了給鄭英魁看。
鄭雲祥住在徐府街的山陝會館裏。晉商和秦商出了名的會做生意,所以,山陝會館是開封城所有會館裏規模最大的。大門正對著的影壁青磚砌就,下以石條為基,基上用磚砌成雙層須彌座,分別雕有仰蓮、雲氣等花紋,頂是歇山頂,簷下方椽。影壁後是山門兼戲樓,南為山門,北為戲樓,上為單簷歇山頂,覆以孔雀藍琉璃瓦。戲樓兩側,各有一方形角樓,是會館廟堂的鐘鼓樓,鐘樓懸匾“舞鯨”,鼓樓懸匾“泣鶴”。再往裏,是一個寬敞的大院,東西配殿各有麵闊五間、進深兩間的廊廡,大院中間先有拜殿,也是麵闊五間、進深兩間,單簷歇山卷棚頂,上覆孔雀藍琉璃瓦,雕花脊,簷下無鬥拱,平板枋上是高浮雕牡丹圖,各間大額枋分別浮雕著“商旅入城”“高士賢隱”“駱駝商旅”“商旅歇馬”等商幫故事和透雕人物、鳥獸。拜殿後是大殿,中間是勾連搭,麵闊五間、進深兩間,單簷懸山頂,前後出廊,殿頂覆蓋孔雀藍琉璃瓦,兩山用琉璃搏風,簷下施五踩雙下昂鬥拱,前後簷各有柱頭鋪作六朵,補間鋪作六朵。平板枋上高浮雕龍、山鷹及山水花草,殿內梁起七架,前出後單步梁,中柱減出一列,顯得殿內非常寬闊。殿內供奉著關羽坐像,因為關羽是山西人,所以山陝會館敬關羽,其他會館則不敬。
戲樓經常有戲,院子裏擺上方桌,桌子四圍擺上長條凳,每條凳子上可坐兩人。院子裏賣零食的著竹籃、托著木盤,到處穿梭,向看客售賣瓜子、成串削皮的荸薺、蘿卜片、生紅薯片、糖蘸山裏紅等,賣水煙的則拿著足有二尺長的銅管水煙袋往看戲人嘴邊一戳,看戲人眼也不瞧,含著煙管“呼呼嚕嚕”抽幾口,隨手扔給賣水煙的幾個銅錢。也有送手巾的,掂著個簸箕,裏邊放著幾十條熱毛巾,走到看客前邊,有的看客順手拿起一條熱毛巾擦擦油津津的臉,然後扔幾個銅錢在裏邊。有的看客大老遠就招呼要熱毛巾,送毛巾的就把熱毛巾卷在一起,隔著人群直接扔過去。
戲樓前熱鬧鬧、亂哄哄,但隻有大老爺兒們,女座設在旁邊角落裏,即使是夫妻也不能坐在一起。
秦腔高亢,唱的是《玉堂春》。鄭雲祥忍不住想到前院看戲,但是,他用手掐掐自個兒的大腿,壓製住了自己的想法,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讀書求功名是大事。鄭雲祥閉門謝客,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刻苦備考了十幾天,終於等到了開考的日子。
頭天晚上,鄭雲祥激動得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也可能是緊張過度,一直到雞叫三遍,他才昏昏沉沉地睡去。天剛蒙蒙亮,仆人就來叫他起床,催他早點兒去考場。
鄭雲祥暈乎乎地和那些從全省各地趕來的莘莘學子坐在一個一個像鴿子籠一樣的小房子裏,奮筆疾書,等寫完卷子交卷時才發現,他的卷子越幅了,也就是沒有按規定寫,名字寫在了裝幀線外。鄭雲祥急得大哭,向監考官求情,被監考官訓斥了一頓。鄭雲祥當時就雙腿一軟,癱坐在了地上。
這次考試,鄭雲祥當然名落孫山。
回家後,鄭雲祥心裏難受,這天到邙山上散心,可是,人該倒黴了喝口涼水都塞牙。他心情不好,腦子暈暈乎乎的,結果,在下山時,一不小心一腳踩空,崴住了腳,摔倒在地。郎中一看,骨折了,需要臥床治病半年。
鄭雲祥臥病在床,鄭振昌年紀大了還要照顧生意,力不從心,累得麵容憔悴,而鄭家生意也因為照顧不周,經營困難。
鄭英魁從東昌府返家後,把王四海送的那兩千兩銀票拿出來了,說:“爹,我這趟回來帶了兩千兩銀子,家裏先用著吧。”
鄭雲祥見了銀票,問道:“兒啊,你去東昌府上任沒有多長時間,你從哪兒弄恁多銀兩啊?”
鄭英魁說:“爹,我聽說您有病,家裏生意又不好,我從朋友那裏借了些錢。”
鄭雲祥說:“你剛去東昌府時間不長,哪有那麼有錢的朋友!”
“這個,爹,你就不用管了,我的朋友多,沒事。”
“啥叫沒事?你跟我說,是啥樣的朋友?”
“做生意的。”
鄭雲祥聽罷臉色凝重,說:“兒啊,你幹這差使雖說官兒不大,可是權不小,管鹽運,那是肥差啊,我雖說沒有跟著你去東昌府,可我也知道,巴結你的鹽商不會少,求你的人多得很,你可要潔身自好,管好自己,可不能收人家的銀兩、占人家的便宜。誰的錢都不好掙,誰給你錢都不會白給你的,都是要回報的,回報小了還不行。”
“嗯,爹,這個我知道,我天天讀《二程全書》,存天理、去人欲,要理學治家,我管著自己呢。”
“你既然管著自己,那為啥還要借人家兩千兩銀子,這可不是小數目啊。”
“這不是家裏有難了嗎?”
“家裏有難,也不能要那不敢要的錢,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去東昌府時間不長,不會有深交,你這錢來路不正,人家不會平白無故借給你這麼多錢,這錢你還拿回去,家裏再難也不能要這錢,這錢不是錢,是陷阱,是火坑。”
“爹,您老先拿住,等我俸祿發下來了,我再還人家。”
“算了吧,你以為我不知道?知府大人一年的俸祿才六十兩銀子,知縣一年的俸祿才四十五兩銀子,你這鹽運使一年的俸祿才三十兩銀子,你拿什麼還人家兩千兩銀子啊?不要說了,把錢拿走。”
“爹,我不能看著爺爺、您和俺娘在家受罪啊,那樣的話,我怎安心在外當官呢,要不我辭官回家吧?”
鄭雲祥聞聽此言,抬手就要打鄭英魁,可是舉了半天,又無力地放下了,說:“兒啊,咱祖宗幾代都想出個當官的,我不就是一心想當官卻沒當上才出事的嗎?你好不容易有點兒出息了,你又撂挑不幹了,你這不是想氣死我嗎?你咋到祠堂跟祖先交代啊?”
鄭英魁低著頭說:“爹,我不能做那不孝之人哪。”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既然當了官,就是朝廷的人,就別想家裏的事,有我在,家倒不了,你就放心走吧,今兒個收拾收拾,明天就回山東去,不能耽誤了公家的大事。”
“爹,當官也老難哪,可不是好幹的,俸祿又低,看看咱家成啥啦?您看病都沒錢,我還真不如在家做生意呢,好賴也比當那芝麻小官強。”
“要是好幹誰都當官了,就是因為不好幹,咱才要幹,才要顯顯咱鄭家的能耐。再說了,要當官就不能想發財,要發財就不要去當官,咱既走當官這條道,就別想掙錢的事兒。”
“爹,咱總要生活吧,你看我這次回來,也沒有帶啥錢,借人家的錢您又不要,您病成這樣了,我這心裏,能不難受嗎?”
“不用難受,明兒個一大早你就走。我沒有當成官,我就全靠你了。”鄭雲祥把話硬邦邦地撂在那兒了,不容反駁。
鄭英魁說:“爹,您有病,我眼下不能走,我不放心。”
“走吧,我的病不要緊,也就是崴住腳了,傷筋動骨也就一百天,歇歇就過來了。忠孝不能兩全,你該走就走吧,別耽誤了公差,你幹好公差就是孝順,你爹才高興,病才會好。記著把錢帶走還給人家。”
鄭英魁點點頭,收好銀票,第二天,依依不舍地離開了老家。
4
回一趟老家,鄭英魁心裏有了新的想法,他明白,隻靠做官掙的俸祿,別說養家,連自個兒生活都困難。千裏做官,為了吃穿,如果連吃穿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怎能安心做官?其實,鄭英魁想掙錢倒容易得很,隻要他歪歪嘴,就有那販賣私鹽的鹽商排著隊給他送禮,銀子就會大把大把地進腰包,就像王四海給他送禮一樣,一出手就是兩千兩銀子,一次所得就是他鄭英魁一輩子的俸祿,當官想掙錢真是太快了,真要把做官當營生,那是最大的營生,啥生意也沒有這來錢快。不過,那可是違法的事啊,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爹說了,不該要的錢不能要,不該收的禮不能收。再說,大清朝查貪腐查得緊,到處明察暗訪,弄得草木皆兵,貪汙受賄,那可是飲鴆止渴的事情啊。
鄭英魁一籌莫展、猶豫不決,常常在驛站裏緊鎖雙眉,走來轉去,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鄭英奇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他瞅了個機會悄悄跟鄭英魁說:“哥,我給你說個事,我看你整天愁,我知道你因為啥愁。”
“因為啥?”
“因為錢。”
“你咋知道?”
“我天天跟著你,我能不知道嗎?”
“你還怪能咧。”
“我不能。我要是能,你就不愁了。”
“這不怪你,要怪就怪咱命不好,命中隻有八鬥米,走遍天下不滿升,沒法兒。”
“啥命不命的,雖說人的命天注定,可三分靠運氣七分靠打拚,命也是可以改變的。”
“別貧嘴了,說吧,你有啥好法子沒有?”
“哥,活人不能讓尿憋死。你管著那些鹽商呢,食鹽是眼下最賺錢的買賣,官府壟斷了鹽業生意,而那些有門路的奸商走私食鹽,他們做生意掙恁多錢,你就不會也做鹽業生意掙些錢?你做生意比他們差嗎?你的腦子比他們笨嗎?”
鄭英魁歎了口氣:“兄弟,做官經商兩條道,不能攪到一塊兒,攪到一塊兒就亂了。”
“哥,看你說的,現如今當官的誰不經商?不經商,恁少的俸祿,早就餓死了。知府大人金道正五品官,一年的俸銀才六十兩,您這鹽運大使是從九品,一年也才三十兩,這不是逼著讓經商的嗎?”
“人家經商都是在官場站住腳的有根基的人,尤其是走私食鹽,那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人家有勢力,有後台,出個啥事有人保有人救,可是咱不中啊,咱上邊沒人,不敢出事,否則的話,咱一下子就玩完了。”
“哥,要我說,有時候該賭一把就得賭一把,隻管經商做生意,錢掙得差不多了,一看勢頭不對,大不了辭官回老家去,人活著弄啥?不就是掙錢嗎?當官不也是為了掙錢嗎?隻要有錢,還當那官幹啥?”
“英奇,你說得不對,我鄭家做官可不是為了掙錢。”
“那是為了幹啥?”
“是為了不受別人的氣。”
“哥,當了官,有了權,平頭老百姓不敢惹咱,地痞無賴不敢惹咱,可是,大官欺負小官,不還是有人惹嗎?您見了金道正金大人不也得低三下四嗎?”
一語點醒夢中人,是啊,幹啥沒人欺負?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世上沒有桃花源,哪兒都是人善人欺、馬善人騎,隻要有錢,活得輕鬆自在就行,人活在世上,不就是圖個填飽肚子有吃喝就行嗎?當個平頭百姓,還想啥咧。至於做官,如果實在做不成,那就不當也罷,那不是誰的祖宗事業,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早晚還得離開,早晚也有不當官的那一天。
鄭英奇的一番話讓鄭英魁想明白了,他開始琢磨經商的事兒了。
鄭英魁苦思冥想了一段時間後,把鄭英奇叫了來,說:“兄弟,我想好了,想在東昌府開個貨棧,經營食鹽。”
“那是好事啊。”
“不過我想讓你招呼貨棧生意,咋樣?”
“我來經營?”鄭英奇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哥,別開玩笑了,我從未做過生意,當掌櫃,我更沒那本事。”
鄭英魁微微一笑,說:“英奇哪,你隻需支撐門麵,我當背後的掌櫃,行吧?”
鄭英奇撓撓頭說:“那也不行,我可是沒做過生意啊,賠了咋弄?”
“做生意,就是一買一賣,賤買貴賣,賺個差價。隻要咱公平經營,不缺斤少兩,薄利多銷,隻要信息靈通,隻要沒人找事兒,生意有啥做不得?況且,咱這生意,經營食鹽,沒人查沒人管,這生意就是傻子也會賺錢。再說了,你聰明伶俐,是做生意的那塊兒料。”
鄭英奇囁嚅著說:“哥,你說行就行,我聽你的,不過,我醜話說頭裏,我要是賠了,你可別怨我。”
“放心吧,哥相信你,你有這兩把刷子,肯定會幹好的,就是賠了,我也不怨你。”
“不過,哥,做生意得有本錢,咱哪有本錢哪?”
“這不需你費心,本錢我已籌好了,你看,這是兩千兩銀票。”說完,鄭英魁從櫃子裏拿出兩千兩銀票。這還是王四海送給他的,他準備做生意賺了錢,再把這兩千兩銀子還給王四海。
“哥,你從哪兒弄這麼多錢?”
“找朋友借的。”
5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籌備,鄭英魁在東昌府開了個魁記貨棧,主要經營食鹽,由鄭英奇坐店支撐門麵經營,鄭英魁在背後坐鎮指揮。
魁是第一、居首的意思,常言說,店有雅號,客人自到,為了取好這個店名,鄭英魁從《呂氏春秋》中找到一句話:“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於是,就起了魁記這個響亮的名字,表示了鄭英魁做生意的雄心壯誌,同時也是取他名字裏的一個“魁”字。
魁記貨棧開業,沒有舉行隆重的開業儀式,鄭英魁不想也不敢張揚招搖,因為他知道,招搖就是招災,張狂是自取滅亡,他隻讓人放了幾掛鞭炮,去除邪氣,便開始進貨做起生意來。
有鄭英魁做後台,別看魁記貨棧不吭不哈,但生意好得很,悶聲發大財,埋頭幹大事,一般人不會在意魁記貨棧的經營狀況。可同行是冤家,魁記貨棧很快引起了王四海的注意。
東昌府的市場就這麼大,做生意的人就這麼多,有頭有臉的人更是屈指可數,如今,冒出個魁記貨棧,而且貨船晝夜運送貨物不停,能不引起王四海的注意?
王四海沒怎麼打聽,就知道魁記貨棧的掌櫃叫鄭英奇。鄭英奇,不用問,那是鹽運大使鄭英魁從老家河洛縣帶來的,這魁記貨棧的背後老板就是鄭英魁無疑。
於是,王四海又登門來找鄭英魁了,不過,這次王四海來,可不是低三下四,而是很有一副知府大人金道正的派頭。他穿一身滑涼的絲綢長衫,腳蹬方口布鞋,搖著一把折扇,在驛丞侯升的陪同下,挺著肚子,笑容滿麵大搖大擺地來找鄭英魁了。
鄭英魁剛吃過晚飯,正在驛站的房舍裏高聲誦讀《杜工部集》裏《兵車行》中的詩句:“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
驛丞侯升咳嗽了兩聲,“梆梆梆”敲窗戶,問:“鄭大使睡了嗎?”
鄭英魁聽出是侯升的聲音,故意問道:“誰呀?”
“我,侯升。”
“噢,是侯老弟啊,來了!”說完,鄭英魁打開門。
侯升領著王四海進來了。鄭英魁一見王四海,吃了一驚,心想,這個災星,他這麼晚來幹什麼?準沒什麼好事,可是,他不敢怠慢,急忙抱拳施禮:“哎喲,是王掌櫃來了,也不早點兒說一聲,有失遠迎,失敬!失敬!”
侯升替自己辯解道:“就是,王掌櫃來也不提前打個招呼,直接就到我這小驛站了,我也是冒昧得很。這不,王掌櫃說來找鄭大使,我就領他上來了。”
王四海抱拳回禮,說:“鄭大使平時很忙,料想你不一定在驛站裏,我也沒提前跟你打招呼,我是吃過晚飯沒啥事,溜達著就走到驛站了,順便到這裏來看一看,要是你在的話,咱就聊一會兒,要是不在,我就繼續遛彎兒。”
“難得一見,請坐,請坐!”鄭英魁熱情招呼著。
侯升識時務地抱拳倒退著出去了,隻剩下鄭英魁和王四海。王四海問:“鄭大使在忙什麼呢?”
鄭英魁說:“沒啥事,看看書,解個悶兒。”
“敢問讀的什麼好書呢?”
“《杜工部集》。”
“杜工部是誰?”
“杜工部就是杜甫啊,河南鞏縣人,我的近老鄉。”
“做啥生意的?眼時下在哪兒?”
鄭英魁聽罷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笑得差點兒岔了氣。自從來到東昌府,他還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
王四海不高興了,沉著臉問:“鄭大使,有這麼好笑嗎?”
鄭英魁也覺得有點失禮了,強忍著笑說:“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這杜甫嘛,不是做生意的,是唐朝著名詩人,號稱詩聖,與李白齊名,合稱‘李杜’……”
“得得得,鄭大使別說了,反正我也聽不懂,不就是一讀書人嘛,一介書生,窮秀才,百無一用是書生哪!”王四海冷冷地說。
“書生怎麼了?文能治國,武能安邦,書生也是國之棟梁啊。”
“鄭大使說書生那麼金貴,不過,我聽說鄭大使也不是正途出身,好像肚裏喝的墨水也不多吧?”王四海一句話把鄭英魁說臉紅了。常言說,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王四海真是哪兒疼往哪兒戳。
鄭英魁回敬說:“正因為我讀書不多,所以我如今沒事兒才要好好讀書呢,最起碼我知道杜甫是誰。”
“拉倒吧,知道杜甫是誰有啥用?是當吃還是當喝?”接著,王四海緩和了語氣說,“不過,一看鄭大使就是有誌向的人,佩服佩服。”
“王掌櫃過獎了,我一個鹽運大使,不入流的官職,有什麼誌向啊,也就是混碗飯吃吧。”
“鄭大使這碗飯可吃得夠香呢。鄭大使,我聽說東昌府有家魁記貨棧,可是你的掌櫃?”
“這個?啊,不,是我的一個本家兄弟叫鄭英奇開的,他跟我到東昌府來,閑著沒事幹,就做點小生意。”
“小生意?據我所知,那魁記貨棧的生意可不小哇!”
“噢,生意上的事兒我不太知曉,都是我兄弟在那兒瞎倒騰。”
“鄭大使,我這人是個直性子,不會拐彎抹角,不像那讀書人花花腸子多,實話實說吧,那魁記貨棧坐店的是鄭英奇,而背後的掌櫃就是你鄭大使。”
“啊?嗨!這個嘛——”鄭英魁有些語塞了。
王四海見此情景,伸頭湊到鄭英魁跟前說:“鄭大使,在我王四海跟前,你就不要這個那個的了,我也是生意人,咱倆眼下是同行,常言說,同行是冤家,不過,我不這樣認為,我做生意向來是有錢同賺、有利共享,我這人走江湖之所以順風順水,就是靠這,我是一個仁義之人,朋友多,財路廣。”
鄭英魁見已無法隱瞞,隻好說:“王掌櫃,實不相瞞,這魁記貨棧確實是我和我那本家兄弟鄭英奇一塊兒開的,我老家河洛縣有個客棧,也有一些河運生意,不過都不景氣,父親又臥病在床,家裏日子艱難,可眼下俸祿又低,萬般無奈,才出此下策,唉——”
王四海拍拍鄭英魁的肩頭:“鄭大使,要不我說你呢,家裏這麼困難,我給你錢你還推三阻四的。這不,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你不也開始想門路了嗎?不也開始做生意了嗎?你可知道,皇上是不允許官員經商的,你這是犯的死罪一條,我要是告發了你,你可是吃不了要兜著走的啊兄弟。”
聞聽此言,鄭英魁倒吸了一口涼氣,不過,他也不是膽小怕事之人,他腦子一轉,很快就反應過來了:“海哥,是不允許官員做生意,可那是太祖定的規矩,這麼多年來,早就沒人按這規矩辦了,滿朝文武,誰不經商做生意?我這點小生意,算個啥?”
“算個啥?你也是在世麵上混的,你也是當官的,你不懂得這個道理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找你的事,你再大的事也不是個事;想找你的事,你沒事也給你整出個事,是吧?”
“是啊,是這個理。不過,我初來乍到東昌府,沒有跟誰鬧別扭,沒有跟誰結冤仇,誰犯得著跟我過不去呢?”
“沒有誰跟你過不去,不過,在東昌府這地麵上,要是不識抬舉、不夠朋友,那就有人跟你過不去。”
“過不去又如何?過得去又如何?誰都有短處,我也不會怕誰。”
鄭英魁一番話義正詞嚴,王四海聽了倒吸了一口涼氣,這小子看來不好對付啊,是個人精啊。於是,王四海緩了口氣,笑著說:“是啊,鄭大使說得對,誰都有短處,誰也不會怕誰,不過,我送鄭大使那兩千兩銀子用著可好?”
鄭英魁一聽這話,徹底服軟了,王四海送的那兩千兩銀子作為本錢投到貨棧裏了。鄭英魁囁嚅著說:“這,海哥,那兩千兩銀子我家裏有困難,有些急用,就先用上了,不過,海哥,等過段時間,我有了錢,馬上還給你。”
王四海語氣陡然一轉,說:“鄭大使,我對你有點兒生氣。”
鄭英魁吃驚地問:“此話怎講?請海哥明示。”
“鄭大使,既然家裏恁困難,我送你錢是讓你還的嗎?我這人重義氣、講朋友交情,你是看不起我,還是嫌我的錢臟?動不動就說還錢,你這是打我耳光,你是看不起我,知道不?”
鄭英魁急忙解釋:“海哥,你資助我兩千兩銀子,我非常感激,不過,我這人臉皮兒薄,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施舍,不想欠人的人情,不想麻煩人。”
“鄭大使,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是外人嗎?”
鄭英魁連連擺手:“不不不,沒那個意思,海哥誤會了。”
“誤會了?說我誤會也可以,那樣吧,鄭大使,這是兩千兩銀子,你且收下,你不用再誤會了。”王四海說完,從懷裏摸出兩張一千兩的銀票,放到了麵前的桌子上。
鄭英魁站起來,把銀票推給王四海:“海哥,我已經拿你兩千兩銀子了,無功不受祿,這銀兩我斷斷不能再接受了。”
“鄭大使,你說無功不受祿,我可是找你有事呢,讓你辦個事咋樣?你就不覺得不好意思了吧?”
“海哥,有事隻管講,我能辦的一定全力辦,況且,你也知道,我來當大使這段時間,你的船,你的貨,我從來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盡量通融的。”
“對啊,鄭大使,你說無功不受祿,你對我這麼關照,你說,我感謝你不應該嗎?”
“這個……”鄭英魁一時語塞了。
“鄭大使,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你說,你千裏迢迢、孤身一人到東昌府,為的啥?家裏窮成那樣,老父親生病都沒錢醫治,你還不要錢,你是既傻又不孝。”王四海站了起來。
鄭英魁說:“海哥,大清朝對官員要求嚴,不能貪汙受賄,那是要剝皮掉腦袋的。”
“鄭大使,咱這東昌府,山高皇帝遠的,皇上咋能知道咱這兒的事兒?別說你了,知府金大人也跟我是好朋友,府衙上下都是我的好朋友,咋著?不都沒事兒嗎?天塌了砸大家,你是小心過度了。”
“海哥,我沒有背景沒有靠山,賺得起賠不起啊。”
“那樣吧,鄭大使,這錢呢,不是我給你送的禮,是我給你的本錢,想讓你與我合夥做生意的本錢,這可以吧?”
“做生意?這咋說呢?”
“咋說?鄭大使,我打小就做生意,是個生意場的老油條了,實話告訴你吧,你開貨棧,隻做鹽的生意,不咋賺錢,想賺大錢,還得做海外生意。”
“海外生意?”
“是啊,鄭大使,實話告訴你,我本家哥叫王強。”
“王強?王強是誰?”鄭英魁佯裝不知。
王四海“嘿嘿”一笑:“鄭大使連王強是誰都不知道嗎?”
“我初來東昌府,孤陋寡聞,請海哥指教。”
“王強哥手下有五六千人、大小船隻幾百艘,專發海上財,就像一個海上國王,日子過得逍遙得很。”
“厲害啊!”鄭英魁敷衍著說。
王四海繼續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隻有熟讀四書五經才能致仕,從而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可是,我本家哥王強打小就對讀書做官不感興趣,跟我一樣,喜歡倒騰事兒,覺得這種日子才充實,過得才有意義,而且王強哥還喜歡做大生意,倒騰大買賣,是個大弄家。”
“海哥,我倒聽說這個王強不是做生意的,是專門收拾做生意的啊。”
鄭英魁探頭望望窗外,漆黑一片,但聽幾聲狗叫在靜寂的夜空回響,鄭英魁壓低聲音緊張地說:“海哥,你跟王強來往可是要坐大牢、掉腦袋的。”
王四海哈哈大笑,笑聲在夜空傳得更遠:“鄭大使,我是一介商人,地位不高,跟那戲子、婊子差不多,但我有錢,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啥都不怕,實話告訴你吧,王強後台硬著呢,況且我跟我本家哥王強聯手幹大生意呢。”
“是嗎?”鄭英魁故作吃驚地站了起來,“海哥,這可開不得玩笑。”
“開啥玩笑?我跟王強哥聯手做海上生意,這事兒東昌府官場、商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不僅如此,上自知府大人,下至辦事差役,都和我聯手做海上生意。”
“海哥,你說的可是真的?”
“我這人以誠信為本,我說的是真是假,你可以打聽打聽,我沒必要瞞你。”
鄭英魁點點頭,話鋒一轉,說:“海哥,明人不說暗話,你今天來找我,所為何事,請明示。”
“啥明示不明示的,我不會說那文縐縐的酸詞,我就是來告訴你,你開有魁記貨棧,咱倆聯手經營海上生意,你也加入我這一夥,以後你幫我組織本地的貨源,我負責往海外運,海外的稀罕貨,運到你的貨棧裏,你幫我賣。”
鄭英魁一聽,直搖頭,說:“使不得,使不得,海哥,官員是不能經商做生意的,特別是不便跟你聯手做海外生意,這些事我是不幹的。”
王四海一聽此言,惱了:“鄭大使,我剛才跟你說了,東昌府大小官員都是我的生意夥伴,就憑你們當官的掙那倆錢,連塞牙縫都不夠,你不要擔心,萬歲爺如今對此事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幾年來大家都是這樣做的,沒事兒,真有事兒的話,我早不在此地了。”
鄭英魁還想推辭,王四海正色道:“鄭大使,你身為鹽運大使,收受賄賂,徇私舞弊,中飽私囊,還開設貨棧,以權謀私,金道正大人若是知道了,恐怕不會饒了你吧?”
鄭英魁聽罷此言,不吭聲了,他知道自從收了王四海那兩千兩銀子,他就像一條魚一樣咬住王四海這個釣魚者的魚鉤了,他再想掙脫開,已經不可能了,他隻有跟著王四海的魚竿在水裏遊動,王四海隨時可以把他釣上岸,把他當作一道美味佳肴。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別人送你一兩銀子,是想撈回十兩銀子,撈不回來,那不就賠了嗎?與商人打交道,怎能算計得過他呢?鄭英魁想到這裏,頭都蒙了。這時,隻聽王四海笑著說:“實話告訴你,想在東昌府這個地盤站住腳,就得跟我做朋友,不然的話——”王四海臉一拉,眼一瞪,“哼哼”兩聲,惡狠狠地說,“從哪兒來到哪兒去,趁早滾得遠遠的。”
說完,王四海把銀票撂給鄭英魁:“這兩千兩銀子你收下,以後跟我擱夥計,你就等著財源滾滾來吧。”
鄭英魁還想把銀票還給王四海,王四海已反背著雙手大搖大擺地離去了。
6
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鄭英魁萬般無奈之下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王四海的銀兩,第二天,王四海就派人去了魁記貨棧,商議跟魁記貨棧合作的事宜了。
鄭英奇急急來找鄭英魁,問:“哥,王四海想跟咱合作做生意,你看該咋辦?”
鄭英魁長歎一聲:“兄弟,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咱在東昌府人生地不熟,想站住腳,難哪!王四海是這兒的一霸,咱做生意搶了他的飯碗,他肯定不樂意,他明著是跟咱合夥做生意,其實是想挖咱的牆腳、壓咱的氣勢、爭咱的生意呢。”
“哥,那咋辦?”
“咋辦?強龍難壓地頭蛇,何況咱也不是啥強龍。人家看得起咱,不把咱的貨棧給砸了,就已經夠意思了,想合作就合作吧,大不了人家得大頭,咱得小頭。隻要能掙錢,隻要比當官的俸祿高就中。”
“哥,王四海的人說了,他們不是隻做鹽的生意,他們要做海外生意,那可是掉腦袋的事啊。”
“唉,兄弟,你別說了,人家讓做咱就做吧,有啥法兒咧?”說完,鄭英魁抱著頭痛苦地流下了兩行熱淚。
“哥,你別難過了,要不咱把貨棧關了吧,要是早知道這樣,咱也不起這念頭了,安安生生當鹽運大使,風風光光地查那些鹽商,大家看見你都是點頭哈腰的,那多得勁,可是一做起這貨棧生意,就有這麼多麻纏事,怪不得大家都想當官,不想經商,經商就是沒有當官好。”
“算了,別說了,開弓沒有回頭箭,覆水難收,眼下隻有暈著頭幹吧,好歹先掙點兒錢再說,一切聽天由命。真的有啥事兒,咱大不了辭職回家,隻要手裏攢倆錢,咱回河洛縣老家經營鄭記客棧去。”
自從與王四海聯手做起生意來,鄭英魁的魁記貨棧生意興隆,白花花的銀子仿佛從天而降,鄭英魁從未想過掙錢有這麼容易,這跟撿錢一樣。
有了錢,鄭英魁每月都派人往家送錢,父親鄭雲祥回信說:“我的病好了,家裏生意也好轉了,一切都好,不要再寄錢了。”鄭英魁回信說:“我在東昌府開了個魁記貨棧,這是咱鄭家在東昌府開的魁記貨棧掙的錢,我在這兒也不是長久之計,掙錢放這裏也不放心,最好是您老拿這錢把家裏客棧的生意擴大些規模,再買些地,置辦些家業。”
有了錢,鄭英魁不忘孝敬知府大人金道正,還經常請同僚們吃吃喝喝,關係十分融洽,也算在東昌府站穩了腳跟。同時,鄭英魁擴大投入,魁記貨棧的貨物周轉量越來越大。
不過,越是有錢,鄭英魁心裏越是不踏實,總感覺心咚咚跳,他知道這些錢掙得來路不明,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出事,他隻有心存僥幸、聽天由命了。
7
又是一年盛夏時節,東昌府經常狂風大作、電閃雷鳴、暴雨驟至,且數日不歇,造成洪水泛濫,運河水漫到了大堤外,街道上積水淹沒了腳脖子。東昌府地處黃河岸邊,黃河有“七下八上”之說,也就是每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是汛期,黃河水量特別大,隨時有決堤的危險,這些,更增加了鄭英魁的擔憂,他的心情也像“七下八上”的黃河水,波濤洶湧,起伏不定。
這天,鄭英魁獨坐在衙署戶房內,外邊烏雲翻滾,天空頓時陰暗了下來。狂風吹動樹木左右搖擺,不時有風透過門縫鑽進屋內,滂沱大雨砸在青磚鋪就的地麵上,發出“劈裏啪啦”的聲音,不久地麵就成了一片汪洋。雷聲轟鳴,忽遠忽近,突然,一陣“哢嚓嚓”聲響,一道灰白的閃電晃過窗欞,鄭英魁不由激靈靈打了個冷戰,頓時陷入恐慌之中。他再也坐不住了,索性站起來在屋子裏來回踱步。他心裏奇怪,自己本不是一個喜怒形於色的人,而且平時也算沉穩,為什麼最近老是心神不寧呢?難道是得什麼病了不成?可是,身上不疼也不癢,沒有什麼不適啊。
鄭英魁沒事兒就拿起《二程全書》看,可是,看不進去,他又拿起《杜工部集》,還是看不進去,於是,他又開始練字,但是,也寫不下去。他像一隻困獸,在屋裏轉來轉去,急得很。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他匆匆吃了晚飯,卻覺得胸口有些疼痛,喝了一杯熱茶,吐出兩口熱氣,方覺好一些,但心中依然悶得慌,他沒有洗漱,索性和衣倒頭便睡,睡到半夜,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夢見父親渾身濕漉漉地站在他的床前,臉色蒼白,一聲不吭,隻是看著他。他驚問道:“爹,您老咋來了?”父親仍是不吭,臉上卻流下了眼淚。鄭英魁伸手去擦拭父親臉上的淚痕,父親卻轉眼不見了……
鄭英魁一下子從夢中驚醒,借著窗外刺眼的閃電,他摸到枕邊的火鐮,打著火,點燃了蠟燭,屋內頓時亮堂起來。鄭英魁抬眼四望,屋內什麼也沒有,他定了定神,覺得這個夢非常奇怪,莫非父親在老家有什麼事了?莫非他的病情加重了?他再也無法入眠了。
風在刮,雨在下,雷聲隆隆響,一直鬧騰到天亮,才稍稍停歇。鄭英魁再也坐不住了,他總覺得家裏可能有什麼事,他要回家,於是,他來到衙署,跟金道正大人告假。金道正大人揉了揉紅腫的眼睛,他昨晚跟人喝酒喝到半夜,早上頭還暈乎乎的。
鄭英魁說了他想要告假還家的意思,金道正大人還沒有迷瞪過來:“什麼?要回家?”
“是啊,金大人,我家裏有點事,想告假三個月。”
“啥事?”
“老家捎信了,父親病情加重了。”
“啊,百善孝為先,既然老父親病重了,理當回去。行,準假。啥時候起程?”
“今天就走。”
“老弟,下恁大的雨,急啥急?”
“父親有病,我心裏不淨,坐不住。”
“那就回吧,把公差安排好,收拾回吧。”
“謝過金大人。”
鄭英魁告別了金道正金大人,雇了匹快馬,回老家河洛縣了。臨走前,鄭英魁把鄭英奇留在了東昌府,繼續經營魁記貨棧。他收拾了行李物品,向驛丞侯升以及相處的同僚辭行,更不忘與王四海告別,王四海說:“鄭大使,咱生意還得繼續做,你在老家再開個貨棧,到時候我給你送貨去。”鄭英魁敷衍著說中,互相作揖告別。
可是,還沒等到王四海去鄭英魁老家送貨,王四海就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