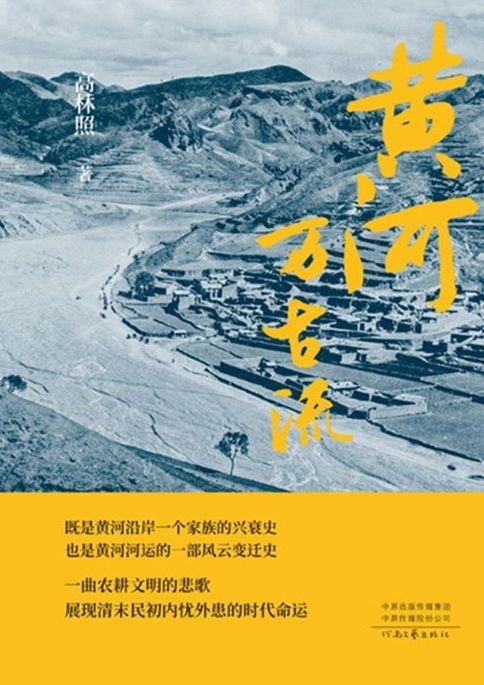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邙山遇險
1
起麒麟,
扛大刀,
您的隊伍叫俺挑。
挑誰?
挑英魁。
英魁不在家,
俺就挑您仨。
…………
清道光二十年(1840)夏月,英國遠征軍抵達廣東珠江口外並封鎖出海口,鴉片戰爭爆發。南方黑雲壓城、戰事吃緊,但在北方黃河岸邊的河洛縣鄭家村,卻是一片靜謐祥和的氣氛。
這天夜晚,明晃晃的月光下,涼風習習,鄭家村村東頭的打麥場上,忙了一天的人們聚在一起,席地而坐,談天說地,享受難得的農家清閑時光。
鄭家村南邊是青青的洛河水,北邊是蒼蒼的邙山嶺,邙山腳下就是波濤滾滾的九曲黃河。黃河千年流,萬古流,晝夜不息,奔騰喧囂,澆灌著兩岸平展的原野,滋潤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依山傍水,河洛交彙,鄭家村絕對是一個風水寶地。
來自黃河深處的涼風帶著陣陣魚腥味撲麵而來,鄭氏家族的大掌櫃鄭振昌和兒子鄭雲祥與鄭家村的老少爺們兒愜意地坐在一起聊天說閑話。鄭氏家族靠在河洛岸邊開客棧起家,後又在黃河、洛河上行船做生意,經過九代人的努力,鄭振昌家已是鄭家村的首富,方圓十幾裏也是赫赫有名。可是,鄭家雖是大財主,卻心存善念、與人為善,深諳財靠人聚、散財聚人的道理,謹記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的古訓,因此與街坊鄰居相處得很好。
大人們在聊天,鄭振昌九歲的孫子鄭英魁則與小夥伴們一起玩遊戲,他們玩的遊戲叫“起麒麟”。隻見小夥伴們分成兩隊,相向而站,一邊三個,共同唱歌謠。唱完之後,這邊站的小夥伴向對方喊話,問“挑誰”,對方站的小夥伴答一聲“挑我”。喊答完畢,先喊的那支隊伍跑向對方的隊伍去搶人,對方的人就開始跑,抱住跑不了的算是搶到了人。有人專門查人數算時間,到時間就停,搶到多少人就算多少人。下一輪,由另外一方先喊,接著搶人,到最後計算,每輪誰搶到的人多誰取勝。
小孩子們玩遊戲時喊的英魁,打小聰明伶俐,讀書過目不忘,《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背得滾瓜爛熟,甚至還會倒著背,這讓鄭振昌欣喜異常。鄭振昌的兒子鄭雲祥生性懦弱,遇事沒有主見,不堪大任,想不到孫子鄭英魁很像爺爺鄭振昌的脾性,像是個幹大事的人,因此,鄭家大掌櫃鄭振昌對孫子鄭英魁寄予厚望。更何況,鄭家三代單傳,鄭英魁是鄭氏家族的唯一接班人,鄭振昌怎不厚愛有加?
鄭家三代單傳。要說鄭家那麼有錢,多娶幾房媳婦多生幾個孩子不是難事,怎麼會三代單傳呢?這主要是因為鄭家的家規。鄭家為了家業永存、基業長青,對後代要求很嚴,定下了家訓家規:要理學治家、勤儉持家、耕讀傳家、孝義立家,勿賭博、勿嫖娼、永勿納妾,以免家事紛爭、禍起蕭牆。這叫傳家二字耕與讀、守家二字勤與儉、傾家二字嫖與賭、防家二字盜與奸。還有,鄭家娶媳婦特別在意,常言說,娶錯一代親,禍害三代人。所以鄭家挑媳婦一定要上查三代、遍訪四鄰,還要找算命先生看看相,是否旺夫旺家,以免娶個有病的、短命的、無德的媳婦,影響下代兒孫。鄭家的家訓家規大都合情合理,唯獨這勿納妾,村裏人都覺得是有利也有弊。不納妾會避免禍起蕭牆,避免子孫後代因為爭家產而不和,但隻娶一個媳婦,畢竟人丁不旺,鄭家時時麵臨絕後的危險。鄭振昌是獨子,鄭雲祥是獨子,到了孫子輩鄭英魁,鄭家還是一個男丁。鄭振昌的老伴也去世多年了,街坊鄰居、親朋好友都勸鄭振昌再娶一房,而鄭振昌也有心把勿納妾這條祖上傳下的老規矩給改了,再找一個,但是,他是一個孝子,深知祖命難違的道理,加之他也擔心再娶一房小的,將來生兒育女,難免與兒子鄭雲祥鬧紛爭,子孫不和,說不定還會釀出大禍,所以也就斷了這個念想,隻一門心思放在照看孫子鄭英魁身上,對鄭英魁特別親。冬天天冷,鄭英魁身邊離不了火盆;夏天天熱,他親自替小孫子打扇,哪兒有涼蔭,鄭振昌就把他抱到哪兒玩。
鄭英魁生在福窩裏,從小嬌生慣養,這養成了他貪玩的脾性。鄭英魁雖說人很聰明,記性也好,卻不愛讀書,這讓鄭振昌很是頭疼。鄭振昌為鄭英魁請的私塾先生王文鏡,是方圓幾十裏有名的飽學之士,是一名老秀才,在縣衙裏當過幾年師爺,因不滿官場黑暗,辭職回鄉,專事教書育人。可是,鄭英魁經常逃學,王文鏡也無可奈何。
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是禍害,鄭振昌不是不懂這個道理,可是,每每他想嚴厲管教鄭英魁的時候,就是狠不下心、下不去手。鄭振昌經營田產家業做事果斷,可對自家孫子的管教卻無可奈何。有時候,他愁悶起來,就想起“樹大自然直”的道理,也許,孫子長大了會變過來吧。於是,他該說說該勸勸,但從不打罵鄭英魁,讓鄭英魁盡情玩耍,釋放天性。
人說三歲看大,鄭英魁打小就是個當頭兒的人。在跟村裏孩子們玩遊戲時,他總是“孩子王”,大小孩子都跟在他屁股後滴溜溜轉,聽他指揮。即使玩遊戲,也把他的名字編排進遊戲內容裏。
白天,鄭英魁領著同伴們到鄭家村北邊的邙山上用彈弓打飛鳥,用長矛捉小動物。有道是“生在蘇杭,死葬北邙”,鄭英魁和小夥伴們玩耍的邙山也叫北邙山,在黃河南岸,本是秦嶺餘脈、崤山支脈,是一座隻有三十丈高的土山。其山雖不高,但東西綿延八十裏、南北最長處三十裏,並因地處中央之山嵩嶽之下,古稱中土,控禦四方,是風水學上能結穴的龍脈所在。自東漢以來,這裏先後埋葬了二十多位皇帝,是中國埋葬帝王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如果算上皇族大臣、達官顯貴的陵墓,邙山總共有古代陵墓上千座。因此,邙山被人稱為帝王之山。明代詩人薛瑄在《北邙行》裏寫道:“北邙山上朔風生,新塚累累舊塚平。富貴至今何處是?斷碑零碎野人耕。”
邙山上紫氣環繞,植被繁茂,銀杏樹、青檀樹、桑樹、側柏、白楊樹、泡桐樹伸向雲天,野菊、艾蒿、紫藤、荊條、酸棗、連翹、蒺藜、蒼耳、鬼針草競相纏繞,難以下腳。這裏還是動物的天堂,斑鳩、鵪鶉、灰喜鵲、金翅雀、大山雀、棕頭鴉雀在枝頭棲息,畫眉、黃鸝、杜鵑、百靈在樹叢中鳴唱,野兔、石雞、山斑雞、岩鬆鼠、黃鼬、豬獾、狐狸在比人高的雜草荊棘中悄悄穿行。當然,邙山深處也有狼、熊等凶猛動物,可鄭英魁他們很聰明,從不去深山溝,隻在邙山近處玩,一玩就是一整天。
鄉村的夜晚,圓月當空,倦鳥歸巢,這是小孩子們的美好時光。鄭英魁把幾個小夥伴召集到一起玩遊戲。他們除了玩“起麒麟”之外,還玩“賣鞭杆”。十幾個小孩子手拉手,圍成圓圈,鄭英魁起頭喊道:“賣鞭杆喲!”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小孩跟著喊:“打燈郎啊!”鄭英魁接著喊:“燈郎高喲!切菜刀啊!”旁邊的小孩接著喊:“菜刀快喲!切英菜啊!”鄭英魁喊:“英菜英喲!切棵蔥啊!”旁邊的小孩喊:“蔥又辣喲!切苦瓜啊!”鄭英魁喊:“苦瓜苦喲!抓把鹽啊!”旁邊的小孩喊:“鹽又鹹喲!撲通撲通二十五啊!”鄭英魁喊:“氣蛤蟆,掛櫻桃,從您寨門過一遭,別叫掛住小耙角。”喊畢,鄭英魁和旁邊的小孩扯著手,高舉成月亮門的形狀,其他的小孩子依次從下邊彎腰鑽過,如果有一個人身上的衣服被掛住,沒有順利通過,就再開始第二輪遊戲。
玩了一會兒賣鞭杆遊戲,玩煩了,再換個遊戲,鄭英魁他們又玩起了篩麥糠。兩個小孩麵對麵站著,拉起雙手,搖著手臂,說:“篩,篩,篩麥糠,伶俐鬼兒,打冰糖,你賣胭脂我賣粉,咱倆打個琉璃滾。”說完,兩人的手不分開,卻高高舉起,倆人同時從手臂下鑽過去,背對背,繼續搖手臂、唱歌謠。
篩麥糠的遊戲玩夠了,鄭英魁又和小夥伴們玩捉迷藏。大樹背後、草叢裏邊、街坊拐角,都是藏人的地方,都是充滿驚喜和快樂的所在。一個叫狗剩的小夥伴藏起來了,鄭英魁和小夥伴四散開在村裏村外尋找狗剩,在牆角屋後、麥秸垛旁找來找去,哪兒也找不到。找了很長時間,鄭英魁已經找到村頭的洛河邊了,這時,月光下的洛河泛著銀光,流水潺潺,白霧也起來了,河岸上的柳樹朦朦朧朧,地裏的秋莊稼罩上了一層乳白色的輕紗,一切都神秘而溫馨。鄭英魁跑累了,索性站在村頭洛河邊一棵大柳樹下喊了起來:“狗剩,狗剩,你藏哪兒了?快出來!”
清脆的童音在夜色裏回蕩,突然,兩條黑影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其中一條黑影向鄭英魁撲了過來,鄭英魁嚇得剛要大喊救命,他的小嘴就被一雙大手捂住了,接著,黑影把鄭英魁拎起來,往胳膊彎一夾,不顧鄭英魁兩條小腿亂踢騰,飛一樣往遠處邙山上跑去,另一個黑影手裏掂著鋥明瓦亮的大刀,在後邊緊緊跟隨。
2
兩個黑影挾著鄭英魁鬼鬼祟祟地來到邙山深處,原來他們是附近邙山上的賊寇。那年頭,人們缺吃少穿,很多窮苦人上山落草,靠打家劫舍過活,有成群結隊的,有三兩結夥的,有長期以此為生的,也有幹幾票就金盆洗手的,還有白天下地幹活兒晚上當賊寇的。反正邙山上草深林密、溝壑縱橫,成了賊寇落草的天然所在。
鄭英魁被倆毛賊挾持到一個破窯洞裏。一個賊看管鄭英魁,另一個賊趁著夜色下山,天亮前偷偷在鄭家大門上貼了條子,言明第二天天黑前送一百兩紋銀到邙山腳那棵百年老皂角樹下,然後就放鄭英魁回家,否則就撕票。
爺爺鄭振昌和父親鄭雲祥本想著鄭英魁跟小夥伴們在村裏鬧著玩呢,可是,到了半夜,卻不見鄭英魁的蹤影,問別的小孩,都說沒見鄭英魁。鄭振昌和鄭雲祥著急了,急忙召喚全家老小打著燈籠舉著火把在村裏村外找鄭英魁。街坊鄰居聞聽鄭英魁不見了,也幫著到處找人。一時間,鄭家村到處是喊叫鄭英魁的聲音,燈籠火把點亮了村裏村外。可是,找了一夜也沒見鄭英魁的蹤影。
天剛蒙蒙亮,鄭家的一個家丁突然發現大門上貼了張紙,近前一看,原來是綁匪索要銀兩的條子,如若不送或報官,等著收屍。家丁急忙稟報給管家劉富貴,劉管家急忙找到鄭振昌和鄭雲祥。鄭振昌和鄭雲祥為找鄭英魁一夜未眠,擔驚受怕,當看到劉管家遞來的條子時,鄭振昌一顆懸著的心落了地,他拄著拐杖搗了搗地,長出一口氣說:“謝天謝地,英魁總算沒事了。”
鄭雲祥說:“爹,您老何出此言呢?分明是英魁被綁匪綁票了,是死是活,還未知呢,您這是啥意思啊?”
鄭振昌說:“兒啊,邙山上的賊寇多是窮苦人,都是被逼無奈才走這條道的,他們落草為寇圖的是錢而不是命,何況綁的是咱鄭家的獨苗苗英魁,咱鄭家在這一帶誰人不知誰人不曉?誰敢動咱鄭家一根毫毛?唉,我也後悔得很,實在是大意了,總想著咱家大業大沒人敢惹;再則說,咱從祖上始就積德行善,十裏八村的誰家有難處了,找咱借十兩八兩銀子,從沒要過賬,為的是啥?就是不得罪人,混個好人緣,圖個家業平安。這麼多年也真的沒人找咱的事,那些賊寇在邙山上盤踞,鬧得再凶,從不惹咱鄭家,可這次是咋回事?這綁匪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嗎?跟咱鄭家過不去,他們這不是找死嗎?我估計這綁匪要麼是窮瘋了,要麼是初入道不懂規矩,看他們要錢的數目,就知道他們是生手,對咱鄭家隻要一百兩銀子,可見他們要價不高,不懂行情,所以,隻要把錢送到,英魁肯定沒事。”
鄭雲祥說:“爹,人家常說,不怕會打架的,就怕不會打架的。會打架的人打起架來有分寸,知道哪兒是要命的地方,哪兒是光打不傷的地方,可是,不會打架的人,亂打一氣,反而會打出大事來。照您老說,這綁匪有可能是剛上路,怕就怕這剛上路的,不懂江湖規矩,我覺得,越是這,越是可怕。”
鄭雲祥說得也有道理,大家紛紛議論起來。
鄭振昌嘿嘿一笑,說:“沒事,這小毛賊既然剛出道,衝的就是錢,咱馬上就送錢。我覺得咱隻要把錢送到,英魁就會平安歸來。要是這毛賊不懂規矩,敢動英魁一根毫毛,我叫他全家老少一個不留,通通人頭落地。”
鄭振昌說了這番話,接著說:“劉管家,咱眼時下就準備錢,找人按指定的地方送去。走,事不宜遲,拿錢去。”
待眾人散去,鄭振昌單獨把兒子鄭雲祥和劉管家叫到一旁,說:“外邊人多嘴雜,保不準這裏邊就有賊寇的眼線,我說那番話就是給那些人聽的。說實話,我心裏跟你們一樣,也毛得很。這小毛賊估計是剛出道,越是這樣的人越可怕,他們不知輕重不知好歹,初生牛犢不怕虎啊,所以,我心裏跟你們一樣,七上八下的。不過,咱的心思可不能讓外人知道啊。人到了事上就知道了,啥人都有,真幫忙的,看笑話的,落井下石的,故意使壞的,咱不能不防啊。所以,眼下就咱爺兒們,咱好好合計合計吧。”
鄭雲祥由衷地佩服:“爹,您老就是比我技高一籌啊,想得比我深比我遠,我自愧不如啊。”
劉管家也說:“大掌櫃辦事就是周全。”
“我再能,還不是把英魁給弄丟了?唉,謹小慎微活了一輩子,到老了老了出了這麼大的事,真是該死。”
劉管家說:“大掌櫃的,您別自責了,這事主要怨我。我當管家的沒把家事料理好,沒有把英魁照看好,怨我怨我,英魁要是沒事便罷,要是真有啥閃失,您咋處理我都中。”
鄭雲祥說:“爹,錢都好說,對咱鄭家來說,錢不算啥。不過,報官不報官?”
劉管家說:“我覺得不能報。一報官,萬一傳了出去,那綁匪孤注一擲,動了殺機,英魁就沒命了。再則說,一報官,那官府趁火打劫,故意把事情鬧大,到時候,咱錢沒少出,英魁還危險。”
鄭雲祥說:“嗯,劉管家說得有道理,那就抓緊讓賬房先生拿錢去吧。”
鄭振昌沉吟了一下,意味深長地說:“你們先別慌,讓我想想。遇事不能急,這是大事,要三思而後行,不能倉促行事。要說咱鄭家出個一百兩紋銀,也是九牛一毛,別說這點錢了,即使是兩三千兩,咱也拿得出,即使咱暫時拿不出,砸鍋賣鐵也能湊。錢是人掙的,沒錢還能掙,可是,人沒了,要錢有啥用?不過,我覺得,關鍵是這頭一開,咱順順當當、老老實實把錢送去了,以後別的強盜都打起咱鄭家的主意,都覺得咱鄭家的錢好掙,那咋辦?”
鄭雲祥眉頭一皺,說:“爹,您老既然這麼想,那幹脆,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咱這次就跟這幫賊人較較勁兒,咱家家丁也不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咱收拾他個小毛賊還是沒問題的,等咱捉住了小毛賊,再報官,大張旗鼓地整整他們,殺殺他們的囂張氣焰,看他們誰還敢打咱鄭家的主意!”
鄭振昌連連擺手說:“兒啊,我老了,我是越活越膽小,你說的不是沒有道理,但是英魁在他們手上,稍有差錯,咱英魁可就危險了。咱能不能想個法子,既給這毛賊銀錢,又殺殺他們的囂張氣焰呢?”
老爺子這話一說,鄭雲祥犯了難,兩全其美的事,不好籌劃啊。
鄭振昌撚了撚花白胡須,自言自語地說:“這賊估計是剛出道,剛出道的肯定經驗不足、考慮不周,這樣,錢我們如數奉上,不過要找個有眼色的人送錢,送錢時記好路線,等錢送到,英魁一回來,咱緊跟著就派人去收拾他們。”
鄭雲祥說:“對,咱把他們抓起來,把咱的錢要回來,再把毛賊送到官府,打入大牢,遊街示眾,殺一儆百,看他們以後誰還敢找咱鄭家的事。”
鄭振昌說:“嗯,咱鄭家從來都是不惹事不怕事,既然有人找咱的事,咱就不能輕而易舉地擱那兒,不然的話,咱鄭家家大業大麵子大,以後咋活人?”
鄭雲祥說:“對,聽爹的,就這樣辦。”
劉管家也點頭稱是。
鄭振昌、鄭雲祥父子倆和劉管家合計了一陣,剛準備派人去給邙山裏的賊寇送銀子,沒承想,鄭英魁回來了。
鄭英魁還是自個兒敲門回來的。
3
這時,天已大亮,沉寂了一個晚上的鄭家村沸騰起來了,陽光穿過淡淡的晨霧灑下道道金光,雞鳴狗叫聲此起彼伏,老牛對著晴朗的天空發出“哞哞”的叫聲,街當中的幾匹馬正歡快地轉圈圈,脖子上的鈴鐺“叮當叮當”響個不停。男女老少都準備下地幹活兒了,新的一天在不安和期望中到來了。
當家丁們聽到“梆梆梆”的敲門聲,還以為是邙山裏的土匪賊寇來要錢呢,嚇得不敢開門,急忙向劉管家稟報。劉管家招呼來一群家丁,擺好架勢,悄悄地把黑漆大門拉開了個縫,往外一瞅,沒有見什麼土匪賊寇,也沒有見什麼刀光劍影,倒是少爺鄭英魁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門外。眾人嚇了一跳,這是咋回事?莫非少爺後邊還跟著土匪賊寇,要尋機闖進鄭家大院?仔細瞅瞅周圍,什麼人影也沒有。
看到門開了條縫,鄭英魁就往裏擠。劉管家緊張地問:“少爺,你是人還是鬼?”
“快讓我進來,我是英魁,啥鬼不鬼的?”鄭英魁脆生生的一句話,讓眾人放了心,肯定不是鬼,是鬼咋會說人話呢?
鄭英魁回來了,這個消息很快傳遍鄭家上下,鄭家的人都圍了過來。鄭英魁他娘趙采蓮趙夫人一夜未睡,在房子裏哭了一夜,眼睛都哭腫了,聽說鄭英魁回來了,也顧不得擦一擦臉上的淚痕,急忙跑了出來……眾人把鄭英魁圍在中間,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見鄭英魁身上一點傷都沒有,這才放了心。
趙夫人見了鄭英魁就哭,把鄭英魁緊緊抱在懷裏,生怕他飛了跑了,說:“兒啊,你去哪兒了呀?可把娘嚇死了啊。”
鄭英魁昂著頭眉毛一挑顯擺地說:“娘,我沒事。”
“啥沒事啊?不中,我得給魁叫叫魂兒。”趙夫人一手拉扯著鄭英魁的衣角,彎下腰去,另一隻手先拍拍地,然後做了個扒拉東西的動作,接著,扒拉到鄭英魁的身上,拍拍鄭英魁說:“魁,回來吧!跟娘回來吧!魁,回來吧!跟娘回來喲!”
這時,鄭振昌和鄭雲祥也來到了前院裏,鄭振昌拉著鄭英魁的手說:“魁,你咋自個兒回來了?還沒吃飯吧,走,到爺爺房裏吃飯去。”
劉管家安排飯去了。眾人簇擁著鄭英魁到了老太爺鄭振昌的房間,眾人落座後,鄭振昌說:“魁,渴了吧?”
鄭英魁點點頭。
早有丫鬟為鄭英魁倒了一碗溫溫的紅糖水遞過來,鄭英魁一飲而盡。
鄭振昌說:“魁,再來一碗?”
鄭英魁又點點頭。丫鬟又遞來一碗紅糖水,鄭英魁接過後又喝了個幹幹淨淨。
鄭振昌歎了口氣:“唉,魁受大罪了,打小哪兒恁渴過啊。魁,餓了吧?”
鄭英魁點點頭。鄭振昌吩咐快上飯。不一會兒,丫鬟端來了一碗熱騰騰的荷包蛋,足有五六個,還有一碟芥菜絲,小磨油的香味登時飄滿了房間。
鄭英魁端起碗三下五除二就把荷包蛋吃了個精光,吃完後,還吸溜了兩口湯汁,用舌頭舔了舔碗沿,把碗轉來轉去舔了舔,這才把碗遞給丫鬟,揉搓揉搓肚子,滿意地長出一口氣。
趙夫人見此情景,眼淚流了出來:“可憐的兒啊,看看餓成啥啦,受大罪了啊。”
鄭雲祥說:“魁,給你爺爺說說你咋回來的,這一天一夜都去哪兒了?”
鄭英魁這才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4
原來,鄭英魁是被一高一矮兩個瘦得麻稈似的土匪綁走的。這倆土匪其實也是河洛縣當地人,都是光棍漢,窮得叮當響,吃了上頓沒下頓,倆人一合計,與其餓死,還不如冒一回險搶點兒東西吃,即使被人刀砍斧劈,混個肚圓去見閻王,也落個舒坦。不過,倆人手無縛雞之力,想搶想劫也幹不過人家,於是,倆人一合計,還是綁票來得穩當,綁個小孩子最省事。倆人掰著指頭數了半天,河洛縣有錢人不算多,鄭振昌算一個,要是能把鄭振昌家的獨苗鄭英魁給綁走,也不向鄭家要太多的錢,弄個一百兩銀子,對鄭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可對他倆來說,就已經不少了。不過,他倆也知道,鄭家防範很嚴,家丁也不少,想綁鄭家的票也不是恁容易。他倆圍著鄭家轉了倆月,終於發現,別看鄭家防範很嚴,其實,也不是無懈可擊,鄭英魁好玩兒,瘋得到處跑,他家人也不管他,任由他滿大街亂竄,尤其是晚上,鄭英魁還常跟小夥伴兒們一起捉迷藏,哪兒黑往哪兒鑽,這不是天賜良機嗎?於是,倆土匪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鄭英魁綁走了。
倆土匪把鄭英魁帶到一個破窯洞後,不給他吃不給他喝,其實,這倆土匪也沒吃沒喝的。倆土匪又合計了一下,高個兒土匪找鄭家送信要錢,矮個兒土匪負責看管鄭英魁。
高個兒土匪下山送信要錢的時候,矮個兒土匪閑來無事,找了半截磚當枕頭,拾了些幹草鋪在地上,往上邊一躺,蹺著腿一晃一晃,逗鄭英魁玩兒。可是,問鄭英魁什麼話,鄭英魁就是不搭腔。矮個兒土匪惱了,就罵鄭英魁,還嚇唬他,說要弄死他。可是,鄭英魁跟沒事人似的,一點兒不害怕。矮個兒土匪奇了怪了,想想也是,從綁走這小兔崽子之後,這小兔崽子的嘴巴就沒有張開過,既不哭也不叫,就跟個啞巴似的,真能沉得住氣。
矮個兒土匪說啥,鄭英魁都不吱聲,這讓矮個兒土匪很是生氣,自尊心很受傷,他忍無可忍,對鄭英魁拳打腳踢。可是,任憑他怎麼打,鄭英魁都不哭也不吭,比啞巴還啞巴。啞巴最起碼會“噢噢”叫,可鄭英魁就是閉嘴不吭。
矮個兒土匪泄氣了,害怕了,這是啥人哪?這麼小的孩子,遇到事這麼沉得住氣,而且倆眼珠子滴溜溜轉,那眼睛像刀子一樣會殺人。矮個兒土匪外表很張狂,內心倒先怯了。叫狗不咬,人狠話少,這小孩兒不是人哪,他是神,是鬼,惹不起,長大後不定是個啥東西咧。他還是鄭家的獨苗苗,要是得罪了他,鄭家會善罷甘休嗎?等這小兔崽子長大了,他會不記仇嗎?
想到此,矮個兒土匪歎了口氣,看這陣勢,鄭家真不是好對付的,連一個小孩都這麼霸氣,這事很可能是吃不了兜著走。想到此,看守鄭英魁的矮個兒土匪不敢怠慢,把鄭英魁用黑布蒙了眼,用繩子綁緊鄭英魁的雙手,然後牽著鄭英魁下山。他要找到在山下的高個兒土匪,把鄭英魁給放了。
高個兒土匪見矮個兒土匪牽著鄭英魁跌跌撞撞地來了,大吃一驚:“老弟,咋回事?我沒給你吱聲,你下山弄啥?”
矮個兒土匪說:“哥,咱剛起事兒幹這麼一大票,我心裏慌。”
高個兒土匪說:“看你那熊樣,慌啥慌?餓死也是死,打死也是死,反正都是個死,闖一闖說不定還死不了呢,幹一票就是死了最起碼還落個肚圓,填飽肚子再死總比餓死強。”
矮個兒土匪說:“哥,我害怕。”
高個兒土匪說:“看你這婆婆媽媽的,就不像那弄事的人。”
矮個兒土匪說:“可不是咧,我算是知道了,孬人學好難,好人學孬也難著咧,咱就不是那幹孬事的人。”
“那你想咋辦?”
“咱這回起票起錯了。”
“咋錯了?眼下說這有啥用?開弓沒有回頭箭,吐到地上的唾沫還能自個兒舔起來?”
“哥,該舔還真得舔啊。老鄭家有錢有勢,誰敢惹?老鄭家還處處行好,方圓十幾裏落得名聲不賴,起票的人都不起老鄭家的,咱倆剛上路就起老鄭家的票,咱不該啊!”
“咱就是剛起事才拿老鄭家下手咧,要不咋打出名聲?咋招兵買馬?”
“算了吧哥,咱不是那塊料,咱還是當個老實莊稼人吧,實在不中,咱要飯去!”
“看你那膽兒,咱惹不起老鄭家不也把他家的獨苗苗綁過來了嗎?兄弟,等著發財吧,咱幹這一回,夠咱回家吃幾年了。往後咱金盆洗手,再也不這渾水了。”
“哥,不中啊,那老鄭家會饒了咱嗎?說不定眼下正組織人馬收拾咱咧。”矮個兒土匪往身旁一棵小槐樹上跺了一腳,小槐樹“哢嚓”斷了,“哥,我後悔了。”
“後悔啥?咱把老鄭家的獨苗苗一綁,就沒有回頭路了,隻有往前走,是懸崖也得往下跳,是火坑也得往裏鑽。”
“幹脆把老鄭家這個小兔崽子給放了。”
“放了?你餓暈了吧?咱踩點兒忙活恁多天是圖啥咧?”
“瞎忙唄!沒事幹,權當練練手,玩兒咧。”
“玩這?這不是拿腦袋瓢開玩笑?咱不是說好了嗎,你咋又變卦了?”
“不是我變卦,是我害怕。”
“看你那膽量,跟老鼠一樣,就這還想上山當綠林好漢咧!”
“不是,哥,你看老鄭家那小子,太嚇人啦。”
“一個小毛孩兒,有啥嚇人的?”
“咱從弄住他到現在,他一句話也不說,一聲也不哭,這不是人哪,我看見他就害怕。”
“真咧?”
“可不是真咧!”
“我試試。”高個兒土匪看看鄭英魁,鄭英魁被黑布蒙著眼,反綁著雙手,繩子上挽了個結,繩的另一頭被矮個兒土匪係在手腕上。他不卑不亢地站著,還是一聲不吭。
高個兒土匪來到鄭英魁跟前,說:“你是個啞巴?”
鄭英魁不吭聲,高個兒土匪對著鄭英魁就是一巴掌,把鄭英魁打倒在地,高個兒土匪緊接著上去又是一腳,把鄭英魁踢得在地上打了兩個滾,牽繩子的矮個兒土匪也不由得跟著往前躥了兩步。可是,鄭英魁還是一聲不吭。
“真咧,真不吭聲啊,是個啞巴。”
矮個兒土匪說:“哥,他不是啞巴,啞巴會哭啊,他連哭也不會。”
高個兒土匪說:“貴人語少,貧子話多。我今兒算真長見識了,這小孩真是奇人,跟別的小孩真不一樣。兄弟,過來,我跟你說。”
高個兒土匪拉著矮個兒土匪到了遠處,倆人一嘀咕,也不管鄭英魁了,悄悄溜了。
鄭英魁聽不到土匪說話了,等了半天也沒人吭聲,鄭英魁心裏一喜,莫不是倆土匪跑了?
這時,隻聽遠處山風在呼嘯,夾雜著餓狼的“嗷嗷”叫聲,還有貓頭鷹的“嗚哇”聲,夜涼如水,樹影森森,幾隻山雀匆忙飛到山林深處,那“嘎嘎”的叫聲在寂靜的山野上更顯清脆。
鄭英魁躺在冰涼的地上,又冷又餓,渾身疼痛,他下意識地挪了挪身子,卻碰到一塊兒又尖又硬的石頭,硌得他傷口更疼了,可是他顧不得疼,顧不得冷,顧不得餓,還是保命要緊。他把反綁雙手的繩子在尖石頭上磨,磨呀磨,也不知磨了多長時間,終於把繩子磨斷了。鄭英魁甩了甩僵硬的手,還能動,扯掉了蒙在眼上的黑布,看看四周,倆土匪沒了蹤影。他見勢趕快爬起來,也不知路在何方,隻有順著山坡往下跑,一直跑啊走啊,深一腳淺一腳的,也不敢停留。
沉靜而柔和的月亮在天上緩緩移動,陪伴著匆匆而行的少年鄭英魁。蒼茫的群山披上了乳白色的麵紗,山路兩邊的樹木婆娑斑駁,就像一頭頭怪獸。這時,一群小鳥突然從樹上驚起,身後一陣“窸窣”的響聲,夜風吹動腳下的野草,傳出陣陣土腥味,鄭英魁渾身打了個冷戰,不由自主地止住了腳步。回頭一看,兩隻狼不知什麼時候跟在他身後,眼睛發出幽幽的綠光,在月光下分外瘮人。
鄭英魁剛要喊叫,突然間,他想到了爺爺鄭振昌曾給他講過的對付山間野狼的絕招,爺爺曾對他說:“魁,遇到野狼,別叫,別慌,站那兒別動,把衣服解開,看著它,和它對著瞧。”
鄭英魁迅速解開上衣扣子,把衣服伸開,突然間身軀像是變大了,就這樣看著狼,狼也站在了原地,看著小小的鄭英魁。
月光明亮,山野靜寂,鄭英魁和狼對峙了約莫半個時辰,兩隻狼還是一動不動,這時,鄭英魁又好像聽見爺爺在說:“魁,山路上都是石頭,彎腰撿幾塊兒石頭,狼看見你彎腰摸石頭,說不定就嚇跑了。狼要是不跑,就脫下上衣把石頭包上,圍著脖子纏一圈,狼咬人,先咬脖子,咬脖子最要命,先護好脖子再說,手裏再拿塊兒石頭,要是狼撲過來,就砸它的眼睛和嘴。”
想到這裏,鄭英魁慢慢地彎下腰,眼睛卻盯著狼,一點兒不敢分心,他從地上隨手摸了幾塊兒小石頭,脫下上衣,把石頭放到上衣裏包好,然後把上衣纏在脖子上。接著,又慢慢彎腰,從山路上摸到一塊大石頭,拿在手中,輕輕站了起來。
沒想到,在鄭英魁彎腰摸石頭的過程中,兩隻狼掉頭跑掉了。
鄭英魁長出了一口氣,再摸摸衣服,渾身都濕透了……鄭英魁加快了下山的腳步。
到了天快亮的時候,終於下了山,碰到一個早起打豬草的老大爺,問了路,鄭英魁這才摸回了家。
5
聽完鄭英魁的講述,趙夫人嚇哭了,她急忙脫掉鄭英魁身上的臟衣服,隻見鄭英魁身上青一塊紫一塊,趙夫人號啕大哭起來:“那千刀萬剮的賊子,看把我兒打成啥啦?我非捉住撕碎他們不可?魁兒,疼嗎?”
鄭英魁搖搖頭。
鄭振昌走上前,仔細瞧了瞧傷,又敲了敲鄭英魁身上的骨頭,問鄭英魁疼不疼,鄭英魁又搖搖頭。鄭振昌說:“不礙事,隻要不傷筋動骨,隻傷點皮肉,用草藥敷幾天就好了。”
眾人都散了,鄭振昌讓鄭英魁躺他屋裏床上歇息一會兒。不一會兒,鄭英魁就呼呼進入夢鄉。
鄭振昌招呼鄭雲祥來到客廳,鄭振昌說:“魁回來了,你說這事咋辦?”
鄭雲祥說:“爹,雖說魁兒回來了,可是,那倆小毛賊咱可不能饒了他,咱鄭家哪受過這窩囊氣?不收拾他們,我這心裏難受。再則說,要是不收拾他們,以後還有別的毛賊找咱的事,開這個壞頭,咱以後可沒有安生日子過了。”
鄭振昌沉吟了片刻,拄著拐杖說:“雲祥,市麵上的事兒,都有好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魁遭此大難,是個壞事,但也有好的一麵,咱要把這壞事變成好事。”
鄭雲祥一臉茫然:“爹,變成好事?咋變?”
“這事呢,雖說魁有難,可我高興,魁這麼小就有膽有謀,長大後定然是個大弄家,咱鄭家後繼有人了。我敢說,等魁長大了,魁的本事隻在你我之上,不在你我之下,說不定,到了魁手裏,咱鄭家會成為最興盛的一代,所以說,我高興,高興。”
“爹,魁兒有恁大本事?”
“有哇,每逢大事必靜氣,你看魁,遇到恁大的事,一點不慌,這是幹大事的人的樣子啊。一個小孩,硬是把小毛賊嚇跑了,你說,這魁是人嗎?不是人哪,那是神鬼托生的人哪。魁是生在咱鄭家,要是生在帝王家,那恐怕是一代明君,不比秦皇漢武,也比得上宋太祖明太祖了。”
鄭雲祥聽到這裏,小心地看看門外,低聲說:“爹,您是老糊塗了吧?您咋敢說這大逆不道的話?這可是殺頭的罪啊。”
“哈哈哈哈,雲祥,我說話是放肆了些,可這都是實話。不過,隻咱爺兒倆在這兒瞎說,出了門那是不敢胡言亂語的。”
“是咧,爹,因言獲罪的事兒多了去了。”
“我說要把壞事變成好事,一則是以後更要在魁身上花些時間和精力,把他培養好;二則是咱鄭家以後要加強防範。今天的事,是不幸中的萬幸,不過倒也提醒了咱,看來咱鄭家還是範防不夠,還是有漏洞。咱要趕緊在村口和田間地頭都搭個庵子,日夜派人防守,再把通往鄭家村的大路挖個深溝,搭上跳板,有行人經過,必須經過防守的人同意,放下跳板才能過,這樣,咱鄭家防範更加嚴密了,你說這不是壞事變成好事了嗎?”
“爹說得很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啥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不過,那倆小毛賊咋弄?”
“不管他們了。”
“不管他們,那也忒便宜他們了吧?”
“雲祥,得饒人處且饒人。我說過,這倆小毛賊不像孬人,其實也是窮苦人。常言說,禮義生於富足,盜賊出於貧窮,窮極生孬法兒。這倆小毛賊若非缺衣少食、為生活所迫,絕不會幹這種起票的事情。可到底他們還不是真孬,這不,他們折騰了半天,還把咱魁給放了。咱要是窮追不舍,非要報官把他倆捉住倒也不難,隻是於心不忍哪。更何況,要是官府把他倆給砍了,以後咱再遇到起票的,人家恐怕說啥也不會放咱的人了,既然是死路一條,他們何必跟咱客氣咧?”
“這倆毛賊也真是的,要是真的沒吃沒喝的了,到咱鄭家門上,哭哭窮,給他們幾兩銀子不得了,咱鄭家給窮人的錢還少嗎?這倆毛賊,你說你們這是圖啥咧,沒打著狐狸反落一身騷。”
“雲祥,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稀罕事多了去了。”
“爹,這事想想也可氣。俺鄭家多少輩兒勤儉創業,有今天也不容易,憑啥你們窮就得搶我們?還要綁我們的票,真是天理不容。”
鄭振昌說:“雲祥,你恁大個人了,咋還沒活明白咧?你就是整天死讀書把腦子讀死了,你翻翻曆史書看看,哪朝哪代窮人造反不是先拿大戶開刀的?不都是殺大戶分田地的嗎?打著均貧富的旗號,把富戶的錢分了,才有軍糧;把大戶家的地分了,才有人跟著他造反。這倆小毛賊隻是個小弄家,大小弄家的想法其實都是一樣的。有錢就招災,為啥我一直交代咱鄭家老老少少對窮人要好些呢?”
鄭雲祥說:“爹說的有道理,我懂了。反正這倆毛賊也沒把魁兒怎麼樣,無非魁兒受些驚嚇,受些皮肉之苦,不過,小孩子家經曆些事也不是啥壞事,吃一塹長一智,對以後有好處。既然爹是這個意思,這事就到此為止吧。”
“對。忠厚傳家世,子賢福祿長啊。”鄭振昌說。
6
鄭英魁生在錦衣玉食之家,祖先的榮光照亮了他的前程,他隻需恪守本分,不嫖不賭不鋪張,自可度過衣食無憂的一生,所以他調皮搗蛋,貪玩好耍,胸無大誌。經過邙山遭匪這件事之後,鄭英魁發生了很大變化。他變得話少了,鬼點子好像也沒有了。
一天,午後的陽光正烈,鄭英魁手持蒲扇遮著頭,走在從家到鄭記客棧的路上,見路邊一棵老槐樹下有兩個木匠在拉大鋸。拉上鋸的站在圓木上彎腰弓背,拉下鋸的站在地上昂首挺胸,鋒利的鋸齒順著一道筆直的墨線“刺啦刺啦”遊走,雪白的木屑紛紛飄落。兩個木匠邊拉鋸邊說話,正說他鄭英魁呢。鄭英魁聽到倆木匠說他的名字,便躲到老槐樹後,支棱著耳朵聽這倆木匠在說他啥。兩個木匠拉大鋸的“刺啦”聲很響,他們沒有覺察到鄭英魁就在身旁。隻聽一個木匠說:“兄弟,老鄭家的小少爺鄭英魁被土匪綁票這事你知道吧?”另一個木匠說:“這事誰不知道?老鄭家就這一棵獨苗苗,金貴著咧,那是老鄭家將來的大掌櫃咧,老鄭家家業咋樣可全看他了,他要是有個萬一,老鄭家就完了。”“嗨!這小子我看哪,長大後不是人才,就是匪才。不是主貴,就是主賤。”“老哥你可說對了,老鄭家小少爺是個材料,爹娘都是有大本事的人,生個孩子會差嗎?你看他遇到土匪不急不慌,硬是把土匪給嚇走,那可不簡單。不過,他家可是太有錢了,有錢也不一定是啥好事,弄不好,老鄭家金山銀山反而會害了他,招災啊。”“兄弟,老鄭家厲害恁多代了,富裕好幾代了吧?”“那是,從他祖上在黃河邊開客棧發財算起,富裕九代了。”“老鄭家是富不少代了。老輩人都說富不過三代,誰人做得千年主?轉眼流傳八百家,可他家已經富九代了,夠厲害了,不過,到鄭英魁這一代,可真說不準了。”“是啊,真說不準了,還是老哥你說得對,鄭英魁長大後哇,不是個人才就是個匪才,不是主貴就是主賤。”
鄭英魁聽了倆木匠的這番話,愣在了原地,好長時間才回過神來,自此他才明白,他鄭英魁在鄭家的地位如此重要,責任如此重大,他才明白街坊鄰居都在看著他呢,他的一舉一動時刻牽動著大家夥兒的神經。他清醒了,不,確切地說,他是警醒了,他終於迷瞪過來了。他也不去客棧了,躡手躡腳地掉轉頭,等離開倆木匠有一段距離了,撒開腿向私塾跑去。
從此,每天天不亮,鄭英魁就伴著滿大街的雞鳴狗叫聲到私塾讀書習字,他還讓老師王文鏡把私塾門從外反鎖上,除了吃飯睡覺上茅廁,他絕不出門。他還在鄭家私塾門口手書一副對聯:“雙手捧起千江水,難洗今日滿麵羞。”私塾中堂則掛著一幅孔子行教圖,兩邊的對聯寫的是:“觀古知今思進退,讀書養誌識春秋。”
以前,鄭英魁看著孔子的畫像,總覺得這個長胡子老頭,穿著那麼肥大的衣服,還兩手抱拳,做出一副樂嗬嗬的樣子,挺可笑的。他想,讀個破書有啥用呢?經過劫難之後,鄭英魁看到孔子畫像,再也不敢有輕薄之態了。人常說,小孩無病不成人,不經事長不大,說的可能就是這個道理吧。
鄭英魁的小心思發生了重大變化,他懂得了創業難守業更難的道理,他也知道,不能躺在祖宗的功勞簿上度此一生。他必須延續先祖的榮光,用超出先祖的毅力和智慧,壯大鄭家基業。
眼看著鄭英魁懂事不少,開始專心讀書了,鄭振昌和鄭雲祥看在眼裏喜在眉梢。為了支持鄭英魁讀書,他們想了不少辦法,甚至出資把鄭家的茅坑也改造了一番,即使如廁也不耽誤讀書,真正做到了古人說的“枕上、馬上、廁上”的讀書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