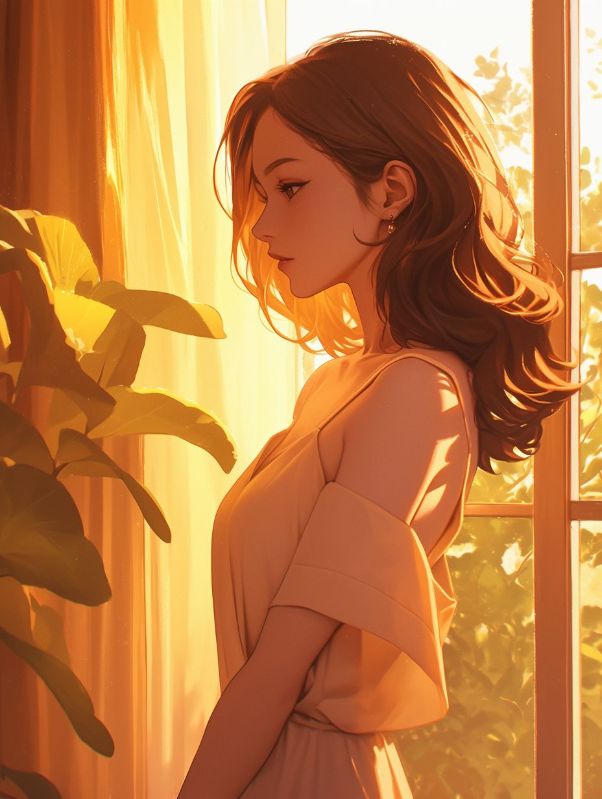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7
“我調查清楚了,是西澤他先騙了你,他那時年輕氣盛,裝窮跟人打賭,又讓你生了個有他們家族遺傳病的女兒。”
“謝枝姐,這些年,你受苦了。”
不知道為什麼,謝枝鼻子莫名發酸。
眼睛竟也有一瞬落淚的衝動。
“但裴西澤這些年更苦。”蘇嫋嫋接著道。
“為了你,他住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為了你用那種劣質的牌子,穿那麼粗糙的衣服......我都不敢想象他裝的有多辛苦。”
“苦?”
原來,跟她過日子,是一件讓裴西澤這麼辛苦的事嗎?
是嗎?
謝枝過了很久都沒想清楚,但頭上的血順著不再年輕的臉流淌下來,她吮了一下淌下的血。
血是苦的。
但之後的日子有太多比這更苦。
比如她以離開裴西澤為代價,跪下來收下蘇嫋嫋施舍的錢。
比如收到裴西澤跟蘇嫋嫋舉辦世紀婚禮的消息。
比如她的女兒好不容易有了錢進行手術,卻在術後三天因為器官排異,死了。
女兒死的時候,裴西澤不在身邊。
直到死後的第二天。
當她捧著一盒小小的骨灰走出醫院時,外麵已經是大雨磅礴。
“枝枝?”
一個直到女兒死亡,所有電話都打不通的聲音傳來。
那人上前,把手中的傘遞給她,“下著雨,怎麼還往外跑?瑤瑤呢,她最近身體怎麼樣,有沒有說想爸爸?”
雨很大,冷意直灌。
裴西澤似乎是想將她攬入懷裏,卻最終伸手隻是為她撐起手中的傘。
見她半晌不答,他蹙了眉,低聲地歎息,“枝枝,再等我幾天,再等我幾天......一切都好了。”
字裏行間,是幾乎要溢出的苦衷。
仿佛不是人格分裂,是另有隱情,謝枝看得懂。
或許這就是最紮心的地方。
她抬眸,怔怔地看了他一會兒,“裴西澤。”
“枝枝?”
“我們的女兒死了。”謝枝突然用最冷靜的聲音,說最瘋癲的話。
“在你沒接電話,我卡裏的錢也被人花光了的時候。”
“那時手術本來已經成功了,卻又出現了排異反應。
想活命就得接著治,卻沒手術費,於是她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我磕頭求漫天神佛救救我的女兒,卻沒有人理我。他們給我唯一的一條路,就是送她最後一程,你說我該答應嗎?”
她說的語無倫次,表情卻冷靜。
天空在這時閃過一道閃電。
半秒後,雷聲轟頂,雨聲磅礴。
裴西澤手中的傘哐的一下落地。
雨露了兩人全身,裴西澤卻怔怔地看她。
原來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受到巨大衝擊時,震驚後的第一秒是什麼都說不出來的。
她看到無數的水光從裴西澤麵上落下,雷聲轟鳴,已經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淚水。
但她已經感受到了口中的鹹味。
然後她突然在鋪天蓋地的鹹味中笑了一下,笑容如同他們剛結婚時一樣璀璨,“騙你的。”
裴西澤重重地喘著氣,半天說不出話。
半晌後,他才苦笑:“枝枝,你嚇到我了。”
謝枝麵無表情地移開頭,連冷笑的力氣都沒有。
她的女兒已經死了。
是非對錯,刨根究底,沒有意義了。
而她現在要做的......
第二天,謝枝退掉了出租屋,把所有東西都打包好丟掉。
捧著女兒的骨灰,她去了海邊。
好巧,裴西澤和蘇嫋嫋的訂婚,也在這座城市唯一的海畔舉行。
一隻腳跨過海邊的欄杆,她甚至能遠遠地聽見,隔壁教堂傳來的誓詞聲。
神父在問:“裴西澤先生,你是否願意娶蘇嫋嫋女士為妻,無論......”
她能想象到,他會用那副深情款款的嗓音,說出那三個字:
“我願意。”
就像多年前,他在那個破舊的民政局裏,對她說過的一樣。
海風吹起她的長發,裙擺在風中作響。
謝枝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張瑤瑤畫的畫。
畫上是三個人,爸爸、媽媽,和瑤瑤。
手牽著手,站在一座大房子前,天上掛著彩虹。
這是女兒留給她唯一的遺物。
她將畫緊緊貼在胸口,痛得她幾乎喘不過氣。
她低頭,看著腳下翻湧著白色泡沫的深藍色大海。
這裏真美啊。
瑤瑤生前最喜歡海和天空,她曾拉著媽媽的手,說如果有來生,她想當一條魚,做一隻鳥。
可媽媽沒用,她沒能力帶瑤瑤飛上天空,那麼,就一起沉入海底吧。
生生死死,她永遠當她的媽媽。
教堂裏,似乎爆發出一陣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裴西澤大概正在親吻他的新娘。
謝枝最後看了一眼教堂,臉上露出了一個解脫的微笑。
“瑤瑤。”她輕聲呢喃,像是在哄女兒睡覺。
“別怕,媽媽來陪你了。”
說完,她張開雙臂,像一隻疲倦的飛鳥。
向著那片無垠的蔚藍......
縱身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