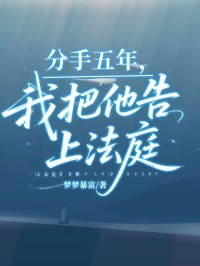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三章
婚禮前一天,沈聿約我去了我們曾經的大學。
五年了,這裏幾乎沒什麼變化。
夕陽下,操場上還有穿著校服的學弟學妹在追逐打鬧,充滿了青春的氣息。
我們並肩走在林蔭道上,誰都沒有說話。
「為什麼是這裏?」我先開了口。
「你忘了嗎?」他停下腳步,看著我,「你在這裏,第一次答應跟我交往。」
我愣了一下,記憶的閘門被緩緩拉開。
那時候的沈聿,還是個意氣風發的法學院學長,而我,隻是個剛入學的菜鳥。
他對我一見鐘情,追了我整整一年。
在同一個地方,他抱著吉他,為我唱了一整晚的情歌。
最後我被他纏得沒辦法,才紅著臉點了點頭。
往事如煙,卻又曆曆在目。
「記得,」我淡淡地說,「也記得我們是在哪裏分手的。」
他的臉色沉了下來。
「江馳,我們非要這樣嗎?」
「哪樣?」我轉頭看他,夕陽的餘暉灑在他俊朗的側臉上,柔化了他冷硬的線條。
有那麼一瞬間,我幾乎以為我們回到了過去。
「明明是在互相折磨,卻要裝作情深不悔。」
他自嘲地笑了笑。
「你不是一直想嫁給我嗎?我成全你。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沈聿,」我看著他的眼睛,認真地問,「你愛過林晚嗎?」
他避開了我的視線。
「她是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也是最適合我的妻子。」
「所以,是適合,不是愛。」
我替他總結。
「那你呢?」他忽然反問,「你這麼處心積慮地回到我身邊,是因為還愛我嗎?」
我沉默了。
愛?
這個字,對我來說,太奢侈,也太諷刺。
「你覺得呢?」我把問題拋了回去。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複雜難辨。
「我不知道。」
「但我會讓你親口告訴我答案。」
他拉起我的手,走向操場的中央。
那裏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擺好了一架鋼琴。
「彈一首吧,」他說,「就像以前一樣。」
我甩開他的手。
「我不會彈了。」
五年前那場事故後,我的右手神經受損,再也無法彈奏複雜的曲子。
這是他親手造成的。
他似乎也想起了什麼,眼中閃過一絲愧疚,但稍縱即逝。
「江馳,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無比可笑。
重新開始?
他憑什麼覺得,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沈聿,你是不是以為,你為我頂了罪,我就該對你感恩戴德,一輩子做你身邊的附屬品?」
「你是不是以為,你毀了我的手,毀了我的事業,再給我一場虛假的婚禮,就能抵消一切?」
我的聲音越來越大,帶著壓抑了五年的憤怒和不甘。
「你錯了。」
「我回來,不是為了重新開始。」
「我是回來,拿回本該屬於我的一切。」
「包括你的命。」
他怔怔地看著我,仿佛第一天認識我。
夜幕降臨,冷風吹過,我卻感覺不到絲毫寒意。
因為我的心,早已在五年前那個雨夜,徹底凍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