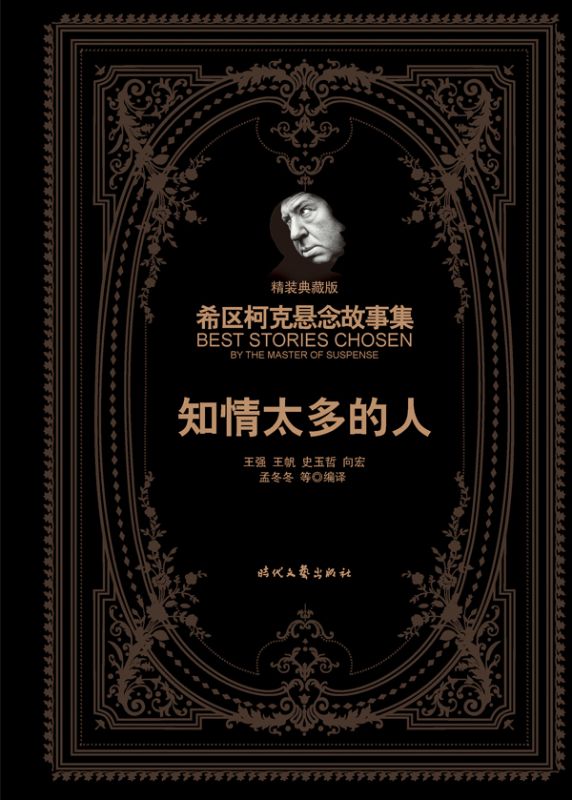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特別債券
赫伯站在門邊,一隻小小瘦瘦的手抓住圓頂高帽和一把折傘,另一隻手擱在半開半閉的門把手上。
“我走了,媽媽。”赫伯對著寧靜的清晨喊道。
“祝你有個愉快的日子!”從後麵臥室中傳出來的聲音甜甜的,但是沒有精神,“你今晚不會遲到吧,孩子?”
“不會的,媽媽。”
“7點鐘,是嗎?”
“7點鐘。”他心不在焉地回答著,眼睛掃過起居室,心裏不覺一動,他想:我將會懷念這一切。
他看看優雅的家具,紅木櫥子,裏麵裝著他母親辛勤收集的瓷器,房角有個小飾物架,裝著各色各樣的小玩意兒。
這個房間——一度頗值得驕傲的房間,每一件家具在晨光中都會閃耀發光。如今,每件東西都褪色,破舊,疲憊不堪,甚至他母親似乎也和這些家具一樣。自從1929年生意慘敗、她又成為寡婦之後,她一直在工作,因為赫伯的薪水菲薄,所以她從沒有舍棄那份工作。
他輕聲對那個剛剛閃進廚房身披法蘭絨袍子的人影道別,等候熟悉的“再見”聲後,再隨手關上門。
赫伯進入電梯,按“1”字的鈕。這部呻吟著的老爺電梯,瘡痍滿目,按鈕上全是年輕人的名字,唯獨沒有他的名字,想到這點,不禁有些傷感。在四十年的歲月中,他有三十年是居住在這幢公寓裏的,但一直沒有勇氣在鏽跡斑斑的電梯裏刻上自己名字的縮寫。他摸摸掛在胸前那隻懷表末端的金刀子,心中有一股衝動,但是天生的膽怯和遵守秩序的習慣,使他將手從背心口袋中挪出——空手伸出來。他歎了口氣,永遠沒有機會了。
赫伯是個一絲不苟、拘泥於形式、生活規律而單調的人。這天,當他步入清晨的陽光中,計劃在日落前偷竊五十萬元時,他也隻給自己一個秘密的微笑。
這天上午和平時一樣,赫伯坐在第三節車廂的後麵,他的《紐約時報》整整齊齊地折疊成四分之一大,試著用近視的雙眼閱讀新聞。
到華爾街站的時候,赫伯和許多身穿黑色西裝、頭戴圓頂禮帽、手拿雨傘的人一起下車。他步行一小段路,進入一座灰色的大廈,進去的時候,向門口的保安點點頭,再乘電梯上到十七層,走出電梯,在一扇玻璃不透明的門前站了好一會兒。那扇門上刻著:
“泰波父子公司,創立於1848年,紐約證券交易公會會員。”
他順著一條通道走過去,推開一道欄杆的門,看都不看用粉筆記載著前一天各公司股票行情的黑板,徑直進入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裏麵有六張辦公桌,鑲著玻璃的檔案櫃,一道牆邊有一個像籠子一樣的窗戶。赫伯的辦公桌和其他人分開著,以表明他在公司做了二十三年的資曆。
9點鐘左右,其他的辦公桌都有了人。高高的、憔悴的比利,草率地和赫伯點個頭,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資曆隻少赫伯兩年。芬黛小姐是個相當有才幹的年輕女人,30歲,當她撲撲粉後,在桌子後麵坐下來,她的座位在一扇通往副經理辦公室的橡木門邊。接下來是兩位低級職員,最後進來的是勞倫斯,他是副經理妹妹的兒子。
勞倫斯剛進來,他舅舅就從裏麵的辦公室出來,檢查考勤。他對大家準時到達感到很高興,然後向芬黛小姐點頭讓她進去。
10點30分,芬黛小姐從泰波副經理辦公室走出來,泰波隨後走出來,來到赫伯的桌邊。
“早晨好,赫伯!”他假模假式地說,“一切都好嗎?”
“很好,泰波先生。”赫伯回答。
“今天是星期五,特種債券下午送到,由你負責。那都是可以流通的債券,我們要存到樓下的倉庫裏。”
赫伯點點頭。突然勞倫斯走到副經理的身旁。
“舅舅,”勞倫斯說,“我也來幹吧。”
泰波問赫伯:“你覺得怎麼樣?”
赫伯可不想再要一個人插進來,他說:“我想我一個人就行了。”
“很好。”泰波說。
勞倫斯回到了他自己的座位。
泰波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赫伯看看整個辦公室,看到沒有人注意到他,便拿起電話,打了三個電話。第一個是給他母親的,第二個是約人在一個自助餐廳見麵的,第三個是打給樓下房地產公司的。
放下電話後,他拉開辦公桌中間的抽屜,拿出一遝空白收據,這是他上個月從一家運輸公司弄來的,這個公司下午又要送債券來。
赫伯開始在空白收據上填寫。中午時,赫伯差不多填寫完了那些假收據,把它們又放回中間的抽屜鎖上,然後穿上外套,戴上帽子。
他下電梯,走到街上,快步走過五條街,走到一家小自助餐館,他選了幾樣食物,端著盤子來到兩個男人身旁。兩個男人一個很瘦小,一個很魁梧。
赫伯稱他們為斯通先生和布朗先生,他們是黑社會外圈的人物,赫伯花了三個星期在紐約的酒吧裏找到的。
吃午飯的時候,赫伯解釋了叫他們來的原因,當他提到金錢的數目時,那兩個人吃驚地互相望望。
赫伯說:“不管怎麼說,這事情沒有一點危險,計劃得非常周密。”他探過身,說出了他的計劃。
計劃裏最重要的是時間。赫伯知道,同事們在星期五總是提前下班,所以要斯通和布朗到樓下房地產公司假裝談業務,然後從防火樓梯離開。芬黛小姐總是在下班前五分鐘到洗手間化妝,搶劫要在她不在的那一刻進行。
計劃很簡單,當赫伯帶著債券進入副經理辦公室時,斯通和布朗要跟進去,拔出手槍,搶過債券,打昏副經理,為了掩人耳目,他們也要打赫伯,不過赫伯警告他們說:“絕對不許傷人。”
斯通問:“如果那個叫芬黛的女人回來得早,那我們就麻煩了。”
“是啊,”布朗說,“如果封鎖全樓,進行搜身,他們就會找到債券。”
“不,他們不會找到。”赫伯勝利地宣布道,“因為你們身上沒有債券。”
兩個歹徒揚起眉毛。
“那是最後的一個細節,”他示意兩個人靠近些,“現在你們聽仔細了,當你們搶到東西之後,在離開時,把兩卷債券扔進廢紙簍裏,我會在桌子上留一些廢紙,你們可以順手一掃,蓋住債券,然後你們從防火樓梯出去,摘掉麵罩,乘電梯下樓。”
布朗說:“那麼就是警鈴響了我們也沒事,對不對?”
“對。”
“不見得,”斯通說,“債券怎麼送出大廈?”
“簡單得很。警方會問我話,當然會發現我是無辜的。當他們離開後,我就從紙簍中取出債券,放進手提箱,離開。”他很驕傲地說。
“真是太妙了!”布朗高興地說,“我們搶五十萬,連被抓到的機會都沒有。”
斯通更實際些,“那些債券我們可以賣多少錢?你說它們很容易兌成現金。”
赫伯說:“可以賣二十五萬元。現在,我們把時間弄清楚。”
他們聚在一起,重新說了一下各個步驟,然後赫伯站起來,戴上圓頂帽。
“再見,”他嚴肅地說,“4點58分見。”
3點30分,送到。
4點時,他默默祈禱那兩個人已經來到樓下。
4點15分,他拿出一張黃色的收據,放在寫字桌上,開始登記偽造的項目。勞倫斯已經離開,另外兩個年輕職員也走了,最後是比利。
赫伯看看時間,驚訝地發現,已經4點55分了,正是斯通和布朗離開樓下辦公室的時間,也是芬黛化妝的時間。
那位秘書小姐從抽屜取出一隻大手提袋,向洗手間走去,經過他身邊時,衝他微微一笑。
他迅速將紙簍放到最方便的位置,小心地把十來張廢紙放在辦公桌邊,部分罩在紙簍上,然後,看了看,覺得很好,接著,用橡皮筋把債券捆起來,壓得緊緊的。他瞧瞧鐘,4點58分,那兩個人該來了。
赫伯緊緊地閉上眼睛,再緩緩張開。這時,門邊閃進兩個戴麵罩的人。
搶劫完全依照計劃實行。
赫伯從他俯臥的位置,看見債券被丟進廢紙簍,廢紙滑落,蓋住債券,四條腿跑開了。
立刻出現了穿著絲襪的兩條腿,芬黛小姐的尖叫聲在房間裏回響。
一個小時之後,警官問完芬黛小姐和泰波副經理,轉而問赫伯。
“這麼說,你描述不出歹徒的模樣,赫伯先生?”警官坐在赫伯桌子的角上,兩腳懸空。
“是的,”赫伯回答說,“一個矮胖,一個瘦高,兩人都戴著麵罩。”
警察手裏拿著一張號碼單問:“這是被搶債券的全部號碼嗎?”
“是的。”
“你還要問我們話嗎?”泰波問。
“我想不要問了,我再問問這位赫伯先生就沒事了。”
“那麼我們先走了。”泰波和芬黛小姐走了出去。
警官在問話時,來回擺動他的腳,踢到了紙簍,紙簍搖擺了一下,差點翻倒。
赫伯屏住呼吸,現在有一捆從廢紙簍中露出來了!
警官站起身,沉思地望著副經理辦公室,赫伯用手肘把其餘的紙從桌上推進紙簍。
警官帶他向副經理的辦公室走去,赫伯看見一個粗麻袋被放在一輛推車上推進辦公室,車後是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女人。
警官看了那老女人一眼說:“是清潔工。”說著拉赫伯走進辦公室。
赫伯向警官敘述當時的情況,這時他聽到擦桌子的聲音,聽到紙簍被拿起來倒進大麻袋。
當他們從副經理辦公室出來的時候,赫伯急忙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低頭往下看。
紙簍空了!
當清潔工推著車穿過門進入走道時,他眼睛一直盯著她的背影。
半小時後,警官才結束談話,和他一起乘電梯下樓,到了街上。
警車一走,赫伯立刻跑到拐角叫了一輛出租車。
當出租車在機場停下時,赫伯跳下車,跑進候機室,喇叭正在播報:
“最後一次播報,飛往裏約熱內盧的706航班的旅客請走4-C門。”
赫伯看看機場的鐘,7點。從早晨起床到現在,剛好十二個小時。
在4-C門前,他走到一位穿黑大衣、戴花帽子的人身邊,那人背對著他,看著兩個行李箱。
赫伯拍拍那人的肩膀說:“媽,我正好趕上。”
“好極了,孩子。”聲音仍然是甜蜜蜜的,但是精神好多了,“一切順利嗎?”
“是的,媽媽,非常順利。”
赫伯拿起行李,向登機口走去,他笑了,從今以後,媽媽再也不用在泰波父子公司當清潔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