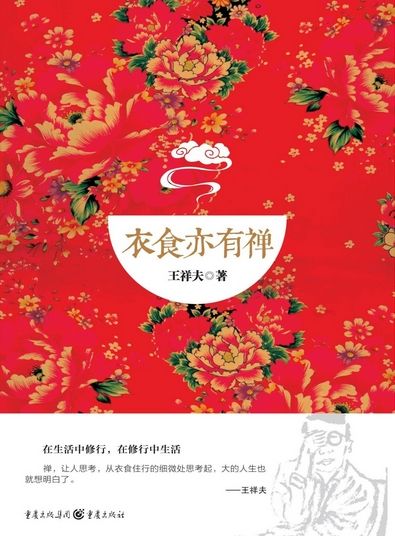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胡同時光
裏弄、胡同、巷子,這三者其實都一個意思。
在北方,沒有叫“裏弄”的,大多叫巷子,這個巷,那個巷。陸遊的“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見宋時已經在叫巷了,或可能更早。胡同、巷子、裏弄一般都交錯在居民區,但也有把商店開在很窄的胡同裏邊的,但那些店一定也大不了,是小店,或買賣文具紙張,或買賣火柴蠟燭,更多的是買賣糧食,所以有“糧食胡同”。叫這個名字的胡同好像是各地都有,北京有,別處也有,還有就是“四眼井”這個胡同的名字,北京有,別處也不少。若考證起來,相信一定有意思。一條胡同裏有四眼井?這比較少見,一般的情況是有一眼就足夠了,除非大宅院非要堅持自己打井,如一條胡同裏有十來戶大人家,而且都要各自打井,一條胡同有十來口井,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糧食胡同”一定與賣糧有關,賣糧就得有糧店,糧店的樣子現在許多人都不大清楚了,一進門,首先是糧櫃,糧食都在木製的糧櫃裏放著,玉米麵,一個櫃;白麵,一個櫃;大米,一個櫃;高粱麵,又一個櫃;小米,當然也要一個櫃。當年還供應豆類,每人每月一兩斤,多不了,黑豆、小豆、梅豆或綠豆,隨你喜歡買哪種,豆子又得要一個櫃。櫃子後邊就是麵袋,都碼得很高,直頂到房梁。白麵碼白麵的,玉米麵碼玉米麵的,大米碼大米的,還有掛麵,也一摞一摞碼在那裏。起碼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所有的家庭要吃飯就得去糧店買糧,家裏要備有許多種麵袋,放白麵的,放大米的,放小米的,放玉米麵的,放豆麵的,大袋兒小袋兒各有各的用,也一定不能亂。我家有一個竹製的小孩兒車,當年母親就經常推著它去買糧,一袋又一袋,買多少,哪一袋放什麼糧哪一袋放什麼豆子都不會出錯。當時每月供應多少白麵大米或粗糧都是有規定的,買白麵的時候,你可以買掛麵,買了掛麵你就別想再買白麵,就供應那麼多。但你這個月沒全部買完,糧店的人會給你存起來,想買的時候再買。糧店內部最特殊的景致應該是那幾個從房頂吊下來的鐵皮大漏鬥,你把空麵袋對著鐵皮漏鬥撐好了,負責稱糧的就會把糧食從鐵皮大漏鬥給你倒在糧食口袋裏。放糧食的木櫃子到了晚上要打印子,一塊大方木板,上邊刻著字,要在麵櫃的麵上一個挨著一個地打印子,這樣一來,值夜的人就沒法子打麵櫃子裏糧食的念頭,你要是去偷麵,那麵上的印子一亂,馬上就會被發現。那塊打印子的板子一定是要鎖在一個地方,一般人拿不到手。究竟誰在保管那個印模子,不得而知。糧店還賣一種糧,就是土糧,是從糧店地上掃出來的糧食,裏邊也許什麼都會有,白麵、玉米麵、小米、大米什麼的,這種糧食也不是一般人都能買到的,必須是熟人。土糧買回去做什麼,雖然被踩來踩去,但買回去還是一個字,吃!
有一年,我們胡同的糧店忽然運來了大批的玉米,是那種整玉米粒,運來,也不進店,都碼在胡同外邊的路邊,一條路的兩邊都碼滿了,從西門外一直碼到了火車站。第二天,糧食部門的人來了,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玉米粒都直接倒在了水泥路麵上,人們這才知道是要在道上曬玉米。這一曬就曬了好長時間,下雨的時候就有人出來把玉米再堆起來,天晴了再攤開,至今人們也不明白那是在做什麼?那些玉米後來是不是又都給磨成麵供應給了人們?或者是千裏迢迢地去支援了非洲,但起碼有一點是,不會去支援了美國。
許多胡同現在都消失了,許多胡同的名字到現在隻是記憶中的事。但也有有心人,在廢墟樣的拆遷工地上到處跑,到處拍照,到處收集胡同牌子。朋友給我看他收藏的胡同牌子,讓我眼前一亮的是“糧食胡同”這塊牌,藍地白字,洋鐵皮搪瓷,亮閃閃的,一點兒都沒有生鏽,想必當年掛在胡同口該是多麼的醒目,現在卻隻有被收藏在私人家裏,這真是讓人懷念,讓人多少還有那麼點傷感。雖然我們現在吃糧方便多了,不用排隊,不用拿糧本兒,不用再找人買從糧店地上掃起來的土糧。日子像是好了,但我們的心情為什麼卻總是不那麼舒坦?為什麼我們不舒坦?為什麼我們總是還要懷念?這也許也是一種動力?
這當然也是一種動力!
玻璃
紫砂器不單隻是宜興有,但說到紫砂就離不開宜興。
到了宜興,可以說是遍地紫砂,有人想買紫砂壺,但轉了一天都沒有收獲,再轉一天,還是沒有收獲,因為紫砂太多,讓他看花了眼。我喝茶不怎麼用紫砂,朋友送的幾把壺平時都擺在那裏,有時候也會用來衝一壺隨便什麼茶,也就那麼隨便喝喝。紫砂壺要長久地用才會精神煥發,總不用,放在那裏,會漸漸失去神采。紫砂花盆種花不錯,但紫砂不宜做餐具,用紫砂汽鍋做汽鍋雞,雞好吃,鍋可不好看,油頭油臉。印象中,雲南昆明的汽鍋雞最好,為什麼?不知道。雞小且嫩,香氣撲鼻。要二兩酒,把雞先吃完,再來一碗白米飯打發雞湯,雞湯最好再熱一下,放些整片整片的薄荷葉子在裏邊,味道很是特殊。好像是,在雲南昆明,吃什麼都要放些薄荷,要不,真不知道那麼多的薄荷怎麼打發?
說到喝茶,我以為還是以玻璃器為好。無論紅茶綠茶,隻要一泡在玻璃杯裏,茶的顏色便會格外煥發。玻璃是從國外傳來,據說是威尼斯人首先發明,一兩千年前或更早,在中國,玻璃器貴比黃金。常見的漢代“蜻蜓眼”珠子,入土既久,一旦出土,珠光寶氣光怪陸離真是有說不出的好看。說到“陸離”二字,其實就是“琉璃”。少時讀屈原《離騷》,其中有這樣的句子,“高餘冠之岌岌兮,長餘佩之陸離”,當時還不懂“陸離”是什麼意思。收藏界習慣把不透明的玻璃叫“琉璃”,透明的玻璃叫“玻璃”。南北朝時期的玻璃器大多都是舶來品,到了唐代大概還是如此,但要是看法門寺出土的那具微綠玻璃托盞,我想那應該是我們本土所產,《東京夢華錄》裏有記載酒肆盛酒用玻璃器,可見玻璃器在宋代的普及程度,但玻璃器終不如瓷器結實,磕磕碰碰,動輒碎裂。吾鄉大同曾出土北魏時期的波斯玻璃碗,學術界多以為當時是用來飲茶的,南北朝時期飲茶之風雖已大開,但我卻以為用這樣的玻璃器做茶具不大可能,因為其遇熱容易裂璺。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散文《美的存在與發現》,寫到了玻璃器:“成排玻璃杯擺在那裏,恍如一隊整裝待發的陣列,玻璃杯都是倒扣,就是說杯底朝天,有的疊扣了兩三層,大大小小,杯靠杯地並成一堆結晶體,晨光下耀眼奪目的,不是玻璃杯的整體,而是倒扣著的玻璃杯圓底的邊緣,猶如鑽石在閃出白光,閃爍著星星點點的光,一排排玻璃杯亮晶晶的,造成一排排美麗的點點星光。”玻璃器的好處就是可以有晶瑩的閃光。我喜歡在家裏比較暗的地方放一個很大的玻璃瓶,讓它把光線折射出來。
為了喝茶,我經常是見到玻璃杯就買,但杯口兒一定要大一些才好。“明前”和“雨前”最好用玻璃杯衝泡,喝茶不但要享受春茶的味,更重要的是享受春茶的顏色,那種無比嬌嫩的顏色,除了春茶不會再有的顏色。如用紫砂壺衝泡不會有這種效果,也很少有人用紫砂壺衝泡“明前”和“雨前”,如用瓷杯衝這樣的春茶,白色的瓷杯和黑色的瓷杯都不會有玻璃杯那樣的效果。人類的生活其實就是一個一直在那裏追尋美的過程,所以,喝茶既要用嘴又要用眼睛。
以玻璃杯衝茶其實是極大眾化的,放茶倒水而已,我主張,幾乎是所有的“明前”和“雨前”都要後投,先把水倒上,再把茶葉投進去,看茶葉慢慢在水中載沉載浮,看春茶的顏色在杯裏慢慢洇開。喝紅茶,用玻璃杯也好,好的祁門紅,初始作葡萄酒色,喝下來,漸作琥珀色,讓眼睛感到舒服。但日本的抹茶卻不能用玻璃杯喝,一是抹茶掛杯;二是抹茶不會讓光線從杯那邊透過來,也沒見過有人用玻璃杯喝抹茶。綠茶粉和抹茶最好用黑色的茶碗。抹茶其實也很大眾,一碗茶,傳來傳去大家喝,雖然有那麼點不衛生。
中國各地的茶館,用玻璃杯的不多,大多是帶蓋兒瓷杯,我喝茶,喜歡找個有庭院有植物的地方,交錢,領一壺開水,要兩隻帶蓋兒白瓷茶杯,然後找地方坐下來慢慢喝。年前與金宇澄去上海靜安寺西邊,居然找到這樣的喝茶地方,坐在池塘西邊的小亭子裏,喝了半天茶,說了半天話,池塘對麵坐了許多老頭老太太,也在喝茶,也在說話。坐在我們喝茶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靜安寺以東那棟張愛玲住過的小樓,那棟樓的大大出名完全是因為張愛玲曾於此居住。忽然就想到了當年張愛玲和胡蘭成在那裏會麵的時候,難免不一邊說話一邊喝茶,無端端的,總覺得張愛玲喝的應該是紅茶,或許就是五月春摘的“大吉嶺”,而且是用大個兒的玻璃杯。滿滿一杯,紅孜孜的。胡蘭成的那張臉,想必也是紅孜孜的。
玻璃樂器
有一種玩具,隻有過年的時候才會有人拿出來賣,是玻璃吹製的喇叭,說是喇叭,卻封著口,放在嘴裏輕輕一吹,“叭叭叭叭——叭!”脆亮好聽,但好景絕不會長,吹著吹著——“叭”碎了!
現在已經看不到這種玩具,好像是也沒人再做,會這種手藝的人大同不知道還有沒有?如失傳,也真可惜。大同人把這種玻璃玩具叫做“琉璃圪棒”。玻璃從域外傳來,漢代在中國本土已有生產,北魏時期的琉璃製品遠遠要珍貴於金銀器,但大多都從兩河流域進口過來。常見北魏墓出土琉璃殘片,真是薄,真是漂亮,在日光下看之,閃爍一如珠母,真是華美異常無可比方!大同把玻璃喇叭稱作“琉璃圪棒”,可見其曆史該有多麼古遠!
玻璃喇叭——玻璃玩具,好像更應該叫做玻璃樂器,在吹製上好像難度相當大,要把玻璃吹到極薄極薄才行,要是不薄,豈能吹之有聲,可見不是一般人所能來得了,我在上海看朋友做琉璃器,我忽然想請他們吹一個玻璃喇叭,我把形狀、大小、薄厚告訴他們,並在紙上畫出來,他們試做一二,但怎麼吹也吹不響。他們說,玻璃能吹響嗎?這是你的一種設想吧?我對他們說,這是一種大同民間的玻璃樂器,壽命絕不會長,吹久必碎,但聲音絕對無可比擬,你想想,玻璃在吹動的時候發出的聲音,那是一種多麼美妙而獨特的響聲!我在那裏說,他們好像還是不相信,玻璃能做樂器嗎?玻璃能發出聲響嗎?再吹幾個試試,均不成功。我忽然更覺得我從小就玩的玻璃樂器是否在大同地區已經失傳,要是失傳,簡直是令人痛心疾首。我去北京,又去北京朋友那邊的玻璃小作坊,我告訴他們“玻璃喇叭”的顏色是紫紅色或淡茶色的,這一回,他們馬上明白了玻璃的配方,這次雖然可以吹得薄一些,但還是無法吹響。雖吹製不成功,但我的朋友的興趣卻高漲起來,他說,吹大大小小幾十個玻璃喇叭,找三四十個人在台上吹奏豈不好看,玻璃閃閃爍爍,聲音清清脆脆高高低低,舞台必須在全黑的底子上有那麼一束光打下來照在那些玻璃喇叭上,那一定是一場極為奇特的演奏會!無可比擬的音樂會!我說這個音樂會是應該在我們大同開,雖然別處也有這種“玻璃喇叭”,但我以為大同的最好!
在中國,經過了舊石器時期、新石器時期、青銅時代,但跳過了鐵器時代,也沒有玻璃時代,而是直接進入了瓷器時代。玻璃在中國的發展史我一直不清楚,好像至今也沒有這樣一本書能把這個脈絡理得清清楚楚。那天我翻看一本《波斯工藝美術史》真是嚇了一跳,上邊寫著“以玻璃做吹器也”!以玻璃做吹器還能做什麼?那不是玻璃喇叭又會是什麼?北魏一朝受兩河流域的影響最大,我設想,那大同民間的“琉璃圪棒”也許一直是從北魏吹到今天!
吹玻璃喇叭要有耐心,我從小到大笨拙且粗心,買兩三個玻璃喇叭,吹一個,“叭叭”——碎了,再吹一個,“叭叭、叭叭”——又碎了,剩下一個不敢吹了,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個盒子裏,下邊還墊一塊布。總記著,我把一個紫顏色的、漂亮的、薄得不能再薄的玻璃喇叭放在了什麼地方,一過就是三十年,我不知道那個玻璃喇叭現在在什麼地方?
爬格子
許多人把作家寫作叫作“爬格子”,像是有那麼點寫實的味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寫稿真可以算是辛苦,寫著寫著就真的要“爬”在那裏了,八十年代的作家也真是能熬夜,寫一陣,看看表,半夜十二點多了,再寫一陣,再看看表,已經是淩晨兩三點了。那時候,我常常會一直寫到淩晨三四點,為了醒醒腦子,我會走到自家北邊的小院裏看看天上的星鬥,那星鬥是那麼的清冷,那麼的明亮,周圍又是那樣的寂靜。在這種眾人都睡你獨醒的時候,你的腦子像是特別的清醒。我那時候年輕,在仰望星鬥的時候,心裏,覺得自己特別的了不起,是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到了後來,才明白作家隻不過是一種職業,任何加在作家頭上的美譽都很好笑。
八十年代作家寫長篇,簡直是無一例外,幾乎全部是靠手寫,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一次大學的講座上,有個大學生突然站起來提問:“您的第一部長篇,三十多萬字,真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嗎?”我當時在心裏笑起來,難道可以兩個字兩個字抄嗎?那隻能是用電腦,一下子打出兩個字或三個字的詞來。所以近二十年中國的小說產量才會那麼高,有人計算過,現在小說的年產量是二十年前的三十多倍還不止。所以我會在心裏更加佩服那些古代的作家,用毛筆,寫小楷,那些上百萬字的小說是怎麼作出來的?那才真叫是毅力!比如《紅樓夢》,或者是《三國演義》。簡直是“好家夥!”
八十年代,是一個充滿了種種美好理想和憧憬的年代,寫作在那時候真是神聖,開筆會,頭天晚上就開始興奮了,想第二天怎麼發言,“思想”和“哲學”這兩個詞在那個年代總是揮之不去。那時候寫發言稿是徹夜的事。由於沒有電腦,隻能靠寫。我那時候特別喜歡那種很大張的稿紙,這種稿紙的天地和兩邊的地方特別的寬大,改起稿來特別方便。那時候開筆會,不止是我,許多人都特別熱心收集稿紙,《上海文學》《人民文學》和《青年文學》的稿紙,是讓青年作家眼熱的東西。一旦收集來,卻並不單單是用來寫稿,更多的是用於寫信,亦是一種虛榮心。八十年代人們沒有手機,打電話也不方便。想和朋友說些什麼就寫信。各種的信紙,各種的信封,都是為寫而準備的。信紙有特別漂亮的花箋,信封也有各種的樣式,上邊且印著各種漂亮的圖案。我認為,近二十年來郵政是中國曆史上最沒有美感的郵政,一時間,竟然取消了所有形式的信封,要想寄信就必須買他們印製的那種牛皮紙信封,可以說是一種可恥的壟斷行為,好在,我們現在有電腦,想說什麼可以發電郵!好在,我們現在有手機,想把消息告訴朋友,我們可以發短信!不必再為那種醜陋而統一規範的信封氣惱。我現在自己印有好看的信封,我給朋友寫點什麼,比如用八行箋,寫好了,裝在我自己的信封裏,然後親自交給朋友以做紀念,我們才不稀罕郵電局的那一枚郵戳。
八十年代對作家而言是個辛苦的年代,是,一定要寫,是,一定要把時間耗到,趴在那裏,把背拱起,眼睛近視的,要把臉幾乎貼在稿紙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起。我的第一部長篇《亂世蝴蝶》,最後一遍抄完,右手的手掌上留下了厚厚的繭。好多年後,才慢慢退去。說作家的寫作是個體力活,可以說一點點都不誇張。用陝西話說,是“沒有身體,吃架不住”!作家有寫死的,從古到今,不在少數!而現在的寫作就相對輕鬆得多。但我還是懷念八十年代,那種情懷,那種神聖感,那種徹夜寫作的“耕作”精神。當然我也喜歡電腦,現在我也離不開電腦。我們這個時代是受電腦左右的時代,你去銀行取錢,有時候銀行的人會告訴你電腦出問題了,什麼都不能辦!
這是個讓人有許多說不完的麻煩的時代,如果電腦一出毛病,作家的煩惱就更大,走出來,走進去,抓耳搔腮。我不大懂電腦,說來好笑,有一年過年的時候,我在電腦前點了一支香,唯願電腦在新的一年裏不要給我找麻煩,好好兒的別出毛病。我現在是完全接受電腦的統治!除此之外再無他法,誰讓現在是“現在”,而不是八十年代。
案頭
我的書房,現在是沒有齋名的。前不久翻閱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汪巢林的詩集,很喜歡他的“清愛梅花苦愛茶”。這句詩真是很好,便想用來做齋名,但太長,如取其中兩字,起一個“清苦齋”,又顯得太嬌矜。我畢竟不清苦,起碼比一般人還過得去,還喝得起八九百元一斤的六安瓜片。我很喜歡周作人先生給自己取的齋名“苦雨庵”,後改為“苦茶庵”,左右不離一個“苦”字。如果自己也真把書房叫做苦什麼庵,恐怕寫出文章也要枯淡無味了,更何況我也沒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把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的情懷。
再說我的書案,我的書案很像銀行堆滿賬簿的台麵,三麵都是書,左邊一摞是工具書,我常用的計有:《古漢語辭典》《辭海》《語言與語言學辭典》《說文解字》《中國地圖》《中國大辭典》《日漢小辭典》。靠著這一摞的是大本可達四斤之重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魯迅手稿》《孫中山先生手稿》。旁邊的那幾摞就常常變換了。比如現在的有:《牡丹亭》《養吉齋從錄》《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金聖歎批本西廂記》《四聲猿》《絕妙好辭箋》《古代房事養生術》《袁中郎尺牘》《壇經》《詩經》《易經》《孫犁論文集》《豐子愷漫畫集》《博爾赫斯小說選》《冬心先生集》《六朝文箋注》《弗洛伊德主義與文學思想》《肯特版畫選集》《林風眠畫冊》《京華煙雲》《燕子箋》。這些書像好朋友一樣團團圍坐在我寫字台的三麵,終日與我頻頻交談,令我想入非非。桌子左邊還鋪著一小塊織得很粗放的小麻毯。這份格局比較特殊,毯子由綠、粉、黃、灰、紫五色的麻織成,寫東西的時候正好襯著左胳膊,一邊寫一邊喝茶時,茶杯也順便擱在這塊小毯上,既不滑動,灑了又不至於驚慌。小毯上有一拳大的玻璃球,球裏一朵永開不敗的粉色玻璃花。還有一青花筆筒,上邊是山水亭林,為楊春華所贈,是她的畫瓷作品。一漢代漆木瑞獸,其狀如蟾蜍,卻有角有翼。一對北魏藍玻璃小鳥,玻璃裏布滿內裂,迎光視之,漂亮非凡,應該是當年從兩河流域那邊過來的存世孤品。還有兩隻大骰子,每一隻都有嬰兒拳頭大,寫累了的時候,擲一擲骰子玩,可以讓自己休息一下。比如說,我的長篇《蝴蝶》,一共寫了七章,就是擲骰子的結果:擲三下,最大一次是七點,就寫了七章。桌子右邊是台燈,粗麻的燈罩,燈下邊是亮晶晶的小銅鬧鐘,提示我該去睡或該去做什麼。旁邊又是一方北魏四足石硯,四邊各一壺門,硯麵四角又各一朵蓮花,硯池圓形,圍著硯池周邊又是一圈綯紋。古硯的旁邊是開片瓷水盂、放大鏡。還有放閑章的盒子,裏邊有幾十方閑章,其中兩方閑章我自己最喜愛,一方的印文是“友風子雨”,一方是“境從心來”。桌上還有鎮紙,一塊是糯米漿石的,上邊鐫“筆落驚風雨”五字。一塊是紅木鑲螺鈿的,三棱形,三麵都鑲的是琴棋書畫。我很喜歡這個鎮紙,畫小畫用它壓壓紙,我喜歡用很粗糙的毛邊紙寫寫畫畫,這種紙留得住筆,畫山水梅花筆筆都枯澀蒼茫!
我的案頭,刪繁就簡到現在還有兩大盆花,一盆是龜背竹,在書桌的左邊,大葉子朝我伸過來,夜晚就顯得很有情。當人們都睡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它是你的朋友,熱鬧時會失去許多朋友,冷清時會記起許多朋友。我的身後,另一盆幾乎可以說是樹,比我都高!葉子有蒲扇大,開起花來可真香,有人說它叫玉簪。我看不大像。這兩盆花總伴著我到深夜。我常常於深夜想到的一個問題是,花用不用睡覺?這個問題恐怕無人能解答。
我的書房裏還有什麼呢?銅炮彈殼,一尺半高,裏邊插著一大把胡麻籽,讓我想起那個小村子和那個部隊。搬家後,我把許多東西送人,但永遠不會送人的是那兩件青花瓷。一件是花熏,像小缸,上邊有蓋,蓋上有金錢孔,遍體青翠。當年是熏小件衣飾的,如手帕,如香包,如荷包。熏襪子不熏我不得而知,但我想象我的祖母用它來熏淡淡發黃的白紗帕,帕上繡著一隻黃蝴蝶和一朵玉蘭花。還有那青花罐,圓圓的,打開,蓋子像隻高足小碗,下半截就更像是碗。我很想用它來做茶碗,但舍不得。這兩件青花瓷,一件上遍體畫著纏枝牡丹,一件遍體畫著鳳凰和牡丹。都是手畫。除了兩件青花瓷,還有幾把紫砂壺,還有一盒老墨,老墨是一位小時候的朋友送的,他去英國倫敦定居已有十一年。那盒墨真香,打開,過一會兒,家裏便幽涼地彌漫了那味兒。盒子是古錦緞的,裏邊是白緞。這盒墨我一直舍不得用,都裂了。十錠墨沒有一錠拿得起來,再過數十年或數百年,它一定是書畫家們的寵物。盒裏白緞上寫著我的一首詩,詩曰:
相見時難別亦難
常思相伴夜將闌
聯衾抵足成舊夢
細雨瀟瀟送離帆
寫這篇小文時外邊正下著雨,是入秋以來第一場大雨,原想打開窗子讓屋子裏進進雨氣,想不到那雨卻一下子飄到案頭來,用手摸摸,案頭分明已濕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