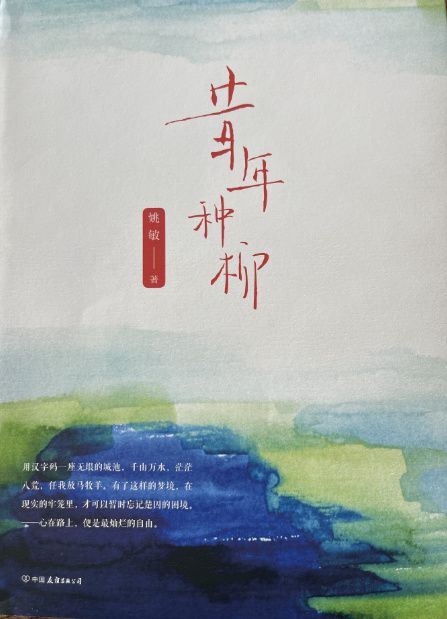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裂帛
春天於我是一個地理概念。
在故鄉溪頭,水底滑溜溜的青苔綠染上了岸邊細柳。風一天天妖嬈,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像打翻了金色的顏料桶,潑濺得漫山遍野。桃花紅李花白,陽光攪混了空氣裏的一萬種香料,煉製成春天的迷幻藥。我像個貪得無厭的浪子,盡日在花叢裏無所事事地穿梭,用力吸吮清晨花蕊裏清甜的鰩水,和蜜蜂蝴蝶爭搶春色。
而其實,這樣的鏡頭隻是成年後的想象,是遠離故土多年之後,在被高樓圍困的都市裏的意念。記憶已經模糊,而距離年老又還早,在一個兩不著地的中間年歲,過去未來,都如同毛玻璃一樣看不分明。春天在一個懵懂少年的眼裏真的停留過嗎,真的喚起過驚喜與悵惘,真的曾經啟蒙過一個孩子心底裏最初的愛情?
幼年的記憶是襤樓的。年輕的母親在春天的竹林裏砍伐隔年的竹子,男人一樣走了長路扛去集市,換回鹽巴和白糖。祖父的藍布長衫已經和須發一樣斑白,春天午後的陽光裏,握著篾刀的祖父,在一棵老核桃樹下昏昏欲睡。春雨浙瀝,從滑溜溜的田埂上跑回家,張開了口的布鞋被泥巴糊得沒了鼻子眼睛。
但春天從不襤樓。每一莖枝頭都歡喜熱鬧,每一瓣落花都潔淨高貴。四月,一聲驚雷過後,雨一夜一夜落在老屋的青瓦上,落在綠茸茸的草坡上,一畦一畦的豌豆苗很快將山坡的黃土掩蓋得沒了一絲痕跡。似乎山野亙古以來就是富足的桃源,從未有過冬天的荒冷與蒼涼。
我生於春末夏初,芒種前後。
我知道這個句子是個病句。其實,芒種一過,就是伸複,與春天分明已然不搭界了。
母親說,生我的那年,故鄉大早,野地裏除了鋪天蓋地的紫雲英什麼也不生長。三十歲的母親從頭到腳長滿了皰,夜裏熱得無法人睡,整整一個夏天便將蚊帳支在院壩裏,直到秋涼。
我常常忘記,母親為我紀年的乃是農曆,農曆的四月,早已經不是春天。但我習慣了這個病句,劉慣了一個一個數著春天的節氣,等待季候上的春天過完,夏天到來。似乎都天隻適合等待,等持一年義老去,然後對自己說,四月過完了,該起身了。
祖父今年整整一百歲了,去世已經三十年。我本來想,要為他寫一篇長文,可是,他正月初人的祭目過了,清明過了,農曆三月的生日也過了。我竟一直不能動筆。
這夜裏被雷聲驚醒,腦子裏竟電光石火般閃過“製帛”這個詞語。想起的是簡娘的句子:“四月的天空如果不肯,五月的希衣如何開頭?“
2008・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