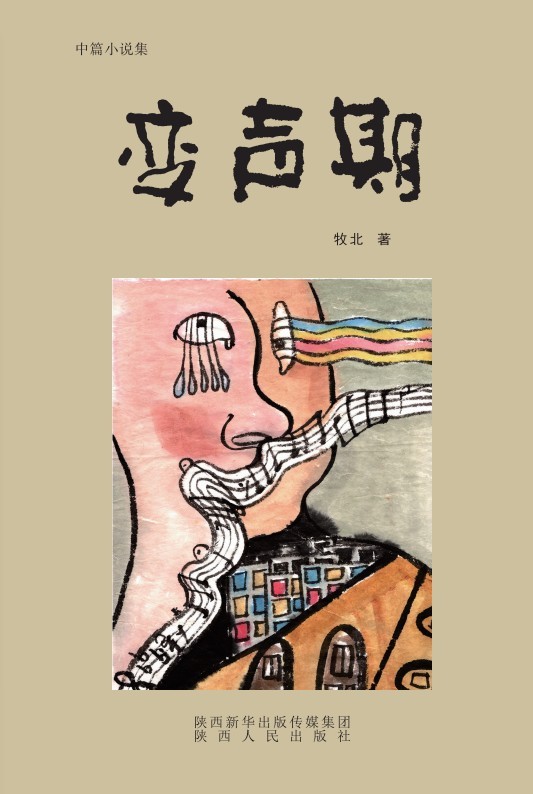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攢年漢
上部
初春夜,姚廣德的驢叫了一宿。
姚廣德清早起來衝著牲口圈罵張能能,應該把你大爺爺放出去,別拴在槽上,要不然它能安生?張能能起得比驢早,蹲在驢槽下,苦惱地央告它,大爺爺,你別叫了!你把老家親們都攛起來了!驢不聽他的話,狂躁不止。張能能隻好將它趕向後山。驢一會兒就跑得不見影了,張能能追得一頭死水往外冒,還是追不上驢。路邊拾糞的孫老漢看到對張能能說,娃娃,^追了,你追不上,就在這等著。張能能氣喘籲籲地說這蓋佬兒,連哭帶嚎一宿,我大都惱了!讓我趕出來遛遛,這一出門不見影了!孫老漢說,你大沒給你說驢咋了?張能能搖頭說,麼!孫老漢說,^管了!驢發情呢,跟你一樣!
張能能耷拉著腦殼,沮喪地回了姚廣德的院子,巧巧端著尿盆往外跑,返回來帶著尿騷味劈頭蓋臉問他,二能子!我的繡花鞋不見了,大清早瞎跑什麼?張能能說攆驢去了。巧巧說驢要緊,還是我要緊?張能能張大嘴巴不知道怎麼回答。巧巧擰著細腰憤怒地回了窯洞。張能能手足無措地懵在院子當中,姚廣德的老婆又擰著水桶粗腰出來說,粘飯熱了,先吃飯,磨磨蹭蹭一早上了!話語裏帶著怨氣,張能能剛要去吃飯,姚廣德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在了當院。他腳步輕盈,五十多歲的老漢,腳大卻沒有風。依然是不知不覺,一個無影腳踢在了張能能的屁股上,大聲嗬斥著問,驢呢?張能能說跑了……跑山後頭就不見蹤影了!姚廣德說,驢沒找回來,你跑回來幹啥?張能能指著窯洞,囁嚅著說,吃麼。姚廣德罵,沒有驢,吃你先人的供品哩?咋去膚施城?還想著吃?張能能說滿山跑呢麼……姚廣德又飛來一腳,張能能下意識地躲了一下,姚廣德怒睜圓目,一大早的戾氣全衝到眼睛仁裏了,張能能嚇得不敢看姚廣德,站在當院子裏聽著姚廣德大罵,羞你先人哩!昨晚跟你說了一夜,你撒泡尿全忘了?去膚施城是大事!人家馬幹部立馬就來了,拿什麼交代?驢日的,你重要還是驢重要?還不快去攆?張能能被姚廣德兩腳踢完,心裏早就崩塌了,不知所措地呆立著,被姚廣德一喊一罵又一腳,已顧不得疼,慌忙跑出院子。窯裏還傳出姚巧巧的叫喊聲,二能子,你死哪去了?我的鞋找不著了!
張能能大清早輪番受了一肚子氣,就把怨氣撒在腿上,腿上歡實起來,帶著對驢的一股子狠勁,傷口崩開了,血從腳脖子上流下來,他自己已顧不得,撒開腿向後山狂奔而去。跑到後山看到二郎神廟威武聳立。山野之中,鄉民所祭拜的神仙千奇百怪,大多是為了安家鎮宅,撫慰風水。張能能站在山坡上看著那廟,心裏畏懼了,寸步難行,黑頭驢就在廟前啃著幹草,張能能叫了幾聲驢,驢不理他,他不敢向前邁步,隻好蹲下來等著它,心裏怵得緊。村裏傳說這二郎神邪門,如若無故衝撞,必然遭受到懲罰,前些年就有衝撞了二郎廟,無故瘋癲,跳井鑽水甕,癡傻結巴的事情屢見不鮮,這廟就妖魔得很,像張能能這樣的人更不敢近前。
他蹲在山坡上,幹吼了幾聲,驢像是被二郎神召喚了,狐假虎威起來,壓根裝作沒有聽到。他望著二郎神廟,像望著一尊巨大無比、法力無邊、令人不寒而栗的黑色鬼怪,當然,他從說書人的口中得知,這二郎神並非壞神仙,而是長著三隻眼睛的好神仙。村裏的二郎廟卻是另一番模樣,他不敢近前,就那麼一直等得肚子直叫,驢才慢騰騰地下了坡,張能能低頭哈腰地拉住驢的韁繩,再向村裏走去的時候已是晌午。
張能能拉了驢剛進姚家的院子,以為等待他的又是一頓臭 罵。沒有想到,院子裏安靜極了。姚廣德搓了一指旱煙吸著,誰也不說一句話,姚廣德的老婆踮著小腳從窯洞門口走出來,故意笑吟吟地問他,二能子,你咋才回來麼?人家馬幹部等了你一上午,尋個驢弄不了。馬幹部,我這兒子他死心眼!憨得很!
姚老婆說完,從她的身後閃出一個人影來,是四區公社派來的馬幹部。馬幹部穿著舊軍裝,懷裏正抱著一卷毛口袋,正微笑看著張能能,張能能上次遠遠地看見過馬幹部,與巧巧不是一樣的女人。走近前看,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不知所措地低著頭。姚廣德罵了一句,一大早跟雷劈了一樣!還不快走?張能能趕快鑽進側後麵的窯洞裏,他一進門,就從窯洞傳出一陣巧巧的咒罵聲。
馬幹部抱著羊毛線口袋,聽著那些粗野的罵聲,看著姚廣德,姚廣德解釋性地掩飾道,就是個賤種子。而後又換副口氣衝窯洞裏喊了一聲巧巧。
一眨眼工夫,巧巧穿著新衣、花鞋走了出來,一條大辮子甩在前胸,眉清目秀櫻口挺鼻,活脫脫的一個小美人。馬幹部不自禁歎道,這是個俊女子!巧巧也不拘束,走過來拉馬幹部的手。姚廣德得意地說,這就是我小女子,巧巧。馬幹部不失禮貌地伸手與她握了握,怎麼也與剛才在窯洞裏傳出來的聲音對應不起來。正愣著神,張能能從窯裏跑出來,背上背著一個大木桶,看起來有些滑稽。姚廣德又罵,懶驢上磨不是拉屎就是尿尿,人家馬幹部這麼站半天了!走麼!
姚廣德的聲音洪亮,張能能背著木桶跑到驢圈慌忙拉了驢就走,姚廣德大搖大擺地出了門。馬幹部這才看清了巧巧的腳,似乎有那麼一點跛,她也不敢多看,跟了上去,張能能走在最後麵,魚貫出了院子。院子裏姚老婆不高不低地喊了一聲,飯還沒吃哩!姚廣德和巧巧好像沒有聽到一樣徑直往外走,巧巧等了一下馬幹部,故意拉上她,和張能能保持了一段距離,馬幹部也沒有多想,和巧巧並排走出了張家圪嶗。
從姚家院子到村口,姚廣德的腰板硬朗,像是去膚施城領 賞。他要讓張家圪嶗的人看到,他姚廣德那是和公社幹部走在一起的人,那可是一種榮耀,似乎在心裏尋求到了某種庇護。巧巧和馬幹部在一起,更證明了他姚家非同一般的地位,這狐假虎威的架勢,村裏人是看明白了。對馬幹部來說,她也沒有想那麼多,她隻有一個任務,那就是帶著張能能,去膚施城的縣政府拉棉花籽,還得上半個星期的棉花種植培訓班。一個星期就是七天,姚廣德不清楚,一盤問這半個星期就是三天。
馬幹部通過在村裏了解、詢問村幹部,最後確定了由張能能參加棉花培訓班。原因是,張能能是張家圪嶗最有苦水的年輕人,張能能最能吃。能吃就把他派出去,姚廣德也因了這條原因同意了馬幹部的提議,但是姚廣德附加了兩個人,他和小女兒巧巧也要去膚施城。他父女倆去幹什麼?姚廣德找了一條理由,給張能能和巧巧置辦訂婚的禮服。
姚廣德有他自己的算盤,土改他被確定為不大不小的地主, 所以一直在張家圪嶗抬不起頭來,這兩年他受盡了張家圪嶗這些窮鬼的白眼。原來,他姚廣德那是張家圪嶗的土皇帝,呼風喚雨,為所欲為。現在隻能跟那些又臟又臭的窮人整天出山種莊稼,當然,通過改造,聰明的姚廣德逐漸看清了世事,現在整個陝北都是這些幹部的天下,他隻能低頭老實做人,夾著尾巴走路,兩三年的功夫沒有白費,馬幹部主動找上門來,要張能能去膚施城 “學習”,這是一個爆炸性的政治信號,姚廣德必須充分利用這次機會,那麼除了提出他和女兒巧巧一起去膚施城拉棉花籽,他還提出了另一個要求,請馬幹部給巧巧和張能能做媒人。如果不答應,姚廣德是不會放張能能去 “學習”,這等於落魄地主姚廣德要和馬幹部結親哩。等於姚廣德又直起腰來了。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馬幹部經村裏老張等人的提醒,不是沒有考慮過這些因素,但是,她想得比較單純,無非是做媒人嘛,好事啊,這是團結群眾的一個好辦法,何況對於地主,馬幹部根據區上的意見,眼下還是要團結、改造為主,於是就答應了姚廣德的要求。老張等人再次提醒馬幹部,張能能不是一般人。說白了,沒有人把他當作人看。馬幹部驚奇,這話怎麼說呢?老張吞吞吐吐地從煙霧裏吐出幾個字,張能能這娃是哩!
啥是攢年漢?馬幹部不明白,她是南方女人,不懂陝北風 俗,老張說了半天,帶著濃重的陝北話,她還一知半解。最後老張婆姨說,曉得童養媳不?馬幹部說曉得。她的陝北話說得有些生硬。老張婆姨笑說,女娃放婆家養,叫童養媳,男娃放丈人家養就叫攢年漢。馬幹部明白了,老張又說這男人五六歲送到咱張家圪嶗,原來也不姓張,姓折。姚廣德就是要欺負張家圪嶗的張姓人,就逼著張能能姓了張。老張又說,人但凡能活,絕不會讓男娃去當這攢年漢,老折家在黃河岸子邊,五個兒子,天災人禍不斷,實在活不下去了,才把這最小的兒送來當攢年漢,等於賣了兒子,羞先人哩!馬幹部說,那這張能能到姚家能幹啥?老張婆姨說,這娃可苦命哩,從來姚家以後,那就等於是姚家的長工哩!老張說,哪是長工?還不如姚家的牲口哩!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要是個人,誰能受得了這苛打?你說這叫啥來著?
馬幹部想了想說,這叫剝削!
張能能拉著驢,看著前麵三個人,有些恍惚,剛出村這才走了不到十裏地,腳底下就有些軟,他的鞋趿拉著,這雙鞋是姚廣德穿剩下的平底布鞋,給他的時候,鞋頭就破了個大洞,這是他
今年過年的禮物。他穿上有些大,姚廣德至少穿了有三年,鞋底都磨薄了。今天這雙鞋好像不是他自己的鞋,它看不到自己的主人,撒歡了,不聽使喚了,自己做了自己的主,自己飛了起來
張能能醒來的時候,看到馬幹部正抱著他,用她自己的水壺給他灌水,馬幹部的水是溫熱的,把他的身子一下子就灌滿了、灌熱了。他驚醒過來,慌忙躲開了馬幹部,看著旁邊的姚廣德和巧巧正怒視著他,他擦了擦嘴角的水,表示自己與馬幹部毫不相幹,但是已經遲了,姚廣德飛起一腳,正中他的小腹,張能能像一個碾軲轆一樣滾下山坡。
姚廣德罵道,羞你先人哩,這大清早裝死人?
馬幹部快速擋在姚廣德麵前,正色道,姚廣德,你怎麼打人哩?
姚廣德被馬幹部突然的舉動嚇住了,隨即趕緊換了副嘴臉, 笑嗬嗬地走近前說,馬幹部,這孫子偷懶哩,這才剛走幾步,裝模作樣,懶驢不打不上磨,別耽誤了咱的大事。馬幹部要去拉張能能,巧巧突然一機靈,轉身去拉張能能,張能能不理巧巧,在土坑裏爬起來,繼續背上木桶,返回路上把自己丟了的鞋撿回來,然後套在自己的腳上,一句話不說繼續拉上驢,等在路邊。
巧巧怨怒地跺腳說,大,他還不理我!
姚廣德給巧巧使了個眼色,巧巧噘著嘴。馬幹部從挎包裏掏出一把炒米,伸手遞給張能能,張能能愣住了,姚廣德也愣住了,張能能看看那白皙的拳頭,手指間還往外流金黃的小米,舔了舔嘴唇,看一眼憤懣的姚廣德。默默拉著驢向前走去,與此同時,巧巧的手就打過來了,差點將馬幹部手裏的炒米打撒了,然後順勢將馬幹部的手和炒米一起推在她的懷裏。
巧巧說,我大說了,他不餓,就是偷懶哩。
馬幹部一刹那對巧巧有些厭惡,但在她的眼裏,巧巧不過十六歲的少女。她對姚廣德說,人是鐵飯是鋼,吃飯也是革命!姚廣德趕忙解釋說,吃了,他飯量大得很,昨天吃了這麼兩大碗^哩,我這家遲早被他吃空!姚廣德一邊說一邊比畫著。馬幹部說,昨天吃,今天不吃嗎?姚廣德說,今天走得急,城裏到處裏是飯館子,我保證讓他吃個夠!馬幹部聽著姚廣德這麼說,站住看著他說,姚廣德,從這兒到城裏,得走一天時間,他是個人,能扛到明天嗎?姚廣德笑了笑說,餓個肚子也不是啥大事麼,我聽說咱八路軍的大幹部現在也天天餓肚子哩,再說了,他咋能想著吃你的幹糧,喝你的水呢?這不是跟幹部搶吃搶喝麼?我姚廣德覺悟這麼高,咋能幹這種事情?姚廣德有些強詞奪理,馬幹部竟不知從哪一句話上反駁,低頭琢磨了一下,然後舒了口氣,心平氣和地說,幹部是群眾裏走來的,說白了,也是群眾的一員,幹部更愛群眾,不像你們地主!這話有些軟,但是姚廣德明白,這話裏硬氣了。他不敢多說了,再狡辯那就是不懂理了,現在是這些穿土布八路軍幹部的天下。得天下者得理。姚廣德這個道理還明白得很。
馬幹部腳步很快,想攆上張能能,張能能故意把驢拉到身後擋住馬幹部,馬幹部看出張能能給出她的距離,落了個紅臉,隻好跟在驢的身後。姚廣德喊了一聲,說,馬幹部,離驢遠一點,它脾氣不好,別踢了你。陝北毛驢確實野得很,她第一次到張家圪嶗已經領教過了,腳步不由得慢下來,姚廣德嘴角泛出一絲嘲弄的笑意。
巧巧追上姚廣德,臉上還是慍怒,她拉了拉姚廣德的後襟, 很不高興地問,大,她說啥?幹部更愛群眾?誰是群眾?二能子?她愛二能子?她咋那麼不要臉呢?二能子是巧巧送給張能能的外號,巧巧說驢都有外號,咱家驢叫大能子,他就叫二能子。後來家裏人也常這麼叫著。姚廣德使勁瞪了巧巧一眼說,瞎說啥呢?閉嘴!巧巧並不閉嘴,帶著哭腔說,我明明都聽見哩還不讓我說?他們幹部咋想愛誰就愛誰呢?姚廣德說,閉嘴!人家馬幹部有男人哩!巧巧說她有男人咋還要愛二能子呢?姚廣德說,你給我閉嘴,巧巧一聽她大生氣了,反而更囂張矯情了,剛要說什麼,馬幹部停住腳,拉住巧巧說,巧巧,我真有男人哩,我男人是從長征走過來的老紅軍,現在在山西前線打日本人呢!巧巧似乎得到了巨大的自我赦免一樣,再次走過去,拉住馬幹部的手,連說帶笑地親熱起來了。馬幹部說放心了?巧巧撲哧一笑說,我最放心你了,姐,你是幹部,你的話,莊裏人都相信,大家都這麼說,還說你俊哩。馬幹部說真的?巧巧說當然真的,姐,你咋這麼白呢?比新磨的白麵還白呢?我還沒見過這麼白俊的女人哩!
巧巧這一說,迎麵就遇到了剛剛綻放的杏花,粉白粉白的, 巧巧指著杏花說,就像那花一樣。馬幹部也笑了笑,這天下的女人都一樣,誰不想聽讚譽的話呢?馬幹部也一樣,這話題一下子就轉移到了別的地方,矛盾也似春風吹過,留下的是杏花淡淡的馨香和泥土中青草剛剛冒尖的芬芳。
兩人一邊走一邊說,竟被落下了有十幾步遠,姚廣德和張能能已經不見了蹤影。從山巒間傳來張能能脆生生的信天遊:
桃花花你就紅來,杏花花你就白。 爬山越嶺尋你來呀,啊格呀呀呔。
馬幹部聽著信天遊,不由得呆了,忙問巧巧說,這好像是張能能的歌呀?巧巧說沒錯,除了他,還能有誰?馬幹部說著,從挎包裏拿出一個馬蘭紙縫成的小本子,不慌不忙地記下來。不懂的地方就問問巧巧,唱完了,記完了,馬幹部咀嚼著那歌詞,感到有趣極了,意味深長地說,他唱的人是你吧?巧巧說,哪裏是我,他給驢唱呢。馬幹部撲哧一笑說,這是情歌哩,你倆真好。巧巧突然臉一紅,趕忙解釋道,哪裏是我,他心裏隻有驢!
馬幹部和巧巧緊趕了幾步,看到張能能坐在路畔子下麵緊緊拉著驢。姚廣德坐在路的上頭,屁股下麵還墊一條羊毛口袋,另一條口袋放在路當中,顯然是為巧巧和馬幹部準備好了。巧巧理所應當地一屁股坐在羊毛口袋上,馬幹部不知所措地看了一眼姚廣德,姚廣德咬著旱煙鍋子,目光凝視遠方。巧巧說,姐,你坐呀,我大腳力不好,咱坐坐就走。馬幹部坐下來,巧巧將一枝杏花別在她的耳朵上,然後稚氣地說,好看!
馬幹部微笑了一下,看到路畔子下麵的張能能也折了一枝杏花,不過那杏枝上已經沒多少花了,一半給驢嚼著,一半塞在了自己的嘴裏。馬幹部一瞬間,心上好像被揪了一下,想說什麼,後麵的姚廣德開口了。姚廣德說,馬幹部,你找我們家二能子學種棉花,那是英明的決定!為啥?我實話告訴你吧,我祖上在這一帶其實也種過棉花,我小時候,我爺還留著二畝地種著棉花,種著種著,我大抽洋煙,就把這茬給丟了,但是我還沒忘,我早些年也種過幾茬,咱這水土,種出來的棉花成色不咋地。
聽到姚廣德這麼一說,馬幹部精神立刻煥發起來,她趕忙轉過身,詢問姚廣德,那你記不記得咋個種法?姚廣德說,你是南方人,不曉得咋種棉花?馬幹部不好意思地說,我家在南方,可我從小在城市長大,見都沒見過幾次棉花的樣子。姚廣德問,是資本家吧?姚廣德的語氣突然變得怪異起來,好像他突然成了審問馬幹部的人,語氣裏帶著明顯的鄙夷和居高臨下的勝利感。姚廣德有些忘形,口水嗆了一下,不知是笑還是咳,半天才緩過來說,那咱是一類人嘛,資本家的大小姐也能革命?馬幹部這才轉過彎來說,姚廣德,注意你的態度,我們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我早就脫離我的家,我是為了真理奔向延安,與我的出身沒有關
係!姚廣德點了點頭,一聲 “噢”字拉得很長,明顯的不服氣。
四區鄉公社在延河邊的半山腰上臨時挖了十來孔窯洞,院子裏還有新土。文書小楊還在新土上翻騰,看到馬幹部回來,連忙打招呼說,馬幹部咋才來呀,老遠照見你了。馬幹部走過去看了看新土上的坑說,這是弄啥麼?小楊說鄰居閆幹媽送了些木槿花籽種上,鄉長不讓種,說不如種些向陽花籽,我偷偷種了點,木槿花耐活,要是開了花,秋天美得很。馬幹部笑了笑說,鄉長覺得活下來更重要。小楊說,活得像花一樣,讓反動派嫉妒去吧!馬幹部又問,都走了?小楊說都下鄉去了,你們趕上明天報道就行。又問,這幾個老鄉都是去學習班嗎?馬幹部說,也不是,不要多問了,有啥吃的沒?小楊一笑說,早上給你留了一點幹糧,在灶房呢,自己拿。馬幹部走過幾孔土窯洞,進了最邊上的灶房裏,一會拿出兩個巴掌大的棕色的窩窩,分成四份給了大家,最後一份給了張能能,張能能看了一眼姚廣德,姚廣德厭惡地說,吃麼,這是公家的飯。張能能試探地接在手裏,驢不高興了,頭一甩,棕色的窩窩掉在了新土上。姚廣德狠狠地罵道,這窩窩還吃不下個你?幹部還沒當,尾巴就翹天上去了?還不去攆你祖宗?!張能能也顧不得那驢,在土疙瘩裏找窩窩,找著後連土帶泥揣在懷裏,跑下了坡,姚廣德也跟了下去。
小楊好奇地指著遠去的三個人,看著神情複雜的馬幹部,問她,這村裏選的這是什麼人啊?他背上背著啥?馬幹部說,洗腳盆。你忙吧,我先走了,你不是還有一個水壺嗎,借我一下。小楊說,送你了,盡管拿去用。我整天在這兒值班,你要是拿上它,才算是革命的水壺。馬幹部也不客氣,將掛在窯洞門框上的水壺摘下來,搖了搖,笑著說了聲謝謝走了。
馬幹部趕到河邊的時候,姚廣德和巧巧正在啃那窩窩,啃得有些吃力,姚廣德說,你們幹部就吃這?馬幹部說,咋了?姚廣德沒說話,但是表情很鄙夷,還有幾分嘲諷地唾一口說,還夾了石頭,你這灶房不實在。馬幹部說,困難時期,這也難免,大家生活都艱苦,困難是暫時的!馬幹部的話有些生硬,她沒有告訴姚廣德這些窩窩本不該屬於她,更不屬於她們,她隻是覺得張能能可憐,才跟文書小楊開口,她看了一眼張能能,張能能的白羊肚手巾散亂,似乎被撕破了,臉上也有抓痕,顯然是挨過打了。馬幹部走到張能能跟前,看著他的傷,張能能慌忙低下頭,不敢看馬幹部。馬幹部憤怒地瞪著姚廣德,姚廣德先開了口說,馬幹部我認識到一個問題!馬幹部說,啥問題?姚廣德略帶哲思地說,穿白衣服的那些官,不把老百姓當人,你們這些穿灰粗布的娃娃們不一樣!馬幹部說,你的認識提高了!哪不一樣?姚廣德笑眯眯地說,咱一邊走一邊說,順路踢了張能能一腳說,你看,那些白軍是連哄帶騙,其實是給有錢人辦事,我嘛最有體會,給點錢就給你個議員當當。你們的政府不吃這套,整天和窮鬼,不不不,窮人在一起,從來沒有瞧不起過任何人,你看,我這樣的地主,也能吃上你們公家的窩窩哩!聽到這個頑固的姚廣德能這麼說,馬幹部似乎看到了改造姚廣德的希望。姚廣德是不是二流子?這個問題其實糾纏了馬幹部很長時期,最後考慮到姚廣德年齡比較大了,就沒有把他列為二流子。這點上來說姚廣德心裏記著馬幹部的好,同時也是他這次有些放肆的理由。馬幹部這才回過神來,看著姚廣德厲聲說,你剛才是不是打了張能能?姚廣德說,沒啊,他那小子就是個賤皮子!三天不打皮癢得很。馬幹部說那也是個人,而且是我們窮苦人的代表!姚廣德,你要是再動手,立刻給我回張家圪嶗去!姚廣德看到馬幹部惱了,知道事情敗露了,琢磨著怎麼辦的時候,一抬頭,馬幹部在他眼前怒視著伸出手來。巧巧慌忙過來勸說,姐,我大又說錯啥話了?馬幹部說,不是說錯了話,是壓迫,剝削!把剛才的窩窩給他!你有幹糧為啥還要霸占?姚廣德看到馬幹部真生氣了,隻得訕笑著說,存點餘糧,習慣了,本來就是你們公家的東西嘛,給誰吃不是吃嘛……馬幹部接過姚廣德交出來的那塊窩窩,走過去拉起張能能的手來,將窩窩塞進他的手心裏,這一次張能能似乎也發泄似的,隻幾下就塞進了嘴裏,也不怕噎著,腦袋搖晃著,羊肚子手巾幾乎快掉下來的樣子,大搖大擺從姚廣德和巧巧麵前走過,又走到了三個人前頭。
姚廣德呸了一口,罵了一句,什麼東西嘛!
水越來越寬,終究是要流向延河,流向黃河,最後奔向大海。小河裏的冰已經融化得看不到影子,但河麵還是有些堅硬。前麵的張能能一邊走一邊唱著:
一壺壺燒酒兩碟碟菜,一樣的朋友兩樣待。 山裏的石頭灣裏的水,什麼時候得罪了你。吃了碗扁食沒喝一口湯,沒一次主意上了人家當。
過了這條河,又是一道坡,坡上春風吹拂過,那些川道坡口的杏花,沿著風的手掌灑遍了半個坡,山坡粉紅了嬌嫩了妖媚了。馬幹部回頭看了一眼巧巧,巧巧又噘著嘴,氣哼哼地衝張能能喊,別唱了!唱得跟驢叫一樣!
歌聲戛然而止。
爬上了坡,轉過了峁,又是一片樹林。這條路,通著好幾個村子,算是大路了,從這條路再翻過幾座山,那就是縣政府。巧巧不好意思地走到姚廣德的跟前說了句什麼,姚廣德看了一眼張能能,把張能能叫到跟前來說,倆女人要逃茅子哩,你去幫著看人去!逃茅子就是上廁所,這山野,哪有廁所?隻能找個避風的地方去。兩個人遠遠地站著等。張能能說我不去。姚廣德說,你不去?難道讓我去?我一個老漢去了,馬幹部不方便嘛!再說了,萬一出個啥事,我老漢能頂得住了?那是個幹部哩,我得燒香供著!說了這些,張能能還是兩個字 “不去!”姚廣德就惱了,又是一個飛腳起來,張能能連人帶盆翻滾在地。遠處的馬幹部要過來阻攔,巧巧拉住她,好像在說什麼,馬幹部隻好作罷。
姚廣德拉著驢,指著兩個女人說,快去!張能能還猶豫,姚廣德又要來一個飛腳,張能能躲開說,你別怨我!姚廣德說,我許了就是許了,以後你也是幹部,跟以前不一樣了!還有,不準偷看!張能能低著頭 “哦”了一聲,低頭轉身走到兩個女人跟前。巧巧說,那邊有個大水渠,我倆就去那邊,你在那棵樹跟前站著!
巧巧的意思是站著把風,張能能自然明白,兩個女人還沒過去,他自己就先走到樹跟前,蹲下來,不看兩個人。巧巧拉著馬幹部就走,臨到樹跟前的時候,踢了張能能一腳說,不準偷看!張能能沒說話,巧巧拉著馬幹部走到深水渠,四處看了看,這才放心地跳下去解手。
張能能唯有這件事敢跟姚廣德叫板,那是有特殊原因。張能能剛到姚廣德家裏的時候才四五歲,從身體和心理來說都不諳世事,但是,張能能長到十來歲的時候,身體和心理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開始意識到,整天一個炕頭睡覺的巧巧這輩子就是自己的婆姨了。他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這個世界了,包括巧巧。他開始睡不著覺了,睡不著的時候,他偷偷看生病睡著的巧巧,巧巧的眉目,巧巧的胳膊和腳,巧巧的身體……
這一切開始都是暗中進行,後來,他膽大起來,他認為這是自己的婆姨,所以巧巧也是自己所有。在姚家,他最後唯一能夠得到的東西就是這個女人。他大著膽子摸了一下巧巧的腳,巧巧咯咯地笑了起來,醒了。他趕緊裝作睡著的樣子,讓巧巧以為這隻是夢境。他嚇壞了,好幾天再也不敢看巧巧。但從此,巧巧成了他心裏一塊油膩膩的肥肉,他吃不得,又時時刻刻想著,他不知道該怎麼下手,又不由自主地想著盼著探著,這磨人的巧巧,讓他厭惡起自己來。他又試探著摸了巧巧的手,摸著她的臉,他不由自主地親了一下巧巧。張能能昏昏沉沉地把這一切做完後,心裏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原來他對於 “婆姨”的概念一直停留在一起能 “玩耍”的概念裏,從此以後,巧巧成了他心驚肉跳後的一種坦然和巨大的平靜,成了他即將青春期的巨大 “誘惑”。
這件事情,他做得隱秘,做得陶醉,沒兩個月,巧巧意外醒來,發現了這個秘密。巧巧生氣了,巧巧負氣將這件事情告訴了她媽,姚老婆就轉告了姚廣德。姚廣德一聽,這事不得了了!狗日的張能能這是長大了,這是要提前揭鍋漏氣麼!這還了得?姚廣德第一個舉動就是把巧巧和張能能分開,讓巧巧單獨睡一個窯裏,張能能扔驢圈裏!而後,把這小子吊在驢圈口上,猛打一頓!張能能被脫光了衣服,吊在驢圈口的椽梁上,挨著牛鞭子,像被摁住的一頭豬一樣號叫著。張家圪嶗有幾個村民來圍觀,又不忍心看下去,又都默默地離開了,誰也不敢多說什麼。畢竟張能能是姚家的人,姚家的家事誰敢過問?張能能不問為啥挨打,姚廣德也不說為啥要打,互相心裏都明白。張能能此時已經有了羞恥心,光著屁股當著眾人的麵挨打,這件事本身對他來說,那是莫大的恥辱。可他還必須咽下這口氣,忍住這種恥辱,反倒覺得沒有那麼疼,沒有那麼難以忍受。
姚廣德打完張能能,從此心裏就多繃了一根弦,他很清楚, 張能能從此不再是娃娃了,那是個隨時都可能要爆發的火藥桶,隨時都會翻牆跑進他防線的狼!他在內心給張能能畫了一條線,這條線他不能逾越,否則就是牛鞭子!牲口和人一樣,必須得用鞭子把他吆喝順溜了,要不然以後長大了,不好使喚!哪個牲口不是這麼吆喝順溜的?現在張能能正是皮癢癢的年齡,這個時候不吆喝順溜,以後就永遠別想管得住他!通過幾年的吆喝,張能能還確實如他所願,終於被他打順溜了,張能能也差不多脫了一層皮,巧巧也更任性了,但總的來說,他的滿意,才換來了張能能的今天,否則,他是絕不能讓他娶了巧巧。
張能能的言聽計從裏,那是牛鞭子揮舞的壓迫,也逐漸失去了對巧巧的親昵,在他的眼裏,巧巧已經不是當初他伸手摸出的感覺,而是一個蛇蠍一樣的怪物,和她大一樣,把他當作一頭牲口。這種話,他不敢說,但是敢想。
馬幹部和巧巧從水渠裏出來,張能能慌忙低著頭走過拐角, 去找姚廣德拉自己的驢。馬幹部心裏的疑惑越多了,卻不再多問什麼。
翻了兩座山以後,姚廣德故意試探地說,馬幹部,到了縣政府,天就黑了,離膚施城還遠哩。馬幹部說,縣政府休息一宿,明天再去膚施城。馬幹部說完,又覺得沒有說清楚,特意解釋說,張能能得去縣政府報道哩,後天你們要是想去膚施城,你們去,他必須在學習班學習哩。姚廣德說,這我曉得哩,他大小算是個幹部哩,我們等他,他啥時候學習完了,我們再回去。馬幹部說,可縣政府隻提供他一個人的食宿。姚廣德說,我曉得哩,縣政府周圍總有歇腳的騾馬店吧?馬幹部說,有倒是有!姚廣德說,費用我們自己承擔,你不用擔心。
馬幹部想了想,然後說,要不我找個地方你倆住下來,住店太貴了。巧巧攔了一句話說,大,要不咱先去膚施城,我想買衣服。姚廣德瞪了她一眼說,馬幹部對咱好,咱要識抬舉哩,那就讓你費心哩。馬幹部說,這是應該的,我來張家圪嶗,你對我也挺好,以後啊,咱就是一家人,別客氣。姚廣德一聽馬幹部這麼說,高興得抿不住嘴說,我就愛聽你們幹部說這話,是一家人麼,你還要給巧巧和能能當媒人哩,請你當媒人,就是沒有把你當外人嘛,都是自家人。嘿嘿嘿,巧巧,你看好馬幹部的鞋,咱得給你買一雙腳,當媒人這是規矩。
馬幹部一聽,立刻正色道,啥?那不行!我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買一雙鞋,那我夠槍斃了!姚廣德看到這事突然又變了,趕忙勸馬幹部說,你以前不是說入鄉隨俗嗎?當媒人在咱這地方有講究,意思是你為了兩個娃,跑了腿,磨了嘴,這是謝意,要是不拿那就等於咒我兩個娃散夥嘛。
馬幹部耐心聽完姚廣德的話,態度還是很堅決:不行!那是舊鄉俗,現在是新社會。為老百姓辦事,那是我們幹部應該做的事情,你給我一雙鞋,那是等於賄賂!嚴重違反紀律,那我這個幹部還當不當了?馬幹部又說,隻要他倆進步,我就高興。姚廣德說,那咋行……馬幹部說,這事沒得商量,若要我做媒人可以,但是你有任何想法,我就不做了。姚廣德趕緊說,行行行,都聽你的,你是幹部懂得比我們多。哎呀,我這老姚家幾輩子修來的福氣,能趕上這麼好的社會,這麼好的幹部嘛。到時候,你可要來主持,要來吃席嘛。馬幹部說吃席就算了,我可以幫兩個娃娃講兩句。姚廣德不敢多要求,趕忙說行行行,按你說的辦。
翻過這道山,下了這道坡,溝槽就平坦了,眼亮了,就能看到縣政府的窯洞。此時正是黃昏,夕陽亮堂堂地隱入山巒,河水蓋了一層金黃,河邊有了綠色,柔和起來,人的心境也開闊起來。馬幹部指著溝口錯落有致的房子和窯洞,掩飾不住內心的欣喜,十分清脆地說,你們看,咱的縣委縣政府就在溝口子上,緊走兩步,馬上就到了。姚廣德不明白馬幹部為何如此歡欣,巧巧跟著心情也敞亮了,拉著馬幹部的手緊跟其後。姚廣德看著張能能愣著神,看西洋鏡一樣,心下有些不滿地踢了他一腳說,你別高興得太早,就算當了幹部,你也是我的牲口!姚廣德說完走了,張能能心上像被他潑了一勺子涼水一樣的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