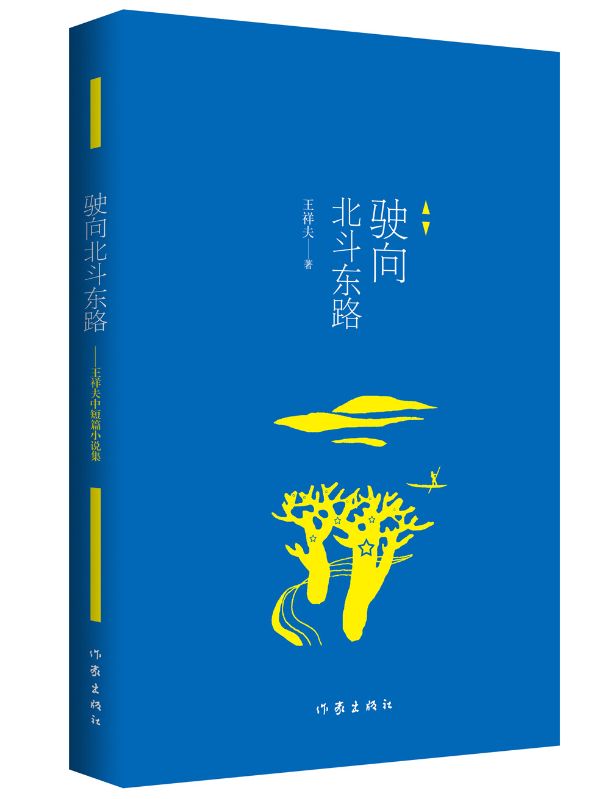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七章
A型血
小美輕輕捅了小陶一下,小陶掉過臉,A型血正朝這邊走過來,這個年輕人,猛看上去像是特別的高,但隻要是細看,就會明白他其實不是高,而是比別人窄了許多。因為他沒有雙臂,所以走路有些扭。
“他沒有可以讓自己保持平衡的雙臂。”小美對小陶說。
小美和小陶都是采血車上的護士,她們的車每天都會停在幾個固定的點兒上,這都是上邊的安排,血站有十多輛她們這樣的采血車,當然都是白色的。她們都在背後把采血車開玩笑叫做“吸血鬼”。采血車內部其實就像個小診療所,有桌子和椅子,都是金屬的,而且都漆著白漆。她們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采血化驗再采血再化驗單調得很,就是這樣,她們認識了不少人,她們對前來獻血的人一般來說都有好感,而前來獻血的人一般來說年輕人多一些,還有就是中年人,很少有老年人來到她們的車上。小陶就是在采血的時候認識的這個沒有雙臂的年輕人,小陶和小美背後都叫他A型血。雖然她們都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因為她們會對前來獻血的人進行詳細的登記,還會發給他們一個小本子,按照規定,持有這種小本子的人一旦需要輸血是免費的。怎麼說呢,獻血的人就像是給自己儲存了一大筆錢在那裏,什麼時候需要都可以取出來。雖然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這一輩子都不會接受輸血,但許多人都願意讓自己的血流到別人的身體裏去幫助別人。這也許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假設某個獻血的人死了,不在人世了,但他的血也許還會在某些人身上流淌,也可以說,他還活著。
第一次給A型血采血的時候,小陶很緊張,她還從來沒接觸過這樣一個沒有雙臂的人,她也沒有從一個人的腳腕處采過血,A型血既然沒有雙臂,采血隻好在他的腳腕上進行,他也隻能坐在那裏,把一隻腳抬起來放在另一張椅子上。她那天眼睜睜看著他把鞋子熟練地脫下來,用另一隻腳脫這隻腳上的鞋子,簡直是靈巧極了,然後再用另一腳把穿在腳上的襪子也脫下來,這一切都做得十分利索,讓小陶想都想不到A型血的腳指竟然會像手指一樣的靈巧。那天小陶不小心還把一支筆掉在地上,正掉在A型血的腳旁,還沒等她彎腰,A型血已經幫她把筆揀了起來,是用腳,輕輕一下子幫她把筆揀了起來,並且又輕輕把筆放在了應該放的地方。她還聽到這個年輕人對自己說,“我是A型血。”她那時光注意這個年輕人的那隻腳了,她知道這個年輕人的腳就是這個年輕人的一切,他的一切事都離不開他的腳,但她不知道這個年輕人怎樣用他的腳吃飯、穿衣、喝水、寫字,當然還會有更多瑣碎的事。後來她看到年輕人用腳趾夾了筆在那裏寫字,而且,怎麼說,字寫得居然很好。她還注意到年輕人的腳長得十分好,腳趾像是比一般人的長,腳的大拇指和第二個指頭十分靈活,指甲也剪得很好,她很想問一下是什麼人給他剪腳指甲,她那時候以為他肯定不會自己給自己剪,但後來她明白自己錯了。怎麼說呢,現在小陶隻要是一看到A型血,不知為什麼,心裏總是一緊,她太想知道A型血是怎麼生活?怎麼吃飯和喝水?還想知道是什麼人在照顧他的起居?
A型血性格其實很開朗,總是愛找人說話,喜歡問上車獻血的人是什麼血型,而且會馬上說自己是A型血。就是這個年輕人,來她們車上獻血已經很多次了,每次來了,坐下,脫鞋,用一隻腳給另一隻腳脫襪子,再用腳趾夾著襪子把襪子放在鞋裏。采完血,再用一隻腳給另一隻腳穿襪子,用腳趾,把襪子穿好,再穿鞋。有一次小陶想給年輕人腳腕處的針孔用棉球多按一會兒,當護士這麼多年,她才知道,在腳腕處采血,針孔的血竟然會一下子流出來那麼多,她嚇了一跳,也許這與地球引力的作用分不開?但A型血已經用腳趾把棉球按好了,用他的第一個腳趾和第二個腳趾,十分靈巧地夾著小棉球。
“我還能做點兒什麼呢?”A型血有一次很傷感地對旁邊的人說,旁邊那個人已經獻完了血,用一個手指按著小棉球兒。
A型血的這句話讓站在一邊的小陶心裏特別難受。
“我也隻能為別人做這麼一點事。”A型血說。
小陶馬上轉身給A型血倒了一杯加了糖的水,車上的杯子都是那種紙杯,很軟。後來那杯水就一直放在那裏。一般來說,獻完血的人都習慣喝一杯加了糖的水。
小陶已經想了好久了,她很想請A型血吃一次飯,這個念頭來得特別強烈,但A型血總是一個勁地搖頭,總是不肯,而且臉都紅了。小陶對他的不肯做了許多猜測,也許是A型血根本就不願意讓別人看到他怎麼吃飯?因為他沒有手,沒有雙臂當然不會有手,他的吃飯也許是個天大的秘密,他怎麼吃飯?小陶還問過小美,小美說大概是用腳吧?這種人幹什麼都用腳,小美說好像在電視上看到過一個人在用腳吃飯,當然到時候頭要拚命朝前伸,“就這樣,像隻鴨子。”小美說那樣子可不怎麼好看。小陶想小美說得也許對,也許A型血吃飯就是那樣子,所以他才不願意讓任何人看到他吃飯的樣子,所以他才不肯接受小陶的邀請。
也就是昨天,下著雨,A型血來了,他沒辦法打傘,又不能一直待在車上。小美抿著嘴在看車上的那台小電視,司機在打瞌睡,嘴張得很大。小陶就打著傘送了A型血一下。雨其實不算大,隻不過梧桐樹的大葉片把小雨滴都變成了一大滴一大滴,打在傘上“嘣嘣”亂響。因為兩個人打著一把傘,小陶和A型血挨得很近。小陶又對A型血說起吃飯的事,“吃飯的時候我可以幫你,你也許還沒在飯店吃過飯吧?”A型血說我的腳很好使。小陶說再好使你也不可能在飯店裏用腳吃飯。A型血笑了一下,說腳就是我的手,不過我挺能吃。
“那就定了?”小陶說。
“好吧。”A型血說。
小陶問小美願不願意一起去,小美想了想說還是下次吧。小美問小陶,為什麼非要請這樣的人吃飯?問題是他到時候怎麼吃?小美的話讓小陶忽然很難受,她坐在那裏,看看自己的手,又摸摸自己的雙臂。忽然覺得自己已經沒了雙臂,怎麼吃飯?怎麼洗臉?怎麼梳頭?怎麼去廁所?怎麼穿衣服?這麼想著,她心裏就更難受。“這種人一般都活不長。”小美又在旁邊說。小陶在車窗玻璃上用手指劃了一下又劃了一下,又劃了一下,下雨的時候外邊比較冷,車窗的玻璃上都是水汽。小美又在一邊說,說A型血這種人既不能旅行,也不能遊泳,跑步也不太可能,因為他們根本就沒辦法讓自己保持平衡。小美也看著外邊,下雨的時候很少有人前來獻血。小美接著說,“這種人最好一輩子都在家裏待著,如果沒人照顧他們他們就死定了,問題是誰能照顧他一輩子?”
小美說恐怕沒人會嫁給這種人。
“也許從來都沒人請他吃過飯。”小陶說。
“你注意到沒注意到他從來都穿沒鞋帶兒的鞋?”小美說。
小陶拿起杯子,到車後邊去了。她決定了,讓王生和自己一起去。
其實三個人吃飯根本就不用看菜單,但小陶還是讓服務生拿來了菜單,她先把菜單推給了A型血,她沒給王生,王生是小陶的男朋友,在把菜單推給A型血的時候王生突然笑了一下。王生是請了假過來的,他也特別想知道A型血怎樣吃飯,他見過A型血,但他從來沒想到小陶要請A型血吃飯,他一時拿不準小陶是什麼意思。王生一笑,小陶就瞪了他一下,馬上又把菜單拿到了自己跟前,她不明白自己就怎麼忘了A型血根本就不可能翻動菜單。“我翻給你看。”小陶對A型血說。來飯店之前,她幾乎把所有的細節都已經想好了,她想好了,她要親自喂A型血吃,自己吃一口,再用A型血的筷子喂A型血一口,她當然想過A型血也許到時候會用腳趾夾了勺子往嘴裏送飯送菜。但即使那樣,她也會覺得沒什麼,所以一進這家飯店她就選了最隱蔽的地方。在這個隱蔽的地方,A型血就是用腳吃飯也不會被別人看到。她讓他坐在裏邊,她和男朋友王生坐在外邊。這樣一來,正好能擋住別人的視線。
王生坐下來,抽出一支煙要給A型血。
小陶看著王生,馬上要發作了。
王生“噢”了一聲。“那我也不抽了。”
小陶看菜譜的時候又聽見王生對A型血說:“來不來點兒酒?”
小陶馬上放下了菜譜,覺得自己這一次真的要火起來了。
“不過我們倆可以用一個杯子。”王生馬上對小陶說。
A型血說他不喝酒,酒會帶來麻煩。
“你從來都沒喝過吧?”王生不知道A型血說的“麻煩”指什麼?
“喝過。”
這出乎王生的意料,王生想那應該是一大杯啤酒,A型血把嘴湊過去喝,或者是,用一根吸管吸。
王生說。“飯店裏有那種塑料吸管。”
“我從不用吸管。”A型血說。
王生覺得自己一下子就興奮了起來,“那我們就來它一小瓶。”
小陶惱怒地看一眼王生,把臉轉過來對著A型血,“別聽他的。”
這時候旁邊的那台電視開始廣播天氣預報,南方都在下雨。王生讓服務員過來倒水,王生想把水給A型血端到嘴邊幫他一下,A型血說他自己能來。A型血低下頭把嘴湊到水杯邊吸了一下,這一口吸得很大,三分之一杯的水一下子就下去了。吸得時候,杯子傾斜了一下。接著A型血又吸了一下,杯子又傾斜了一下,再一下,杯子已經銜在了A型血的嘴裏,A型血把頭往後仰,一杯水就這麼喝光了,杯子銜在嘴上。
王生向兩邊望了望,他真希望有人看到這一幕。
王生低頭試了一下,他想自己肯定是來不了。
“我不行。”王生說。
“你要是跟我一樣你就會了。”A型血說。
王生在心裏說但願我下輩子也不要像你一樣。
當所有的飯菜都端上來以後,A型血和小陶還有王生他們三個忽然都不再說話。小陶和王生希望自己把注意力都放在飯菜上。小陶特意向服務員多要了一雙筷子和一把勺子,其實放在A型血那邊的餐具根本就沒用,A型血不可能使用它們。但小陶還是讓服務員給他備了一份兒。小陶是用那雙公用筷子給A型血夾菜,她想讓自己來得自然一些。小陶對A型血說:“這個菜挺好,來。”她把菜夾起來送到A型血的嘴邊,她很怕菜汁掉在A型血的衣服上。她注意到自己喂A型血的時候王生的那種神情。王生笑了一下。王生忽然覺得事情有些好笑,現在他們吃飯好像是出牌,小陶先給A型血夾一筷子,然後把那雙筷子放下,然後再拿起自己那雙筷子給自己夾一筷子。然後再輪到王生。平時吃飯,小陶和王生總是邊吃邊說話,可是這時他們都沒了話,不知該說什麼,隻有一種新鮮的感覺,那種感覺絕對不像是在喂一個人吃飯,而像是把一筷子一筷子飯菜塞到一個洞裏去。A型血總是把嘴張得很大,隻有這樣,筷子上夾的菜才不會掉在外邊。那是一個很大的洞,要是在平時,誰都不會注意人的嘴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洞,隻有你喂一個人吃飯的時候你才會發現那個洞其實很大。
“我是不是夾得太多了?”小陶說。
“正好。”A型血說。
王生在用他的勺子吃他麵前的那盤菜,王生說這盤青豆很好吃,你吃一下?王生這麼說話的時候小陶瞪了他一眼。
王生“噢”了一聲,馬上給A型血舀了一小勺。“來。”
“好不好?”王生說。
“不錯。”A型血說。
接下來,小陶把筷子拿混了,不是用自己的筷子喂了A型血,就是用那雙專門用來給A型血夾菜的筷子給自己夾了菜。小陶和王生都注意到了,A型血每吃一口菜都會把身子往前探一下,好像是以示禮貌,或者是他已經習慣這樣了,不這樣不行了。好像是,A型血的這個動作會傳染,王生吃菜的時候也把身子往前探,而且往前探得更誇張,小陶在他下邊踢了一下,當然是趁A型血沒注意的時候,A型血給自己麵前鋪了兩張餐巾紙,他低下頭用下巴把一個煙灰碟挪了一下,正好壓住了餐巾紙的一角兒,這樣一來他就能時不時低下頭把自己的嘴在餐巾紙上擦一下。
要酒的主意是飯吃到一半兒的時候小陶忽然又想起來的。剛才她不打算讓王生和A型血喝酒,可現在她突然打消了這個念頭。她覺得這頓飯是不是吃得有些沉悶?她希望A型血高興起來。這麼想的時候她的心裏就有些難受。因為她發現A型血並沒有高興起來,她在心裏問自己,“請A型血吃飯為了什麼?”
王生是那種酒量不大但隻要是一有酒就會話多起來的人。小陶讓服務生給王生和A型血每人上了一個小瓶。那種紅蓋子的小扁瓶。小陶其實也能喝酒,王生看著小陶,說你不來?王生一邊把酒倒在一個玻璃杯裏一邊又對A型血說小陶其實酒量比我都好。這時候服務生拿來了兩根白色的塑料吸管兒,小陶覺得自己不能端著酒杯喂A型血,這和吃菜不是一回事。
“用吸管喝酒其實也挺好。”王生說。
“我不用。”A型血說吸管是喝飲料的,隻有小孩兒和女人們才用。
小陶看了一下王生,王生看了一下小陶。
“這酒幾度?”A型血說。
王生已經把酒倒在了一個玻璃杯裏,A型血剛才用過的那隻。
“我能聞出來。”A型血說。
小陶不知道A型血這話是什麼意思,小陶想了想,讓服務生再上一小瓶。
“我陪你喝。”小陶對A型血說。
“是陪我們兩個。”王生笑著說你不能把我給忘了。
小陶發現A型血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A型血聞了一下杯子裏的酒,“45度。”
“我想你是看瓶子了。”王生說。
“酒瓶離我很遠。”A型血說。
小陶瞪了王生一眼,酒瓶已經被服務生拿走了,再說A型血也無法把酒瓶子拿起來看。王生對服務生說請你看一下酒是多少度?服務生連看都沒看,說這種牌子的酒都是45度。但服務生還是轉了一下身把空酒瓶拿了過來。小陶看酒瓶的時候王生忽然靠近了A型血,小聲問了一句什麼。
“我不去。”A型血的臉紅了一下。
王生站起來,離開桌子,去了另一邊,衛生間在那邊。
小陶對A型血說:“45度你沒事吧?”
A型血說沒事,“不過喝酒會找麻煩。”
小陶不知道A型血說的“麻煩”指什麼?
“你要去,就說話。”王生從那邊回來時,坐下來,又對A型血說。
“我這會兒不去。”A型血的臉更紅了。
王生用杯子碰碰A型血的杯子,又和小陶碰了碰,“今天有點像過節。”
A型血說,“謝謝謝謝。”
“慢慢喝。”王生說,他想看A型血怎麼喝他的酒。其實和剛才喝水一樣,A型血低下頭來,用嘴唇銜住杯子,讓杯子慢慢慢慢傾斜,他這口酒喝得很有分寸。
“你要是去,怎麼去?”王生接住了剛才的話題,他很想知道A型血怎麼去廁所小便,怎麼解褲子,怎麼再把褲子提起來,還有一些別的什麼細節,既然他沒有雙臂。
“你要是和我一樣你就會了。”A型血臉紅紅地說。
小陶不知道王生在說什麼,她看著王生,把手裏的杯子在A型血的杯子上輕輕碰了一下。王生也跟著碰了一下。酒讓王生忽然覺得自己已經跟這個沒有雙臂的A型血親近多了。A型血這會兒對王生來說簡直就是一個謎。王生接下來問了A型血許多問題。比如他平時怎麼穿衣服和穿褲子?怎麼洗澡?怎麼給自己剪指甲?王生每問一個問題,A型血總是那句話:
“你要是和我一樣你就會了。”
“洗衣服呢?”小陶在一邊說。
“用腳。”A型血說。
“燒開水?”小陶說。
“用腳。”A型血說。
小陶“啊”了一聲,“那可太危險了。”
“你們要是像我一樣你們就會了。”A型血說其實也沒什麼危險。
“你家裏還有誰?”王生又用手裏的杯子碰了一下A型血的杯子。
A型血把杯子慢慢慢慢用嘴傾斜了一下,喝了一點。
“洗碗是不是也用腳?”小陶說。
“我會用腳織毛衣。”A型血說你們要是像我一樣保證也什麼都會。
王生拍了拍A型血的肩膀,“問題是,我們永遠不可能像你。”
“你真讓人受不了!”小陶大聲對王生說。
王生不再說話,看著小陶。
小陶說人活一輩子誰都不會知道自己下一步是怎麼回事。
“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A型血說。
小陶把臉掉向了另一邊,誰也看不到她眼裏忽然有了眼淚,然後她去了洗手間。小陶去了很長很長時間,直到後來王生有些不放心,他抽了一支煙,接著又抽了一支。這個小飯店其實隻有一個衛生間,是男女合用,無論男女,進去後隻要把門從裏邊插住就行,裏邊點了一隻盤香,但味道並不怎麼好聞。
王生知道裏邊是小陶,他敲了好一陣子門。
小陶從裏邊出來了,眼紅紅的。這誰都能看出來。
“怎麼回事?”王生小聲說。
“你要是我你就會知道怎麼回事。”小陶說。
王生說我也沒別的意思。“你說我們能不能跟他一樣?你說?”
這頓飯吃下來,最後上來的是一盆湯,窗外的陽光把湯照得亮閃閃的。
“我剛才碰到個熟人。”小陶對A型血說,“那個人真是能說,沒完沒了。”
“我說什麼也要陪你去一下。”王生站起來對A型血說。
“我也真的該去一下了。”A型血臉紅紅地站起來,但他對王生說我不要你陪我,我自己什麼都能來。
小陶和王生早就住在一起了,他們是下午四點多回的家。小陶從廚房抽屜裏找出了一截繩子,她要王生把自己的雙手從背後牢牢綁住,“能綁多緊就綁多緊。”一直到晚上,小陶就那樣兩隻手被反綁著在家裏走來走去,她努力試著用腳做一些事,比如,用自己的一隻腳給另一隻腳脫襪子,脫下來,再穿上。比如,用腳開門關門。再比如,她還試著不用手端杯子喝水,低下頭,用嘴讓水杯慢慢慢慢傾斜下來,再慢慢慢慢把杯裏的水喝光。小陶還試著用腳指夾東西,她把一支筆放在地上,夾來夾去,夾來夾去。
王生一直在那裏看電視,兩隻腳蹺在玻璃茶幾上。他想好了,要是晚上小陶還堅持不把綁在雙手上的繩子解掉的話,那麼他要先洗個澡,那也許是種全新的體驗。但他想小陶到時候也許會不同意,他明白小陶此刻心情不是太好。
“請A型血吃飯,小陶是對的。”王生還在心裏想,自己在吃飯的時候說話有沒有不對的地方。王生還想,自己什麼時候也應該去獻一回血,從腳腕那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