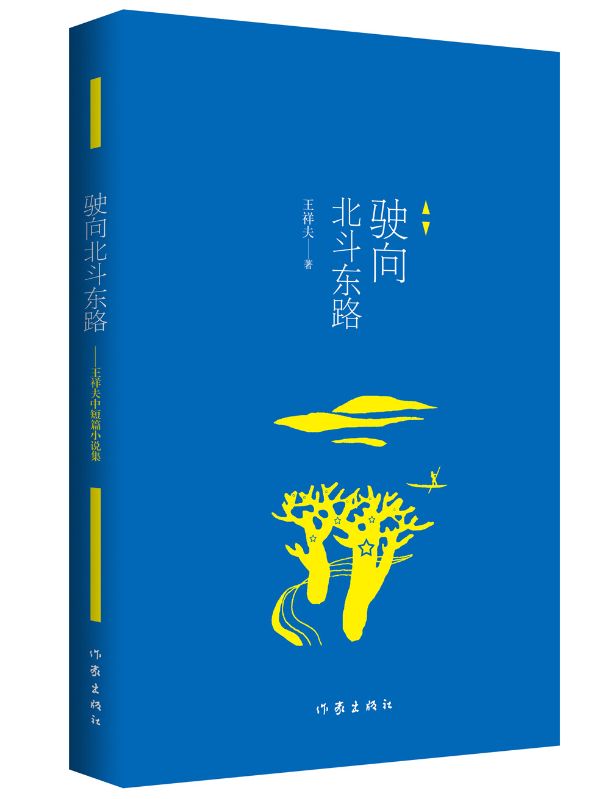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蜂蜜
“你們現在就來吧。”
安莉在電話裏說要給張北和小晨看樣東西。張北在電話裏想知道安莉想讓自己看什麼東西?但安莉說你們來了就知道,“你們如果沒事就馬上來吧。”
張北放下了電話,他覺得自己應該收拾一下。他給自己換了一條褲子,接電話的時候他正在收拾院子,把去年的枯枝敗葉堆在一起燒了,煙一條線地冒上去,天氣很好。他想不到安莉會給自己打電話。安莉的命真夠苦的,先是男人得了那種病,花完了家裏所有的錢,也花完了朋友們能夠支持給他的錢然後就去了另外的世界。安莉和她的男人和張北都是很要好的朋友,當然還有小晨,當年他們總是在一起聚會或者是去河邊野餐,在河邊野餐的好處是男人們可以去釣魚,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運氣好能釣到一條或者幾條很大很大的草魚,魚釣上來可以直接架在火上燒烤,但那時候他們總是隻能釣到一些很小很小的小東西。
安莉的命苦還在於她男人住院的時候她的孩子忽然不見了。也就是說她把自己的孩子給弄丟了。當時朋友們都不太在意安莉的孩子去了什麼地方?怎麼會很長時間沒露麵?都以為是安莉的親戚或者是她男人的親戚把孩子給接走了,因為那時候安莉和她男人都顧不上他們的孩子。直到後來安莉對朋友們宣布說孩子丟了。朋友們當時的吃驚不亞於聽到什麼地方發生了九級大地震。朋友們都責怪安莉為什麼不通知他們一塊去找?安莉說她當時已經昏了頭,醫院裏的事讓她身心交悴。緊接著安莉的男人就去世了。再見著安莉的時候張北和小晨還有安莉別的朋友們都吃了一驚,安莉幾乎比以前瘦了一大半,頭發也剪短了,感覺是不能再短,而且還學會了抽煙。不怎麼說話,坐在那裏一根接一根地抽。那是一次聚會,朋友們說把安莉也叫來吧,讓她從悲傷中慢慢過來吧,男人死了,孩子也丟了,得讓她從悲傷中慢慢過來。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朋友們在網絡和街道上到處發尋找孩子的消息。張北對自己愛人說“是時候了”小晨說“是什麼時候了?”張北說“是到了幫安莉把孩子找回來的時候了。”那一陣子,安莉的朋友們隻要一有工夫就到處去貼尋人啟事。如果能找到那孩子,那孩子差不多快到五歲了。安莉的孩子小名兒叫兔子。
“小晨”張北說安莉讓你和我一起去看她的東西。
“我想去做頭發。”小晨說她會有什麼好東西?
“也許是她給你搞到了一箱蜂。”張北說。安莉的一個親戚在蜜蜂研究所工作。小晨一直想在院子裏養一箱蜂,到時候就可以吃到最純淨的蜂蜜。張北也喜歡有蜜蜂在院子裏飛來飛去。
“給她帶些蔥。”小晨說,“還有你的水蘿卜。”
“我的水蘿卜?”張北咧開大嘴笑了一下。
“當然是你的。”小晨伸手在張北身上輕輕劃了一下。
“我的水蘿卜?”張北笑著說,“那是你的專利。”
“張北——!”小晨尖叫起來,看著張北。
“好好好,不說了。”張北說。
“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小晨說。
蔥和水蘿卜都是張北在院子裏種出來的。
不知為什麼,張北和小晨都隔著窗子朝那地方望了一下。
張北說,“蔥老了就辣了。”
小晨說想不到蔥開花是那個樣子,“像個絨球”。
張北又朝院子那邊看了一下,那棵樹下有隻很大的棕色塑料桶,他總是徑直走過去往桶裏撒尿,那隻桶很大,去年漚的草葉還在裏邊,現在都已經變成了很好的肥了。他總是把這種肥施給院子裏的植物,包括蔥和蘿卜。
“你這條褲子也太瘦了。”小晨對張北說看看你那前邊。
張北說鞋也不行了,“沃爾瑪那邊褲子和鞋都很便宜。”
“你想不出她想讓咱們去看什麼東西?”小晨說。
張北說電話裏她又沒說,“如果不是一箱蜜蜂,那會不會是一隻貓?”
“記住,她不提,你最好別說兔子的事。”小晨說。
“現在去是不是有點早?”張北的意思是,晚去一會兒,晚上一起吃飯,請安莉出去一起吃晚飯,安莉夠可憐的。
小晨看著張北,“到時候她又哭怎麼辦?”
“那就算了。”張北說自己無所謂。
小晨不知想起了什麼,忽然笑了一下。
張北把一隻手放在小晨的腰上,還有另一隻手。
“安莉現在也不用減肥了。”小晨說。
張北卻笑不出來,有一陣子,那時候安莉家裏還沒出任何事,安莉還很幸福。她雖然不胖,卻經常說減肥的事,雖然誰都知道她根本就花不起那個錢。她和她丈夫那時候工資都很少。
“你這話一點點都不好笑。”張北說。
“我隻是想說壞的事總會有好的一麵。”
“她現在肯定想讓自己胖一些,再胖一些。”張北說,兩眼看著外邊,那一隻鳥想在牆邊的那株樹上築巢,這時候又飛來了,銜著一根又細又小的樹枝。“說不定她也許真養了一隻貓?”有一次聚會,張北勸安莉養一隻貓,到了晚上貓會睡在枕邊打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呼嚕。
“那你就變成一隻貓吧。”小晨說。
“可我是你的貓。”張北說。
敲門的時候,安莉在屋裏小聲問,“誰?”
“呼嚕、呼嚕、呼嚕、呼嚕。”張北在門外說。
張北沒再像以前用一個手指把貓眼堵住,以前他總愛開這種玩笑。有一次,他在外麵用手指堵,安莉的男人就是不開,一直僵持了好長時間,後來弄得好像誰都不開心。安莉的男人說“你這樣做不好,要是個壞人呢?安貓眼就是為了看一看外邊是什麼人,你這樣不好。”安莉男人去世已經一年多了。他再也沒有可能去釣到一條很大很大的草魚。用安莉男人的話說草魚最好能大到一人高,然後他會把它切成塊醃起來,這樣一年到頭就會總是有醃草魚吃。安莉的男人現在去了另一個世界,另一個世界可能也沒有那麼大的草魚。
開門的時候,安莉在裏邊小聲說“快進來,快進來,快點。”
張北讓自己愛人先進,她提著東西。
“快進來,快進來。”安莉又說。
張北覺得自己的猜測也許是對的,肯定是安莉在家裏養了一隻貓,有些貓隻要門一開就要往外跑,而有些貓永遠沒有往外跑的意思,不想跑的這種貓往往是越吃越胖。但張北沒看貓。緊接著,張北和他愛人卻看到了那個小孩兒。一隻手放在嘴一隻手拿積木在那裏站著,看著他們。他剛才肯定是在玩積木,他好像被張北和小晨嚇了一跳,就那樣呆呆看著他們。這孩子的腳下是那些積木,那是一些舊積木,各種顏色的木塊兒,可以搭汽車也可以搭房子。張北記著自己和安莉的孩子用這種積木一起搭過房子,那些積木房子總是搭著搭著就“嘩啦”一聲垮掉。出去野餐和釣魚的時候,安莉也會把孩子帶去,隻不過那時候孩子更小,沒有人抱他的時候就把他放在鋪在草地上的塑料布上。但一般情況下,總是大家輪流抱他。
張北聽見小晨已經尖叫了起來,“啊,兔子!”
“小點兒聲小點兒聲。”安莉說。
“怎麼找到的?”小晨看著安莉。
“小點兒聲小點兒聲。”安莉說。
“你在電話裏也不說,我們應該給兔子買點東西。”小晨又說。
“喝茶不喝茶?”安莉說。
“兔子,兔子,”小晨又對那個孩子喊,一邊把鞋脫了。
那孩子退了一下,看著張北和小晨。
“過來。”小晨說,蹲下來。
那孩子退了一下,再退,沒地方了。
安莉的臉彤紅彤紅的,她去了廚房,從廚房把那隻藍玻璃煙灰缸拿了過來。煙灰缸擦得很幹淨,也許安莉現在已經不再抽煙了。安莉又去了一下廚房,安莉在廚房裏不知道洗什麼,水的聲音,“砰”的一聲,又是一聲什麼。
小晨拿了一塊積木,但她手裏的積木一點一點攥緊了,她已經蹲在了孩子的旁邊,她想看看孩子的模樣有了什麼變化,但她馬上就明白了眼前這個孩子不是兔子,她一眼就認出來了,這不可能是兔子,光看耳朵就不是兔子。張北卻側著臉看著廚房那邊,張北對廚房那邊說:“你現在是不是不抽煙了?”安莉把什麼又掉在了地下,“砰”的一聲。又是水的聲音。
安莉從廚房裏出來時,手裏卻什麼也沒拿。
“你在廚房做什麼?”張北說什麼東西掉地上了。
“我洗了一下手。”安莉說。
“什麼東西‘砰’的一聲。”張北說。
“我隻是洗了一下手。”安莉說。
“你現在不抽煙了?”張北說。
“兔子和以前不一樣了吧?”安莉有點兒結結巴巴,看著小晨。
小晨深深吸了口氣,她看著安莉,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跟以前不一樣了吧?”安莉又說。
小晨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她想讓張北也看一看兔子,她想對他說這個兔子可不是以前他們人人都抱過的兔子。起碼耳朵就不一樣,兔子的耳朵很大,所以安莉的朋友才都叫他兔子。
安莉又去了廚房,她說應該做壺水。“喝茶。”
“你好好兒看看。”小晨小聲對張北說,“看耳朵,這根本就不是兔子。”
小晨脖子那地方馬上感受到了張北的呼吸,張北哈腰站在了她的身後。“我記不起來了。”張北說。張北說的是實話,所有的小孩兒在他眼裏幾乎都一樣,除非這小孩兒有特別的地方他才能夠記住,比如這小孩兒的臉上有顆痣,或者是留一種特別的發型,總之,張北現在還不太喜歡孩子,所以他不記,但張北能記住各種魚的名字,隻要一有魚釣上來,他馬上就能把魚的名字叫上來,說實在的,張北他們總是釣魚的地方也沒什麼魚,也隻是那麼三四種。
“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保證能記住。”張北又說,“怎麼回事?”
這時候安莉在廚房裏接水,能聽到水聲。
張北現在還沒有孩子,小晨對張北說托兒所那麼多孩子,要是到了以後記不起來哪個是自己的孩子可怎麼辦?這讓他們既困惑又有些害怕。因為張北和他愛人總是記不住小孩兒。朋友的小孩兒他們都記不住,小孩兒在他們的眼裏幾乎都一樣,當然這是小孩兒,三四歲,五六歲的小孩兒。“也許咱們自己有了就好了。”張北說。安莉這時候從廚房出來了,她接了一壺水,坐在了煤氣灶上。安莉的男人去世後,朋友們特意為她換了一把壺,是會叫的壺,隻要水一開就會尖利地叫起來。就像救火車忽然開到了家裏。那時候,幾乎是安莉所有的朋友都為安莉總是恍恍惚惚擔心。
“怎麼樣?我的兔子。”安莉的臉不那麼紅了。
“什麼怎麼樣?”小晨說。
“兔子的變化怎麼樣?”安莉說,臉馬上又紅彤彤的了。
“我和張北擔心我們以後有了孩子去了托兒所認不出來怎麼辦?”小晨說,她忽然有點語無倫次,她想把話岔開,眼前的這個孩子讓她心裏很亂,明明不是兔子,安莉卻說眼前的這個孩子就是兔子?到底出了什麼事?從什麼地方冒出來這麼一個孩子?孩子又不是別的什麼東西。
“一喊名字就知道是誰的孩子了,所以人人從小都要有個名字。”張北說,“這你不用發愁,隻要一喊就知道誰是誰了。”
“兔子,兔子。”張北對那個小孩兒喊了兩聲。。
“你給他塊兒糖他就答應了。”安莉取了一塊兒糖。
張北要把糖遞給兔子時兔子閃了一下,卻把手裏的積木放在了嘴裏。
“那不是吃的東西!”安莉大聲說,“什麼都往嘴裏放。”
“你不說他是兔子我就不敢認了,他的耳朵和以前不一樣了。”小晨終於把自己的擔心說了出來,“耳朵的變化太大了。”
“沒變化。”安莉好像一下子就不高興了,“是你記錯了。”
小晨看著張北。兩個人又都一齊看著安莉,安莉的臉又紅了起來,她緊張起來。“你們記錯了,耳朵原來就是這樣,就這樣。”
張北看看自己的愛人,張北覺得應該把話岔開說點別的什麼。就說起蜜蜂的事。“春天的時候蜜蜂可能要分箱。”又說自己的院子南邊有一大片開黃花的植物,“可能是黃花菜。”
“蜂蜜能放很長很長時間。”安莉不緊張了。
“天熱也放不壞?”小晨說,她也不願安莉緊張,但她覺得安莉有問題了,這個小孩有問題了,他是誰?這個被安莉叫做兔子的小孩兒。
安莉說:“蜂蜜甚至可以放好幾千年。”
張北對這個問題十分感興趣,這種說法他從來都沒有聽到過。“不可能吧?”
安莉的一個親戚是研究蜜蜂的,她有時候去她的那個親戚那裏看蜜蜂,有時候還會把蜜帶回來,早晨的時候喝蜂蜜水,她喜歡那種味道,一開始她還不習慣。“埃及曾經出土的一罐蜂蜜都有三四千年了。”安莉說所以蜂蜜是放不壞的。
張北馬上就聽到一個聲音在自己心裏說,“所以我要養蜜蜂。”
小晨和安莉說起養蜜蜂的事來了,“我已經看過那種塑料蜂箱了,黃色的,很好看。”這時候廚房那邊水開了,水壺尖厲的聲音把他們都嚇了一跳。
“衝蜂蜜水是不能用剛開的水。”安莉去了廚房。
廚房裏“砰”的一聲,接著是往暖水瓶裏灌水的聲音。
“安莉肯定是有事了。”小晨小聲對張北說,“這孩子是誰的孩子?”
張北不說話,他對孩子的事不太感興趣。
“孩子可不是小事!”小晨又小聲說。
張北明白自己愛人說這話的意思,誰又肯把這麼大的孩子送到這裏呢?現在人人都隻有一個孩子,就更不會。“你再仔細看看,也許你看錯了。”張北小聲說。
這時候安莉從廚房那邊過來了,她的手裏拿了一個很大的玻璃罐頭瓶子,不用問,裏邊黃黃的是蜂蜜。
張北的嘴裏酸了一下。
“最好是茶裏別放蜂蜜。”張北說,“我想隻喝茶。”
安莉又去了一下廚房,去取茶葉。安莉去廚房的時候張北和小晨都不再說話,隻是看著那個孩子,那個孩子又開始玩他的積木,但不說話。張北想起了兔子從小就吃蜂蜜,據說吃蜂蜜要比吃白糖好,因為有那個養蜂的親戚,安莉就總是給兔子吃蜂蜜。有時候還會給兔子吃一點蜂王漿,後來不知道聽誰說蜂王漿可以使一個人的性早熟,她就不再給兔子繼續吃。張北覺得蜂王漿的味道並不怎麼好,主要是讓舌頭不舒服,發麻。
安莉從廚房裏出來了,她對張北和小晨說:“蜂蜜裏邊有各種維生素。”
張北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右手的大拇指靠指甲的地方有些疼,冬天的時候張北的那地方總是愛裂,現在是春天了,那地方又裂了個小口子。張北對安莉說:“蜂蜜也許會治好我手上總是裂口的毛病,要不要我也來一杯。”
“兔子的耳朵也許真就是給蜂蜜弄好的。”這句話突然就從小晨嘴裏說了出來,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說這句話,她看著安莉。
安莉的臉就又一下子紅了起來,紅彤彤的。
張北對小晨說,“喝吧?正好。”
喝著蜂蜜和茶水,老半天,他們誰都不再說話。屋子裏都是蜂蜜的味道。
張北好一會兒才說:“什麼時候也帶我去看看蜜蜂。”
安莉說,“好吧。”
“要是蜇了你怎麼辦?”小晨對張北說,“你實際上不太喜歡蜜蜂。”
張北突然笑了一下,說,“讓蜜蜂蜇一下有好處,可以提高免疫力。
然後,張北和小晨就告辭了。
走之前,小晨幫安莉把茶杯去廚房洗了一下,廚房的地上都是水,有一個綠色的兒童塑料澡盆,裏邊接了半盆水,看樣子,安莉是要給兔子洗澡了,或者是已經洗完了。總之廚房裏很亂。
已經看不到安莉的房子的時候,小晨才對張北說:
“也許過兩天就有尋小孩的啟事貼出來了。”
“這事肯定與安莉無關,”張北說,“我認為那孩子肯定就是兔子,隻不過是大耳朵吃蜂蜜吃的變小了,”張北說,“我相信蜂蜜有這種功能。”
“如果是我們的孩子呢,你想想,你會怎麼辦?”小晨說。
張北看著小晨,“那我也許真應該讀讀偵破小說了。”
“你說什麼小說?”小晨說。
“我看還是先讀養蜂手冊吧。”張北說院子裏有一箱蜜蜂挺好,我同意你養蜜蜂了,天天都可以喝到新鮮的蜂蜜。這麼說著,張北都好像聽到了蜜蜂扇動翅膀的輕微的聲音。張北忽然站住了,對小晨說,“我要先去買雙鞋子。”
“要不要再買兩瓶蜂蜜,你的耳朵比較小。”小晨說。
“我的耳朵不需要往大長,需要往大長的不是那地方。”
張北步子邁得很大,小晨在後邊追,他們進了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