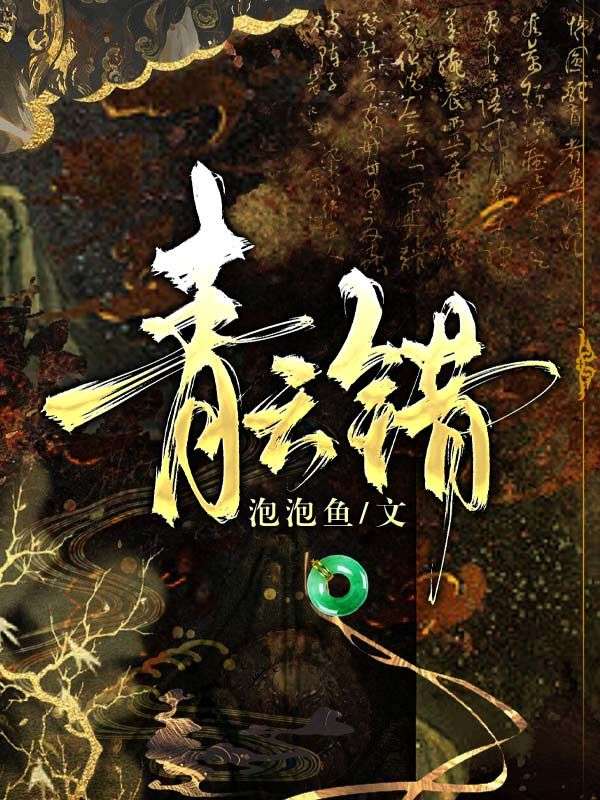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章
未婚夫帶回一個孤女後,全江湖都在笑我。
青雲大小姐十幾年情深,不如孤女一滴淚。
他為她當眾悔婚,裁我新衣、棄我口味,連我生辰那日都在陪她賞梅。
前世我不甘深情錯付,硬逼著他履行婚約,最終落的家破人亡。
重來一回,我選擇成全他,和他人成婚。
可他卻死死拽我手腕:
「和你成親的本該是我!」
未來夫婿三拳將他捶倒在地,冷笑:
「引細作入青雲的蠢貨,也敢提本該?」
1
因任務一別三個月的江澈,終於在婚期前一周趕回了青雲山。
我站在廊下看著他風塵仆仆地穿過庭院,心口那點積壓的委屈忽然就散了。
到底還是記著婚期的。
可我還沒迎上去,他就徑直去了爹爹的書房。
我悄悄跟到門外,卻聽見他見到爹爹的第一句話是要與我退婚。
「師父,我對風筱隻有師兄妹之情,如今我已找到真愛,此生非阿月不娶,請師父成全。」
爹爹瞥見了門外的我,臉色鐵青:「胡鬧,婚約豈可兒戲。」
江澈順著爹爹的視線望向我,眸中沒有久別重逢的欣喜,隻有盼我鬆口的希冀。
我死死盯著他,拳頭在袖中越握越緊:「退婚?除非我死。」
他的眼眸猛地一深,垂下眼去,避開了我的目光。
我不信我們從小到大的情分、練劍時他專注糾正我招式時溫柔的神情、月下他曾說「筱筱,此生唯你」的誓言,全都比不上一個來曆不明的女子。
夜深,我輾轉難眠,終是去了他的院外。
燭火搖曳,窗紙上映出兩個親密依偎的人影。
我正要叩門,卻聽見裏麵傳來低語。
「阿澈,我聽說有種藥能讓人忘情失憶,若是大小姐忘了對你的感情,或許就肯放手了。」
回答她的是一段沉默。
良久,才聽見江澈聲音低沉,帶著一絲掙紮後的妥協:「容我想想。」
我揪緊衣裳的手瞬間鬆了,留下一團褶皺,心也涼了半截。
第二日,我魂不守舍地去了百草房。
管事的弟子見是我,恭敬地取出記錄冊。
我一頁頁翻過,最終停在他的名字上,名下寫著忘憂草、三生花、斷腸珠。
一味不差,正是那失憶古方所需的藥材。
他竟真的聽了那女人的話想對我用藥?為了退婚,不惜毀了我?
證據擺在眼前,可我心底竟還存著一絲可笑的妄想。
或許他有苦衷?或許那藥不是為我準備的?
猶豫再三,我再次走向他的院子,腳步虛得如站了一天的樁。
院門虛掩著,未關嚴實。
還未走近,女子的呻吟和男子粗重的喘息便清晰地傳出來。
「輕些.」
「我的阿月.」是我從未聽過的充滿占有欲的語氣。
我僵在原地,一個字也說不出。
所有的不信與情愫,在這一刻被屋裏曖昧的纏綿碾得稀碎。
原來他不是一時糊塗,他是真的不要我了。
2
自那日後,江澈對阿月的好不再顧忌。
阿月畏寒,他便將庫房裏那塊為我獵來、說要在婚後給我做圍脖的火狐皮裁了,給她做了暖手套。
我練劍不慎劃傷手臂,血漬染上衣袖,他路過瞧見隻蹙眉道:「怎如此不小心?自己去處理一下。」
轉身卻緊張兮兮地捧著阿月被樹枝劃了道白痕的手,小心翼翼地上藥,如珍似寶相待。
他曾知我嗜甜,每次外出歸來總會變戲法似的給我帶各式各樣的糖糕。
如今,他帶回的全都緊著阿月的口味,清淡的、酥軟的,反正再沒有一樣是我愛的甜口。
他甚至忘了,三天後是我的生辰。
以往每年,他再忙也會備好禮物,清晨便放在我窗前。
今年,我等到日上三竿,卻隻聞見他陪阿月在後山賞梅的笑語聲。
他醉倒在阿月的溫柔鄉裏,早已將過去十幾年待我的好忘得一幹二淨。
父親曾說過,凡事不能太過強求。
我想起了江澈取走的三味藥,心想若他真能對我下手,那感情便如握不住的沙,散了就散了。
江澈像得到感應一般,這日端著一碟精致的雲片糕,主動來了我院子。
他語氣不再柔情,還含著一分僵硬:「筱筱,嘗嘗這個,新來的廚子做的。」
糕點上撒著我最愛的桂花糖粉,香氣誘人,卻混著一絲苦澀。
我的心終是沉了下來。
我看著江澈複雜的眼神,心想忘了也好。
就在我指尖即將觸碰到雲片糕時,一聲厲喝響起:「別碰!」
緊接著,一道掌風掃過,打翻了我手中的碟子。
碟子碎裂在地上,雲片糕散落一地。
我愕然抬頭,瞧見院門口的雲硯,一雙總是含笑的眼此刻卻怒氣滔滔盯著江澈。
雲硯的聲音發冷:「大師兄,你給她吃的是什麼好東西?」
被突然質問,江澈臉色忽變,眼神躲閃著:「不過是尋常糕點。」
「尋常?」
雲硯一步向前,將我護在身後,以身軀隔開了我與江澈。
「要不要現在請藥堂藥堂長老來驗驗?」
江澈嘴唇動了動,終究一個字也說不出,狼狽轉移視線。
我看著地上的狼藉,心口的痛密密麻麻地散開,提醒著我人是多麼善變。
我慢慢抬頭,看著曾愛慕的少年郎,輕聲道:「不必驗了。江澈,我們退婚吧。」
說完,我不再看江澈瞬間發白的臉,走進內室,散下了簾子。
簾外,是兩個男人無聲的戰爭,以及我要揮別的過往。
退婚的消息不出一個時辰傳遍了青雲。
我尚在屋中對著娘親留下的鎖心佩出神,前廳便傳來爹爹召見的消息。
我以為是安撫,或是關於退婚後續的事宜。
卻見雲硯鄭重跪在爹爹麵前:
「師父,弟子雲硯心係筱筱多年,隻是往日她已定下婚約,弟子隻能將心意深藏。如今婚約已退,弟子懇請師父將筱筱許配於我。我必傾盡所有,護她一世周全,絕不叫她受半點委屈。」
爹爹吃了一驚,目光複雜地看向我。
頓了片刻,爹爹道:「硯兒,你先起來。此事.終歸要看筱筱自己的意思。」
他看向我,語氣沉重而寵溺:「筱筱,你若願意,爹沒有異議。你若不願,爹爹養你一輩子。」
爹爹話落,雲硯身子猛地一顫,視線緊張地落在我身上。
我看著跪得如鬆般的雲硯眼裏爭相湧出的情意,想起方才他打翻雲片糕時的身影,想起他多年如一日的默默守護,緩緩閉上的心門似乎又有了一絲晃動。
3
我深吸一口氣:「多謝二師兄的厚愛,隻是現下我無心再談婚嫁,若你不介意,我們可以先試試,但不急著定下婚約,可好?」
雲硯眼底閃過一分失落,但隨之而來的欣喜讓他鄭重相應:
「好,都依著你,隻要你肯給我機會,多久我都等。」
父親見狀,也微微頷首,算是默許了我們的事。
我原以為所謂的試試,不過是多了些碰麵相處的機會。
卻不知雲硯的試試,是鋪天蓋地的溫柔進攻。
自那日起,我院中的小廚房再沒開過火。
每日清晨,必有熱騰騰的早膳送來,花樣多而不重複,且樣樣符合我的口味。
午後的甜湯,晚間的宵夜,甚至是癸水期間我慣喝的薑茶都備得恰到好處。
最讓我心驚的,是院中的螢火蟲。
那日我不過隨口提了句夢中的流螢,可惜青雲山高,不見流螢。
沒幾日,他竟獨自潛入山麓溫暖濕地,用內力小心護著,帶回整整一袋的螢火蟲。
入夜,螢火蟲在院中流淌,如銀河般閃爍,照映著他略帶疲憊卻欣喜的臉。
他撓撓頭,笨拙道:「這些都是用內力溫養著的,不知能活幾日,你若瞧著喜歡,我明日再去捉些。」
我若去練劍,他總恰好在不遠處練功。
我若去藏書閣,他總能剛好找到我想看的孤本。
我若因江澈和阿月的出現而情緒低落,他從不追問,隻默默陪伴,或講些江湖趣聞,或用他新得的寶劍舞一套劍。
這一切,江澈都看在眼裏。
他起初嗤之以鼻,甚至帶著幾分居高臨下的憐憫。
一次任務歸來,他在山門處撞見雲硯正將一支新得的玉簪插入我發間,腳步頓了頓,唇角勾起一抹嘲諷的弧度,仿佛在看一場徒勞無功的戲碼。
他認定我隻是在賭氣。
認定我十幾年深入骨髓的喜歡,絕非雲硯這短短時日的殷勤所能撼動。
他甚至覺得我收下雲硯的東西,不過是為了刺激他回頭,畢竟他的腰間還係著我曾送出的鎖心佩。
那鎖心佩原是一對,是母親的遺物。
父親說,這鎖心佩分為陽佩和陰佩,陽佩給我未來的夫婿,陰佩自己留著,寓意鎖心同心,永不相負。
當年我滿心歡喜將陽佩贈予他時,他鄭重發誓定用性命守護。
如今我還沒有要回,便成了他堅信我絕不會真正離開他的憑據。
他醉倒在阿月的溫柔鄉裏,做著左擁右抱的美夢,卻忽視了人心都是肉長的。
我封閉的心門,正一點一點被雲硯笨拙而堅定地敲著,已有了鬆動的跡象。
我有時看著雲硯為我忙前忙後會有些恍惚。
雲硯對我的好,與江澈從前對我的好似乎有所不同。
江澈對我的好,像暖陽。
我曾在其照射下驅散寒氣,貪婪地以為我思故永恒,卻忘了晝夜更替,太陽會落山。
而雲硯對我的好,像沉默的青山屹立不倒,從前不覺,如今卻明了更為踏實可靠。
隻是,那枚鎖心佩還掛在江澈腰間,時刻提醒著我過去的愚蠢。
雲硯從未提及過鎖心佩,但他的目光偶爾會不經意掃過江澈腰間,眸色發沉,而後朝我揚起更溫柔的笑意。
我知道他在等。
等我親手去解開那把名存實亡的鎖。
4
那枚鎖心佩是要拿回來的。
我尋了個江澈獨自一人的時機,在回廊處攔下他:
「大師兄,請將鎖心佩歸還於我。」
江澈微微發怔,手下意識撫上腰間懸著的瑩白玉佩。
他臉色微變,強顏歡笑:「筱筱這是何意?這玉佩,你既贈予我,便是我的。」
「此佩是贈予我未來夫婿的。」
「婚約已解,你亦非我良人,此佩自然該物歸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