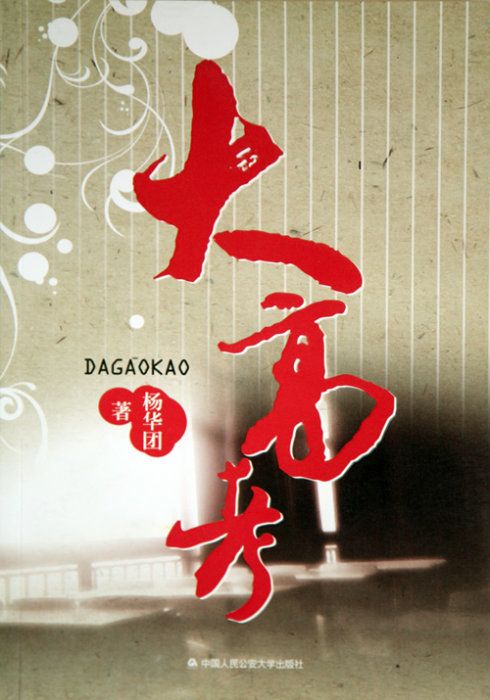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高考作弊案
第二章 高考作弊案
6、男人哭泣
奧賽班要通過考試重新選拔,陳一卉對女兒的實力有信心。當天晚上有人約她吃飯,對陳一卉來說又是意外的煩惱。
出麵約陳一卉吃飯是她一個姨媽。這個姨媽是陳一卉母親的堂姐,早年嫁給了祁北公司(本市最大的那家礦山集團公司的前身)的工人,成了城裏人。陳一卉母親多病,家庭生活困頓,姨媽多年來一直資助她家。前些年祁北公司職工福利搞得好,姨媽每每回鄉下,總會給陳一卉家帶來凍雞凍魚大米清油,也帶來濃濃的情意。母親得了大病,在市醫院做手術,也是這個姨媽跑前跑後精心照顧。陳一卉進城時間不長,她母親病故了,姨媽在她心目中和親媽差不多。兩年前姨夫也去世了,陳一卉不時到姨媽家走走,幫老人家做家務,和她拉家常,是報恩的意思。這次,姨媽電話都沒打,親自上門來請吃飯,陳一卉“噗嗤”笑了:“姨您真逗。我請您還差不多,您請我吃的什麼飯呀?您看我沒工作不掙錢,賑濟災民呢?”老人被陳一卉逗笑了:“這個一卉!你不是外甥女,你是姨的親女兒,我也不繞彎子。不是我請你,你姨夫一死,他的退休金沒有了,我哪兒來的錢請你吃大餐?可是不行啊,我幹兒子劉庚旺說要認識你,叫我引薦一下。劉庚旺你沒見過吧?他媳婦沒了,留下個孩子。我給他照看過小孩,他把你姨夫喊幹爹,把我叫幹媽呢。庚旺搞建築,可有本事啦,會掙錢。你姨夫得癌症,做手術花那麼多錢,都是他讚助的,也不讓還。你說說,我這幹兒子該有多仁義,不象有的人當了老板就成白眼狼了。他不知道有啥事要找你,托我約一下。一卉,這事兒姨推不掉。隻要你肯去,我不去也行,人老了,坐到飯桌上顫顫巍巍,丟人得很。”聽了姨媽一番話,陳一卉覺得這頓飯不去吃看來是不行的,於是隻好答應了:“我去,您也要去。不過我沒本事,給人能幫啥忙?白吃飯多不好意思?”
“一卉呀,我這幹兒也一直單身,帶著個兒子,跟你家姑娘大小差不多。哎呀,要麼姨媽給牽牽線,你倆處一處咋樣?”老太太恍然大悟說。
“姨,您還會亂點鴛鴦譜?您要這樣說,我還真不去了。”
“別別別,一卉。牽線是我隨口說的,不作數。劉庚旺找你肯定有別的事情。”
到了飯桌上,陳一卉對劉庚旺第一印象不錯。沒去之前,她想象中的劉庚旺無非是個包工頭,滿嘴酒氣,滿身煙味,西服皺皺巴巴,領帶歪歪扭扭,扭曲變形的皮鞋上沾著泥巴,說話粗俗,隨地吐痰……可見了麵,全然不是那回事兒。劉庚旺一身休閑裝,清清爽爽,人很筆挺,相貌端莊,戴一副金絲邊眼鏡,看上去頗像知識分子,見了女人甚至有幾分羞澀,弄得陳一卉預先在思想上構築起來的防線土崩瓦解。
“劉先生,有什麼事您直說吧。我在姨媽跟前和親女兒差不多,您也把她老人家喊幹媽,咱就算親戚。隻怕我沒本事,幫不上您什麼忙。”剛剛在飯桌上坐定,菜還沒上來,陳一卉就主動表態。
“嗬嗬,小陳這麼說我真高興。哦,我叫你小陳很冒昧,不過,估計我比你大幾歲吧。”
“沒關係,怎麼稱呼都行。”
“咱不談事情,先好好吃飯成不成?在我心裏,吃飯比談事情重要——本來也沒啥大不了的事。幹媽說了,小陳是好人,很本分的人。不象我這種做生意的,建築承包商,想做好人也做不了。能跟你這樣的好人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我該有多大的麵子啊!”
陳一卉被男人逗笑了:“一般來說,承認自己是壞人的人,想必壞不到哪兒去。”
“哎呀小陳,你這樣說讓我歡欣鼓舞。一會兒好好敬幾杯酒,就衝你不把我當壞人。”
這頓飯吃得輕鬆。美女陳一卉不經意間飲了很多葡萄酒,弄得臉上紅光四射,比平日更顯漂亮。姨媽還算有眼色,吃飽了飯,看幹兒子和外甥女意猶未盡,就說:“我吃好了。年齡大的人本不喜歡在外頭吃飯,坐著累。要不我先走一步,你倆再坐會兒?庚旺不是有事要說嘛?”聽老太太這麼說,劉庚旺看看陳一卉,她麵帶微笑不置可否。劉庚旺於是很受鼓舞,把老太太送到餐館外麵,攔輛出租車給送走了。
“一卉。”再回到飯桌上劉庚旺改變了對陳一卉的稱呼,“我這樣叫你不介意吧?跟我幹媽學的。叫‘小陳’有點兒生分。你說呢?”
“我說什麼呢?你怎麼稱呼都行。”陳一卉微笑中帶點兒羞澀。
“太好了!你叫我老劉,庚旺,或者‘嗨’、‘呔’啥都行,就是別喊‘劉先生’,有拒人於千裏之外的感覺。一卉你說,還要不要繼續喝酒?再來一瓶幹紅,還是洋酒?”
“隨你。”陳一卉對這個男人幹脆不設防了,她對自己的酒量有信心。
兩個人又喝了一瓶幹紅葡萄酒。劉庚旺越喝越興奮,外衣脫了,眼鏡也摘了:“一卉,你真是女中豪傑!今兒咱一醉方休如何?或者,換個更好的環境繼續喝?”
“適可而止吧。你我第一次見麵,交往要有度。不過我告訴你,和你一起喝酒很愉快,以後假如還有機會,我不會拒絕。”
“爽快!一直沒敢誇獎你的美麗,這會兒我鬥膽說說,一卉,你很美。不僅五官、身材好,更重要的是氣質。你是能讓男人著迷的女人,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我是心裏話,你該不會認為我輕佻吧?”
“嗬嗬,聽一個男人說自己美麗,對女人來說很受用。況且我都快半老徐娘了,這樣的機會不多。你多誇幾句,我愛聽,我也不認為你輕佻。不過劉先生——我還是喜歡稱呼您劉先生——我還能記起,今天你請吃飯,好象有事情要說。現在是時候了,再不說會坐失良機。你甭看我狀態挺好,我知道快醉了。等我呼呼大睡,你後悔就來不及了。”
“開玩笑,一卉你開玩笑。要麼這樣,咱找個安靜的、能說話的地方,再喝會兒茶,等你酒醒了,我再說事情?”
“隨你。”
後來在一家很高檔的茶館裏,劉庚旺才說出他找陳一卉的目的。
“一卉,今天找你很冒昧。真有點兒事情求你幫忙,不好意思開口呢……”劉庚旺吞吞吐吐。
“有什麼不好意思?既然姨媽介紹我們認識,連你的飯都吃了,酒也喝了,說明我們已經是親戚,是朋友,起碼是熟人。有話直說,我瞧不起男人哼哼嘰嘰躲躲閃閃。”陳一卉說。
“我也不明白在生意場上混了許多年,臉皮咋就練不厚呢?尤其在女人麵前。”劉庚旺的確有幾分羞澀,“這樣吧,先給你說說我家的情況——一卉你千萬別嫌我羅嗦——除了搞建築做生意,我一個人帶著兒子過日子。兒子十五歲,叫劉遠航,剛剛考上高中。我是從鄉鎮企業走出來的,孩子他媽也是農村人。當初家裏很窮,我經常在外麵跑,老婆一個人在家種莊稼,還要操持家務贍養老人,把她累壞了。後來我掙了點兒錢,在城裏買了房子,家裏的地不用種了,老婆本來可以進城過好日子,能享福了,可誰知道,她的先天性心臟病突然發作,一下子走了……”劉庚旺說到這兒,眼圈泛紅,聲音也哽咽了。
“哦。她有心臟病你不知道?怎麼能不操心,讓她犯病了呢?”陳一卉不知不覺被劉庚旺的敘說吸引住了。
“這正是我不能原諒自己的地方。當初知道她心臟不好,我不主張要孩子,可女人天性喜歡小孩。生我們家遠航老婆冒著生命危險,我強不過她,隻好在醫生指導下小心翼翼擔驚受怕,總算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了,一天天養大了。後來她身體反倒比生小孩之前好了許多,我倆都對病魔放鬆了警惕。還是怪我,隻顧做生意,對她照顧不周。”劉庚旺說著滿臉戚然,眼淚順著兩腮悄然流下。
陳一卉被感動了,覺得這個男人不錯,有情有義。
“我今天求你,說到底是為兒子。”劉庚旺終於說到正題上了,“事情是這樣的,市一中新生編班,劉遠航本來進了奧賽班。我也不瞞你,他中考成績不是很好,我托了關係,走了門子。一卉你可能覺得我是那種投機鑽營、翻雲覆雨的人,可為了兒子,我並不覺得找找人、想想辦法、走點兒後門是丟人的事。畢竟為了孩子嘛,可憐天下父母心,何況,我不能對不起亡妻,她在天上看著我們父子倆呢。進奧賽班又不是上大學,不是出國留學,最多不過是給孩子創造一點好的學習條件,奧賽班畢竟老師配備得好,學習氛圍也好,有競爭性。”
“嗬嗬,難怪我女兒進不了奧賽班,原來讓你們這些有辦法有門路的家長給擠出來了。”陳一卉說。話雖這樣說,但陳一卉對劉庚旺並不反感,反而覺得他做的事情可以理解,覺得這個男人很真實。
“這兩天家長一鬧事,學校把原來編班的結果推翻了,奧賽班要重新選拔考試。我打過聽了,家長眼睛瞪得大大的盯著,教育局和市一中放出話來,一定要公開公平公正,走門子肯定不行了。我兒子能考成什麼樣,我沒有把握,所以才來找你幫忙。”
“我能幫什麼忙?”陳一卉很詫異。
“嘿嘿。我好不容易打聽到,你女兒——她叫楊帆吧——學習成績特別好,上初中全校數一數二,中考成績沒有拔尖,隻不過是因為考試身體出了小意外。奧賽班再選拔,你女兒肯定能考中,百分之百進奧賽班。恰好我幹媽是你姨媽,我沒有別的辦法,隻好硬著頭皮找你。今天一見,我覺得咱倆是老朋友了,相見恨晚。我覺得你一定能幫忙,我的信心比沒見到你之前充足多了。一卉,請你看在我死去的老婆麵上,你能幫我就幫一把吧!我求你。”劉庚旺態度十二萬分誠懇。
“你倒挺會說話。說實話,截至目前,我對你印象良好,真有點兒一見如故,你可千萬別破壞我對你的好印象。你說說,我怎麼幫你?”陳一卉問道。
“唉,真不好開口。再難也得說出來,我把這張臉當屁股了。”劉庚旺在臉上抹了一把,仿佛把害羞的臉皮拿掉,“是這樣的,盡管奧塞班選拔考試會很嚴密,我還是有辦法讓我兒子坐在你女兒旁邊或身後。我的意思想讓你給楊帆安排一下,考試時把她的答題卡、試卷不要遮蓋得太嚴,給我兒子提供一點點方便。僅此而已。”
說完這幾句話,劉庚旺冒出一頭汗,不知是急還是羞慚所致。
“哦?嘿嘿,嗬嗬,哼,我做不到。”陳一卉的臉沉下來,“暫且不說這種事情見不得人,假如僅限於大人之間,我能幫你搞點兒小動作,為了孩子,也就罷了。可這種事怎麼能讓孩子去做呢?你想沒想,劉老板,讓我女兒幫你兒子作弊,我在女兒麵前怎麼開口?虧你能想得出來!”
陳一卉的態度讓劉庚旺瞠目結舌。他滿臉的無奈和沮喪,枯坐半天,然後說:“一卉,在你麵前碰釘子是預料當中的事。既然你覺得為難,就算了,權當我什麼都沒說。實在對不起,請你原諒我的冒昧和大不敬。”
劉庚旺一臉的失望以及恭謙的態度反倒讓陳一卉愧疚,她努力擠出一絲笑意:“幫不上忙,我也覺得對不起你。怎麼辦呢?飯也白吃了,酒也白喝了,改天我回請你吧。”
“你說哪裏話!求人幫忙也不能強人所難,吃頓飯算什麼?交個朋友該有多好!不過,你要是不願意交我這樣的朋友,今天出了門,你可以當作咱倆根本不認識,再遇到了你就把我當空氣。我心裏肯定會遺憾,但絕不怪你,要怪,隻能怪自己。”劉庚旺努力調動笑意,笑比哭還難看。
“哪兒能呢,朋友還是朋友。和劉老板交朋友,我也算高攀了。”陳一卉感覺心中的愧疚愈甚。
“事情倒不大,我可以再想別的辦法。隻是兒子進不了奧賽班,我對老婆的在天之靈怎麼交代啊?”劉庚旺這樣一說,眼淚再次奪眶而出。
男人的眼淚又一次碰觸了陳一卉心中最柔軟的地方,她忽然失去了原則性:“好吧,我改變主意了。我試試給孩子說吧,要是你兒子和我女兒坐不到一起,那怪你,萬一我女兒臨場發揮不好,也怪不得我。”
劉庚旺喜出望外,差點兒跳起來:“一卉,一卉呀,我簡直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我兒子會感謝他陳阿姨,我老婆在天堂給你作揖哩。一卉,你真好,真好!”
陳一卉看到這個男人眼睛裏淚光閃爍。她的感受很複雜,腦子成了一盆漿糊。
回家路上陳一卉想,這個男人咋那麼愛哭呀?簡直比劉備還會哭!
這樣的事情,日鬼搗棒槌,該怎麼對女兒說呢?讓孩子弄虛作假,做母親的在她心目中還會有威信嗎?
陳一卉有點後悔。